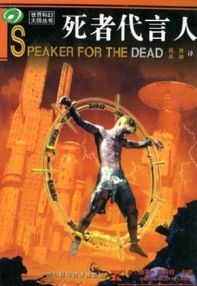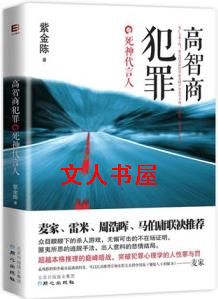姑妄言-第1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知他是拐带逃走。叫那丫头来,问道:“他既逃走,你可有不知道的?你实说,他同谁有奸?跟谁去了?”那丫头道:“我不知甚么叫做奸?【妙极。是无知小丫头语。】他往里去,又不曾告诉我,我那里知道了?”【更妙。如听得一个小丫头说蠢话。】阮大铖越怒,上前打了几拳,踢了几脚。那丫头大喊大哭,疼得满地打滚,道:“腿在他身上,他走了,我如何晓得?我要知道,我也去了。”【妙妙,愈答愈奇。我也去了,不知他去作何事。】阮大铖更怒,揪过头发,又踢打了一顿,道:“你快说,不然我打死你。”丫头怪叫道:“杀了我,我也不知道,与我甚么相干?我每常只见苟雄常来屋里,姨娘就把我倒扣在那边。我间或看见他腰里塞些东西出去,别的我不知道。”
此时毛氏同众妾听见吵闹,都起身走来。毛氏听见这些说话,暗暗吃惊叫苦,生怕阮大铖处治苟雄。阮大铖叫上夜仆妇下去叫那一个管事的家人庞周利来,吩咐道:【毛氏何幸,苟雄始去,而傍州例之。家人即现乐哉。】“看苟雄在那里,叫了来。”庞周利去了一会,来回道:“苟雄反锁着门,小的拧开看时,房中一空,大约逃走了。”阮大铖知是他拐去了,心中痛恨。要报官缉拿,又怕马氏说出他偷媳妇的话来,只得暗恨忍住。惟独毛氏更咬牙切齿,恨这马氏把他一个活心肝生生的摘了去。
再说爱奴一夜同花氏睡着讲闲话,忽然想起郏氏的事,向他道:“你道大奶奶这淫妇该杀不该杀?我动那一夜,听得他向二相公说老爷那老禽兽同他也是厚间。这没廉耻的淫妇,公公媳妇也做这样的事。就是骚极了,宁可偷别人也不肯偷公公。”花氏听了,暗想道,倒是老爷奸我的话不曾告诉他。若他知道,把我也看得不值钱了。这夜两人高兴了一番,正然睡熟。花氏梦中忽然一惊跳起,爱奴也惊醒,忙一把抱住,道:“你怎么了?” 花氏定了半晌,方说道:“我梦见姆姆房中那丫头,一身鲜血,来向我索命。骂我说不是我私通了你,如何得害了二相公同姆姆。因你杀了他两人,故此才又杀了他。你的一死不消说,连我也放不过。我再三求告他,他决不肯放。向我身上一扑,一惊醒来,魂都几乎吓掉了。”爱奴听说,心中也有几分害怕。只得勉强安慰他道:“这是心上梦,理他做甚么?” 口虽如此说,心下未免怀着鬼胎。那花氏日间间或陪公公,夜里每宿伴爱奴。过了数月,竟怀了孕,也不知是那一个的种。渐渐丰肚。那花氏要把公公奸他的话说与爱奴,或商量出个法子来,竟往阮大铖身上一推,谅阮大铖自然替他想法。
花氏因前爱奴说郏氏的话,他硬口怕羞,不肯说出。但向爱奴道:“这怎么处?若露了出来,就不好了。”那爱奴问他要了几钱银子,寻了些打胎药来。吃了数剂,毫无效验。爱奴道:“如今没法了,只有逃走一着。他一个官宦人家媳妇跟家人走出,决不好报官访拿。苟雄同马六姨不是样子么?我同你到他乡外府做一对夫妻过日子去罢。连丫头也带了去,万不得巳卖了他,做盘缠也好。”花氏一来无可奈何,二来他心中实爱爱奴,憎嫌公公老了,便依从他。问那丫头,丫头恐主母走了,追问他起来,可有不知情的?也情愿同去。遂将细软打了两个大包,爱奴背了一个,丫头背了一个。花氏包了头,穿了丫头的布衣裙,三人悄悄开门而去。
次早,管门的人来开大门,见重门洞开,吃了一惊。走了进来,层层门都开着。见花氏的房门也大开,叫了两声,不见人影。入内一看,见满地旧衣服,东西撂得乱三搅四,主婢二人都不见了,忙上去回了阮大铖。阮大铖又吃一惊,命查。家人说爱奴也走了。阮大铖虽知是他拐了去,但家奴拐去儿妇,说不出来,只暗暗通知了亲家。
这花氏的父亲花知县也是个在闲乡宦,听得乃爱演了红拂记,可还说得出一句话来?当年司马懿假瞎,他也只好假聋罢了。可笑这阮大铖奉承魏珰,做了多少恶事,富贵二字不曾图得一件。积作得一个正妻,两个儿媳妇,两个美妾,一个爱女,都报应做出这等好事。他不但不知警省改过,心肠愈丑愈辣,后来便见。
且说那爱奴同花氏并丫头偷出了大门,天尚未明,觉得眼前一个黑影拦拦挡挡。及走到了跟前,却又不见。【显报则说明易晓。此等是隐隐忽忽报应,看者须知。】爱奴心中甚是疑影。每常是走熟了的路,此时昏头昏脑,总看不清街道。直至东方大亮,眼前黑影不见了。【向花氏梦中索命是他,花氏腹中之物也是他,此时黑影也是他。此时作书者暗含报应,不肯说得活现,恐人讯说鬼话也。】才走出了水西门,要雇船往上江去。因见来往的人络绎如织,恐遇着熟识,心下未免惊慌,面上的颜色便有些变异。不想正遇着几个捕快出城拿贼,见他三人既无行李,只背着两个大包,,慌慌张张,见人都有惊惧之色。又见花氏虽布衣淡妆,面孔非贫家妇女,知是逃走的人,上前一阵盘问。那爱奴是心虚的,面容失色,嘴中话都说不清白。那花氏同丫头脸如白纸,浑身抖战。
捕快将他三人带到一个僻静小庙中,把爱奴拷问起来。他忍受不得,方说是阮大铖的家人,拐的一个是幼主母,一个是丫头。他众人又问花氏,花氏今虽做了淫奔的妇人,当日也是宦家的闺秀,何尝见过这些恶事?他先见拷问爱奴的那些非刑,魂都没了。恐怕拿他也拷问起来,二来冥冥中也有个神鬼。那郏氏、阮优虽有可死之道,而爱奴非杀他之人。况爱奴、花氏罪更浮于他二人之上,岂有逃脱之理?花氏遂将如何通奸起,如何遇上阮优,如何将他责打,如何杀了他丈夫嫂子丫头三个人,又如何通奸有孕,才逃了出来。【阮大铖造化,到底亏他害羞,不曾说出也。】鬼使神差,细细说出。捕快遂带到县中,详细禀知。知县先问花氏,花氏又细说了一遍。然后问爱奴,也不曾用夹棍,也就一一招成。二人画了供,知县将爱奴打了三十收禁。花氏因有孕免责,也下了女监。丫头交与官媒保出。申报了上司,上了本。爱奴因奸杀害家主,问了凌迟。花氏虽非同谋,知丈夫被杀不首,反与爱奴通奸私逃,与同谋杀夫罪等,也问了剐。阮优、郏氏叔嫂通奸,律绞,已死勿论。丫头免议,并赃物给还原主。
爱奴到了监中,众禁子一来因他无钱打点,这是第一件。二来恨他凶恶,日钻夜押,受了无限苦楚。【此因无银打点耳。若有钱,彼奉承不暇,何恨之有?】花氏又带上了两个禁子,【此极写禁子之恶。】每日每夜上下口都有得受用。等他养过了娃娃,才带他二人到了市上。上了木驴,受用了一剐。临刑的前一夜,爱奴、花氏同梦见郏氏的那丫头,笑容满面,向他抚掌道:“你们也有今日。”二人醒了,自知死期一到,欲悔从前,已是无及。再说那知县差人去叫阮家来领丫头赃物,阮大铖回书都不要了,任凭发落。知县命将丫头官卖,赃物入库,那也就是他囊中之物了。
且说花氏的这一件事,也是眼前报应的一重公案。【这一部书讲淫亵的事,千言万语总不过归到报应两个字。看花知县这一重公案,似乎赞笔,可以不用。然是一个要紧报应,亦可警掌刑名之辈,勿谓其为蛇足也。】他父亲花知县,名叫花翩,倒也是一榜出身。做官虽不甚贪酷,却任性多疑,凡事偏拗。【为官者任性已大误,再多疑偏拗,焉有不枉杀民命者?】他问公事,若任性起来,凭着幕宾朋友百般劝戒,他再不肯听。人知道他是这样个倔强性子,也就没人肯苦口劝他了,因此上地方上的百姓也吃了他许多的亏苦,含了无限的怨恨。且把他的事略叙一两件,便知他的为人了。
他县治中有个百姓叫做司新,家虽贫寒,却识字知书,心地奸狡。【嗟乎!读书识字,原图效法圣贤,若读书但能奸狡,读之奚益?】他有一座祖坟,与一个土财主名钱泰的山地相邻。他欺心想谋这钱泰的地扩充他家的坟山,因使了个奸心,弄了几块大砖,写了基址界限,倒写了数十年前的月日,用刀镌刻了,暗暗埋在钱泰的地上。也过了十多年,钱泰的妻子死了,就请地师在这块地上点了穴,要来安葬。司新争执说是他家的坟山,不容下葬。两家争竞起来,司新便到县中去告,说土豪恃富霸占穷民坟地。
钱泰倒运,刚刚撞在花知县手里。花知县一接了状子,便疑心钱泰是财主欺压贫穷,霸占是实。随拘了钱泰来问。钱泰禀称:“这是小的几辈传流的山地,山邻皆在,非强占。况还有当年买地的文约为据,上面写着与司家的坟地为界。”花知县命取了原契,并众山邻来问。次日,又审众山邻。异口同声都说:“小的们素常听得说是钱家的是实。”花知县问司新道:“众人都说是钱泰家的地,文书上地界又写得明白,你如何告他霸占?” 司新禀道:“老爷天恩。他倚富欺贫,想白占小的的地,小的可敢赖他?文书上虽写着与小的家的坟地为界,但那一片全是两家的地,并不曾写着亩数长尺,如何做得准?这些山邻都是他买出来的硬证,总求老爷上裁。”
这花知县先有个疑团在胸,听了这些话,越疑钱泰霸占,却无可为凭。踌躇了一会,忽问司新道:“你说的固是。但你执定说是你的,可有甚么凭据么?” 司新说:“小的父亲在日,曾向小的说,坟山后来恐有人吞占,山地界址都有砖字埋在地下。虽向小的说了埋的地方,却不曾眼见。年深日久,不知可还有没有了?” 花知县道:“这就是凭据了。纵然年久,必定还有形踪。”随差衙役押他众人同去眼看刨挖,果然在疆界上挖出几块砖来。钱泰所点之穴却在司家砖界之内,差役回衙呈上。花知县见了那砖非一日之物,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