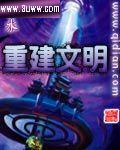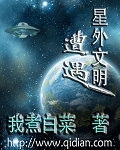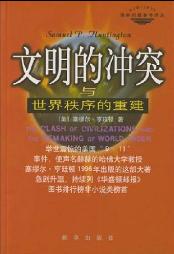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苏丹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致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族”经济。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尽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下面的石油财富和其他因素相关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现代通讯加强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私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相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区。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伊斯兰唯一的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到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围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除了这些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纱瓦外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更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一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侵占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影响的混合体。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纪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上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