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第8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猛子突地起身,出门,去了北书房。拍门声很响。老顺觉出了猛子的反抗意味,忍了几忍,才没发作。
“活人难得很。丫头。”妈抹抹泪,发话了,“你叫我们当娘老子的说啥好呢?大人是压菜缸的石头,啥事也得压。你叫我们说啥好呢?”
这老妖。老顺差点骂出口来。听她口气,仿佛是同意姑娘离婚,只是由于“大人是压菜缸的石头”,才不好明里支持。呸,头发长见识短,瞭事不远。就算离了,你又能找个啥样的?人会咋说你?没脑子。就说:“这不是压不压搅不搅的事。明里说,老子不同意你离婚。路越走越宽。生牛生马都能调过来,不信他白福是个榆木脑袋。人嘛,多劝劝,也就改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哩。”
“劝。劝。”兰兰说,“要是多少能听进一句话,也算个人了。你不说还好,一说,人家就上头上脸的。”
老伴接口道:“就是。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愣子的脾气。碰到啥就提起啥,劈头盖脸的。犯了性,爹妈都不认,能听进谁的话?”
老顺火了:“你个老妖,少煽风点火。想干啥干去!……动不动离婚离婚,你老妖离了一辈子,也没见离出个啥名堂来。”
老伴也红了脸:“哟,朝我使气来了?有本事外面使去!丫头是我养的,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不心疼,我心疼。养上十几年,我骂了句啥?打了几下?现在,倒成了人家的出气筒了?”
“你不叫人家管,就养老丫头呀,为啥往外推?”
“养老丫头也比现在强!”
兰兰抹泪道:“行了,行了。你们别再吵了。不说吧,心里憋得慌。一说吧,你们就争呀吵的。”兰兰哭了:“这日子真没过头了,哪里都是吵吵吵。活着不如死了好。”
(5)
这回,兰兰铁心了。
夜深了,但不静。至少,兰兰觉不出静。爹的鼾声闷雷似滚。兰兰怨爹没心肝。女儿天大的事都搅不了他的瞌睡。兰兰知道爹是个大肝花。前些年,柜里没一把米面时,爹就这样。妈生娃娃疼得炕上翻滚时,也这样。按妈的说法,大肝花好,心上没事,身体就好。可爹的身体也不见得有多好,伤风感冒是常有的事。妈说,大肝花的人不得噎食病。兰兰知道,得了噎食病的人饭坑里饿死。爹只要不得那坏病,大肝花也好。但兰兰总有些伤心爹的态度。当然,要是爹真为她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兰兰更难受。
第十九章(8)
妈悄声没气的。兰兰估计妈没睡。但兰兰明白妈不想叫她知道她没睡。妈的心细。她不想叫兰兰知道她为她愁得睡不着觉。妈瘦了,明显瘦了,皮包着骨头。为她,为憨头,妈的心早操碎了。兰兰心里疼,真不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妈。但除了妈,又能告诉谁呢?世界真大,人真多,可兰兰的世界小。兰兰世界里的人也少。能在妈的怀里哭,是兰兰的享受。
窗帘开着。兰兰看到了空中那瘦零零的月牙儿。兰兰觉得自己和那月牙儿一样,悬在无着无落的黑空里,孤零零的。她叹口气,很轻地蜷了身子。她怕自己的动作惊动了母亲,但被子的窸窣仍山一样响。妈的被窝似乎也响了一下,也很轻。某个角落里有老鼠在啃着什么,咯吱咯吱的。间或,还交谈一阵。兰兰认为这是一对老鼠夫妻。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兰兰都羡慕它们。兰兰和白福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你一枪我一炮的干仗外,谁都是没嘴的葫芦。吵架或是沉默是夫妻间最常见的功课。而且,这沉默是对对方的厌恶之极的无话可说。和白福在一起,兰兰没有谈话的欲望。那家伙是个什么货色,兰兰比谁都清楚。太清楚了,就什么都不想说了。
兰兰也有朋友,同村的,几个媳妇,都和兰兰谈得来。这是过门不久的事。后来,兰兰和白福一闹矛盾,婆婆就认为是那些女人教坏了兰兰。婆婆的声音难听,站在大街上耍猴似地骂。之后,朋友们就不敢做“朋友”了。一见兰兰,远远地就避了。
兰兰叹口气,觉得胸里闷得慌。许久了,老这感觉。心里像堵满了脓似的粘液,老像要呕,可也没呕出过啥。
许久了。
老鼠夫妻仍在亲热交谈。父亲仍在香甜地呼噜。母亲没动过被窝,仿佛连呼吸也没了。但兰兰分明看到了母亲那双注视她的眼睛。那是两口深枯枯的井,总叫兰兰心疼得哆嗦。
好几年没盘新炕了,炕粪味弥漫于夜气里,沁入她的毛孔,更添了她心里的浊。胸腔里更是憋得慌。
生存空间与自己格格不入。总是烦,莫名其妙地烦,想撕裂胸膛的烦。一切都不顺眼。一切都不和谐。
“这样活,有啥意思?”她想。生命成了透明通道,从这头,能瞭到那头。有啥趣味?婆媳间的呜呜闪电,夫妻间的口舌拳脚。而唯一维系她人生乐趣的引弟又走了——那是她灵魂深处不忍触摸的所在,偶一触及,便撕心裂肺——父亲却老劝她忍,忍,凑合。说是一辈子快得很。争的人,一堆骨头;忍的人,也是堆骨头。兰兰想,“忍”和“等死”有啥两样?所谓“忍”,不就是一语不发,接受现状,等自己变成一堆骨头的结局到来吗?
兰兰不愿意。
不堪回首。不敢回味少女时候的梦。青春,梦幻,追求,理想……像过眼的烟云一样远去了,消失得那样快。分水岭仅仅是举行了一个嫁人的仪式。
兰兰的幸福就像瓦上的霜一样,轻而易举就化成了水气。而无奈,却像卧在村口的沙山,你很难改变它,人家反倒步步逼近了你。
第十九章(9)
干脆,结束这婚姻!
第一次冒出这念头时,连自己都吓坏了。离婚,在她眼里,比裸着身子在大街上走更丢人。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离婚的女人,大都有无法饶恕的过失和缺陷,如不生孩子,偷情等……所以,那念头一次次冒出,一次次被她强捺下去,像按浮在水中的皮球一样,按得越深,上浮的力也越大。她终于懒得去按了。由它浮吧。
她开始认真正视它。
换个角度,她幻想了离婚后的生活。沉闷的天空顿时开了一道裂缝。清新的空气和亮光透了进来。虽说,离婚是可怕的,尤其是村人的议论--她甚至能想像得出那一道道怪怪地望她的目光--但相对于一眼就能望到白骨的生命通道,离婚无异是诱惑。而兰兰,自小就不想过乏味单调的生活。
当生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运行的时候,生活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乐趣。土地、院落、锅台、厕所构成一个巨大的磨道,而她则成了磨道里的驴,一圈圈转。本以为走出老远了,一睁眼,却发现仍在既定的轨道里转圈。变化的,只是自己脸上青春的水红消失了。她不甘心就这样走向人生的尽头。
但她一直没提出“离婚”二字。原因自然是换亲。她知道,她一跳弹,婆婆一定要强迫莹儿做相应的事。为了哥哥憨头,她得忍。
爹的态度使她失望。但兰兰知道,爹是个老脑筋。而且,爹老了。爹管得她一时,却管不了一世。她的路,最终得靠她自己走。
但这次,她铁心了。她再也不能和“杀”女儿的凶手同床共枕。
(6)
望见婆家的墙角,兰兰产生了强烈的厌恶,真不想再踏进这院落,这儿的一切令她压抑。每次,从外面回来,她就发现这房舍有种掩饰不住的丑陋:剥落的墙皮,被炕洞出来的烟熏黑的后墙,还有那柄长长的木锨。冬天,婆婆就拿这长木锨填炕,一伸一缩,透出泼妇的强悍。一见长木锨,兰兰就想到了婆婆的银盘大脸和那双小眼睛。嚷仗时,那张脸会泛出红光,小眼睛比刀子还利,令兰兰不寒而栗。
平心而论,兰兰最怕婆婆。婆婆是那种被人称为“金头马氏”的女人。从她薄薄的嘴里,能吐出许多叫人听来都脸红的话。但她又很会应酬人,会说许多客套话。嘴是个蜜钵钵,心是个刺窝窝,见人就喧“东家长,西家短,三个和尚五只眼”,能把吕洞宾说成是狗变的。不多日子,村里人就知道了兰兰究竟是个啥货色。于是,有些婆姨就感叹了:“哟,看起来灵丝丝的一个媳妇,咋是那么个人呀?”婆婆就发话了:“金银能识透,肉疙瘩识不透。能看了人的皮皮儿,看不了人的瓤瓤儿。把她当成棵珊瑚树,谁知道是个红柳墩。早知道是这么个货,宁叫儿子打光棍,也不叫娃子受这个罪。自打这骚婆娘进了门,娃子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如果说前面对兰兰的评价还叫村里人将信将疑的话,那后面说的白福受罪的话就明显是大白天说夜话了。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白福是个啥货色。
第十九章(10)
婆婆正在扫院子。兰兰进了门,婆婆扫她一眼,吐口唾沫,将扫帚使得格外有力。一股尘土裹向兰兰。这是婆婆惯用的表现自己内心不满的手法。平时也这样。她会装做没看见的样子将鸡屎垃圾等物狠狠扫向路过的兰兰。对此,兰兰是敢怒不敢言的。一说,婆婆就会扔下扫帚“哟”起来——“哟,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怕土?为啥不生在城里呀?为啥不当娘娘呀?为啥是个小姐身子丫环命呀?粘点土天就塌了?农民哪个不粘土?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怕土?到城里去呀?哼,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此外,婆婆还有一连串令兰兰大开眼界的手法。一是“抡”人。这个“抡”字有凉州独有的含意。要了解其含意还得加上凉州人常用的“呜呜闪电”。这一来,含意就明确了:“呜呜闪电地抡人”。见了你,猛转身,十分威风--“呜呜”;速度极快--“闪电”;猛给你掉个屁股——“抡”,蹬蹬蹬背你而去。这一去,也是“呜呜闪电”:腿脚格外有力,动作幅度机械夸大,每个部位每个细节都明显表示出对你的厌恶和不满。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招,婆婆常用,威力奇大。一则一家人,老碰面,此招时时可用。二则令你有口说不出个道道来,你总不能说婆婆不和你说话,走路快些就有罪了?兰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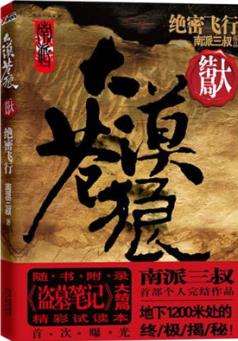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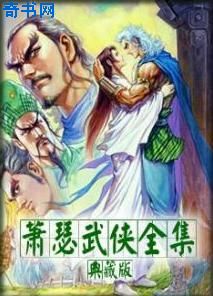




![[综漫]咎恶祭典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8/82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