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爹厚实的肩膀上,引弟晃势晃势地“走”着。她大睁着眼睛,新奇地看起伏的沙山,看蓝蓝的天,看撒在沙山沙洼间的一星星柴棵。好开心。但是一感到开心,引弟就觉得不对了:她的开心,是爹累的哩。
“下哩,爹。”她扭动着身子。
“咋?不好吗?”爹的声音闷闷的。
“好是好,可爹累。”
“不累。丫头,爹没好好地待过你。也怪不着你,谁叫你……,不说了,丫头,记住爹的话,别怨爹。”
引弟不明白爹的话。爹咋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呢?不就是打过我几巴掌吗?早不疼了,就说:“爹,你还给我买过方便面呢。你忘了?你真好……就是,以后,你不要打妈妈。成不?”
“以后?好。爹听你的话,不打了。”
(7)
日头爷悬在了最高的那座沙山上。几股子很红的光射来,连引弟的身子也染红了。
白福放下引弟,他的头上满是汗,眼窝里也是汗。引弟想,眼窝里咋也淌汗呢?她想起妈妈常说的“眼窝里淌汗,手心里起皮”的话,就想,背了我,爹可累坏了。
第十四章(13)
这是啥地方?引弟揉揉坐麻的屁股蛋子,歪了脑袋,四下里瞅。沙山,沙洼,沙米棵,黄毛柴……还有许多引弟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引弟终于记起来了:她跟顺爷爷来过这种地方放过羊,叫啥来着?对了,叫沙窝。可为啥灵官舅舅叫另一个名字呢?不知道。大人的事,小孩子少问,管他们叫啥叫啥去。
毕竟打春不久,天还冷得很。引弟的小脸蛋冻红了,小脚脚冻麻了,小手手被爹捏得死疼,但引弟还是很高兴。沙窝窝里好玩,不像村里,尽是坦土,多好的衣服也弄得土眉土眼的。这儿,打个滚啥的,也不会弄脏衣服。看看爹买的新衣裳,已有些脏兮兮了,那是村里娃儿摸脏的。沙窝里好,你想叫脏,都脏不了。引弟喜欢这“沙窝”。
白福蹲在沙洼里,木头一样,好久,才问:“引弟,天快黑了,你害怕不?……你自己说,你玩哩,还是跟爹回去?”
“玩哩,爹。你瞧,月亮牙牙。顺爷爷说,狐子就拜月亮牙牙呢,就是给月亮牙牙磕头呢,乓——,乓——,一个一个地磕头。顺爷爷说,磕几百年,就变成姑娘了,可俊呢。不知道有没有莹儿姑姑俊?”
白福于是望引弟。引弟觉得爹的眼睛很怪,怪得她都不敢望了。她想,是不是我又说错话了?这回,我可没说“刻”弟弟呀?爹为啥不高兴。但白福马上转过头去了,自言自语地说:“这丫头,看来,就这么个命了……也怪不得我。”
白福很快地起了身,下了沙洼。不一会儿,就拾来了一堆怪怪的东西,长长的,像黄瓜,好像哪里见过。引弟问:“爹,这是啥呀?”话一出口,却想起来了,和顺爷爷放羊时,她见过这东西,顺爷爷叫它“沙驴球棒子”。顺爷爷拿了一个,乓乓地敲。棒子就折了,里面也是沙。
“金子。”白福说。
“金子是啥?”
“金子?是啥呢?”白福皱了眉头,老半天,才说,“金子就是金子,比钱还值钱。指头大一疙瘩儿,买牛大一疙瘩钱呢。”
“比双福舅舅的还多?”
“当然。”白福奇怪地望引弟,“你也知道双福?”
引弟吐吐舌头,笑了。该不该把这话告诉爹呢?长大,她要挣比双福舅舅更多的钱,叫爹玩去,赌去,只叫你输。可爹,一输就不高兴了。爹不输,别人的爹就又不高兴了。这可是个难事儿呀。咋办呢?
“死丫头。”白福不问了。
引弟高兴了。以前,爹赢了钱,就这样骂她,然后才在她脸上吧唧。这次,爹没亲她,只望那堆金子。引弟想,这,能换来多少钱呀?莫非,也不用等她长大了?但引弟又疑惑了,既然有这么多金子,爹为啥老叫穷呢?就说:“顺爷爷说,这叫沙驴球棒子。”
白福吃了一惊,前后左右望了几眼,又怪怪地望引弟。
第十四章(14)
“这个……他们……那个当然是沙驴球棒子……这可是金子呀。”白福拣起一个,狠狠折断,寻了许久,寻出个针尖大小的亮星,说:“瞧,这就是。带回去,用水泡了,把泥清掉,澄下的,就是这。一撮,一撮,又一撮,就一大把了,用铁勺子盛了,放火上烤,一会儿就一大块金子了。”
引弟信了。她见过一个铸铝锅的,就像爹说的那样,用铁锅盛了铝,放火上,烧呀烧,一会儿就烧成亮亮的一锅“水”了,往模子里一倒,不一会,嘿,就成个铝锅了。
引弟想,以后,妈妈就不愁钱了。爷爷奶奶也不愁钱了,莹儿姑姑……好多人就不愁了。自己也不用长大了。天天来背这有金子的沙驴球棒子,背回去泡了,澄了,换了钱……引弟想痴了。忽然,她说:
“爹,你坏……”
白福吃了一惊,脸白了,又望望四周。
“你为啥……不早说呢,这么多金子。爷爷就愁不白头发了。”
白福不知说什么好,张了口,很蠢地望引弟。
“这……这……”
引弟拧了眉头,想一阵,才笑了:“我知道,人参娃娃……”
“啥人参娃娃?”
“这东西,也像人参娃娃。莹儿姑姑喧过的。人抓不住,一抓,嗖——,就不见了。只有好心的娃娃才能见到。对不对?爹。”
白福痴了,许久,才叹息道:“精灵鬼。丫头,你是个精灵鬼……你咋知道这么多,嘿,还真是的。”
“那我就是那个好心娃娃了。我抓了他们,他们会不会死?爹,你当那个坏人呀?”
“哪能呢?他们多孤单呀,瞧,这儿又冷……那个……带回去,洗了身上的脏东西,他们才俊呢。”说着,白福懊恼地晃晃脑袋。他望望悬山的太阳好大会子,嘴里咕咕哝哝,不知说了些什么。
“带红头绳没?”引弟问。
“干啥?”
“拴呀。那人参娃娃不拴,嗖——就不见了,红头绳一拴,他就跑不了。莹儿姑姑说的。这金子娃娃,肯定也这样。”
“……也好,丫头,我去取红头绳,你就看着他们,别叫跑了。成不?”说着,白福忽然哭了,牛吼一样。
“丫头,我不是人……可……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
引弟吓坏了,小心地望一眼爹,说:“爹,我又没说不看的话。爹,你放心去,我……哪儿……也不去。”
第十四章(15)
(8)
夜幕降临了。
沙山上很红的几抹光也叫夜气淹了。空气变成了凉水,漫过来,荡过去,不一会,引弟就打哆嗦了。爹穿走了他的大棉袄。是引弟硬叫穿的,爹拧了一会儿眉,就穿了。引弟的牙齿虽然打架,可她想,爹不冷就好。爹多好,爹给我买方便面呢。那么好吃的东西,香到脑子里去了。引弟笑了。引弟觉得笑起来没平时那么顺溜,牙巴骨似乎有些硬了。
月牙儿挂在天上,像一块冰。引弟望一阵,想,月亮牙牙是不是也在等他爹,等呀等,等不到,就哭了。瞧,那泪珠儿就成星星了。引弟就想,月亮牙牙好可怜,流了那么多眼泪,变了那么多星星。
可为啥莹儿姑姑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星星”呢?也许,莹儿姑姑是对的。莹儿姑姑没骗过引弟,引弟信姑姑的话。那么,妈妈是哪颗星星呢?灵官舅舅是哪颗呢?莹儿姑姑是哪颗呢?她肯定是最漂亮的那颗。爷爷奶奶肯定是老星星了。星星老了,一定就长胡子了。引弟想,扫帚星可能就是长胡子的星星了。
奶奶老在背后骂妈扫帚星。引弟心里说,奶奶,你才是长胡子的扫帚星呢。她笑了。
引弟就一个个给星星安名儿了,这是妈妈,这是灵官舅舅,这是莹儿姑姑,这是顺爷爷……,到后来,星星就哗哗哗地乱跑了。引弟的眼就花了。她想,你们跑啥呢?是不是也像人那样串门呢?对了,人一串门,他的那颗星星也就动了,你来我往的,不乱才怪呢。
望一阵,引弟又觉出了冷。脚冻木了,她就跺脚。身子也煞凉煞凉的,她就使劲地跳,边跳边安慰自己:爹就来了,你急啥哩。爹走路快,一蹿,一截子;一蹿,又一截子。她甚至“看见”了大步流星的爹呢。
(9)
望望脚下的一堆“金子”,引弟很高兴。不管咋说,爹总算找了这么多金子,带回去,化成泥水,怕能澄好厚一层呢。妈妈该多高兴呀。引弟想,爹带我来,一定是因为我是个好心的孩子。那个坏人抓人参娃娃时不就用那个好心娃娃吗?想到这里,引弟有些内疚,觉得自己对不起金子娃娃。他们肯定也和人参娃娃那么好。放火上烤,他们疼不疼呢?一定疼的。一次,一个火星迸到她手上,她疼了好几天呢;就又为金子难受了。她想,还是别烧了,就这样卖了,少卖几个钱也成,叫金娃娃少挨些疼。
风大起来;欧欧地叫着,卷向引弟。她连气都出不来了,她打个寒噤,使劲裹裹衣襟,可仍是冷。引弟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忍了又忍,才没有哭出声来。引弟抹把泪,四下里望望,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可又怕这些金娃娃跑了。他们会不会跑呢?说不上。引弟觉得自己的心已“坏”了,有“贼”心了。金娃娃早知道了,他们肯定要跑。一跑,爹又要不高兴了,爹又要蒙头睡了,爹又要打妈妈了,爹又要喝神断鬼地骂奶奶了。引弟说,金娃娃,委屈一下吧。我不好,可……,可……,我们是朋友,帮帮我,成不?引弟看到金娃娃笑着点头,引弟就笑了。
“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她想。
爹还是不来。
臭爹。
第十四章(16)
引弟快冻僵了。引弟的脸上有针扎了。引弟的小手冻木了。引弟的身子冻成冰棍了。她把小手放到嘴上,不停地哈气,可还是冷。引弟想,怕是快成冰棍了。想到冰棍,引弟又想起了村里学校门口的那个卖冰棍的。引弟一直没吃过那白白的、或是黄黄红红的冰棍。啥味道呢?引弟想疼了脑袋,也想不出冰棍究竟是啥味儿。这下,引弟明白了,它一定是手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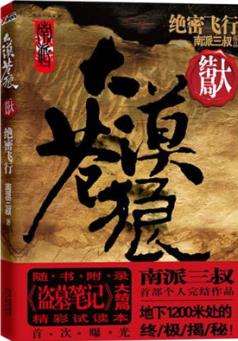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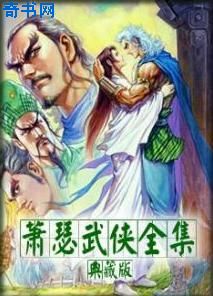




![[综漫]咎恶祭典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8/82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