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1)
灵官把骆驼拴到黄毛柴棵上不久,天就黑了。从晚霞满天到黑气沉沉的过程赶趟儿似的快,仿佛真有个叫夜幕的玩艺儿降了下来,瞬息间便遮住了眼前的一切。灵官点着了马灯。昏黄的光照在那只熏得比夜色更黑的锅上。做好了半锅面片,他开始焦急了。昨日此刻,他和孟八爷已回到窝铺,今日怎么了?莫非迷路了?一想到迷路,灵官笑了。因为孟八爷老说对沙漠的熟悉程度超过了自己的掌纹。但他也说过,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决不追赶使自己在日头落山前还回不到窝铺的狐子。尤其在冬天。要是出发时忘了带火,那么,到不了半夜,大漠冬夜独有的酷寒便会把违背规则的生灵们变成冻肉。
大漠祭 第三部分 大漠祭 第四章(1)
灵官担心的当然不是他们会变成冻肉。这时节,既使露宿沙海,也不过受寒而已。他担心的是“有经验的猎人”没有在日落前回到窝铺的那个不明不白的原因。他怀疑问题会出在花球身上,很可能他跑不动了。花球是个没长劲的调皮骡子,出去时蹦蹦跳跳,有兴头得很。回来时,难说。他是那种多少有点疼痛就龇牙咧嘴哎哟呻唤的货。肯定跑不动了,拖累了孟八爷。肯定。灵官眼前出现了龇牙咧嘴一瘸一拐的花球,拄着枪,像电影里的******伤兵。哎呀,灵官的心里抖了一下,柱着枪吗?他忽然记起父亲喧过的一个猎人柱着枪上坡时弄响了枪一命呜呼的事,觉得花球也会干那种蠢事。会的。累极了的时候枪托柱地,枪口朝上,轰--,便倒下了……可没有死,在血里滚来滚去……灵官感到胸部很闷。孟八爷咋办?按理说,他会慌里慌张,跳来跳去。可灵官却想不出他咋个慌里慌张。从没见过孟八爷慌张,仿佛他生来就成竹在胸,早知五百年的事……想来想去,倒想出了他跳来跳去的样子,只是不慌张,倒老顽童似调皮。荒唐。灵官笑了,中断了这个联想。
该来了呀?他抬头望望天。天异常的黑,仍像个巨大的黑锅扣在大漠上空。没戴表,也不知啥时候了。理智告诉他刚入夜,感觉上却过了半个世纪。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落到烽燧墩那边去了。他马上想到那个姑娘,心暖暖地荡了。他拚命去想姑娘的脸,但大脑的荧光屏黑漆漆的,不显一点儿图案。记得他当时留意地打量过几次,记得她很清秀,爱笑,鼻头有点翘,可他死活想不出她笑的模样和清秀,甚至想不出鼻头翘的样子。倒是那倔老头的吊死鬼脸却摇摇晃晃进了脑子。扫兴。灵官晃晃脑袋,倔老头的脸才像水面上被风吹碎的月儿,模糊成一层亮雾了。
她在干啥呢?灵官站起来。明知道望不见啥,却依然朝那个方向望去。睡了,肯定睡了。不睡又怎样?遇了那么个榆木结疙瘩一样的爹,又能浪漫出个啥情致?那可真是个老脑筋败兴鬼呀。对,败兴。灵官笑了,真败了人的兴头。啥兴头呢?喧的兴头?没咋喧呀——可又像喧了许多。他仔细地品味着她的每一句话。她的模样不清楚,可话清楚,一字一句都清楚。尤其那独特的憨实中透出婉转柔和的古浪口音,像一粒粒水豆子敲打着灵官的心。她还给了他一个山芋呢。那么香。从来不知道山芋竟会那么香。真剜了那老败兴鬼的护心油了。他说啥来着?“想吃就吃”?当然想吃,而且……而且……嘿嘿……“高不过蓝天美不过酒,甜不过我尕妹的舌头。”哎哟,灵官笑了。
忽然,脑中有根蚕丝似的东西晃了一下。他想不起来,但感觉到确实还有个啥活没干。他拧着眉头,就着马灯昏暗的光亮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帐篷,在夜色下像童话中女巫住的小屋。饭,已经做好,肯定凉了,而且泡成面糊糊了。水,拉子,提包,纤维袋子……他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一堆柴上。对了,他终于记起来了。孟八爷走的时候叫他放火,到一个高高的沙丘上。
哎呀,灵官叫了起来。他懊恼地拍拍脑袋。夜这么黑,你叫人家到哪儿找窝铺?真吃猪脑子了。幸好记起来了,不然……嘿!他飞快地把柴抱到一个高沙丘上,点着。火苗儿腾起来了。他喘着粗气,提着马灯,又砍了许多黄毛柴,抱到沙丘上。他得有充足的柴。这个火熄不得。他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走到能看清火光的地方。要是他们一夜不来,他得叫火燃一夜。
天凉了下来。大漠的气候更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昼夜温差极大。灵官胸前虽被火烤得暖烘烘的,脊背却感到冰凉。他也懒得去加件衣服。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掉过身去烤烤脊背。
夜风像寒水一样流了过来,火苗被吹得呼呼直叫。灵官换个角度,避开被夜风裹带来的呛人的烟。因为夜黑,他顾不上选柴的干湿,砍来的柴中一半是湿的。湿柴滋滋地叫,为单调寂寞的夜添了一些悦耳的音韵。灵官发现湿柴的好处,不容易着,但一旦着了,却耐,燃的时间长。不像干柴,呼呼呼几下就成了一堆灰烬。
不知过了多久,灵官听到了人声,隐隐约约,很远。可能来了,他想。他离火堆远了些,不使那呼呼滋滋声干扰自己的听觉。果然,他听到了孟八爷独有的理直气壮的咳嗽,心才稳稳地回到肚里了。他往篝火中丢几根柴,提马灯,下沙丘,把锅搁到挖好的灶炕里,点了火。锅里开始响起了咕咚咕咚的声音。不一会,孟八爷的声音传了过来。
“又吃猪脑子了。是不是?多走了至少十里路,走偏了,走过了。要不是看见火,真要走到天亮。”
灵官从孟八爷的声音里听出责备的成份少,喜悦的成份多,就断定他们收获不小。果然,两人肩上各扛一个狐子。
“没剥皮呀?”灵官问。
“顾不上。”孟八爷笑道:“打了一个,想回,可又发现一个踪踪子。就想,打上算了。撵到日头爷悬山子,总算撵上了。”
花球闷声不响,把狐子扔到地上,一屁股坐下,塌了架似的。
“真是个驴死鞍子烂了。啊?”孟八爷笑道:“一个小伙子,跑这点路,就瘦狗努尿似的。老子十七八岁时,扛个梯子,跑几十里路,到凉州城里嫖个风,赶天亮回来,还要上地干活呢。嘿,现在的年轻人。”花球一听,索性躺倒了。
灵官舀碗饭,递给孟八爷。孟八爷仍旧搁在沙上,取出烟锅,吧哒起来。吸几口,吹一下。红星划弧,飞出老远。
灵官又给花球端过一碗,喊他,不动。他已经睡着了。
大漠祭 第三部分 大漠祭 第四章(2)
(1)
上粮,是农民一年的大事。向国家交的农业税,和乡上征收的各种费用,都用上粮的方式来交付。其程序说来简单:验粮,过称,结帐,领款。
粮站上很乱,尽是人,尽是车。加上人的嚷嚷,驴马的嘶鸣,机动车的咆哮……把个敞大的粮站撑得窄小了许多。老顺是最怕进粮站的,从心底里怕。不仅怕粮站上工作人员的吆喝,还怕粮站的那种气势。进了那个水泥砌的足有几十亩地的晒场,老顺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不由得产生无助的恓惶。最使他感到挤压的是粮垛和粮堆。那清一色装满粮食的麻袋足有几十丈高,看一看都眼花。还没装成的粮像山——那可真是山呀——老顺每次抬着斛踏上颤微微上下晃动的木板时,就会想到村里那头在西山上滚洼而死的青犏牛。
老顺因此得出个结论:粮不值钱,是因为太多。物以稀为贵。要是农民都不卖粮,粮价肯定涨。于是,他开始看不起那些像炭毛子驴那样急匆匆上粮的农民,而忘了自己一点也不比他们落后。
“哎——,到这里来。”循声望去,是白狗北柱他们。
“有地方吗?”老顺问。
“有哩。”
老顺打量一下四周,发现驴车是过不去了,便抛下缰绳,抱起一个细些的袋子,从人缝里挤过去。憨头迟疑一下,也抱一个过去了。
白狗占的地方很好,一是离秤近,二是离粮堆近。秤起来方便,抬起来也省事。老顺放下袋子,喘着气。白狗笑了:“行了,你歇着,我们来。”与北柱过去,三下五除二,把粮搬过来了。
北柱问:“就这些?”
“还有一趟。”老顺说。
“哟,这么多。吃亏哩,价这么低。你不等涨价了?前天,铁门来了个起刀磨剪子的,不要钱,要粮。不是现在要,要等到粮价涨到一块的时候才要,听说不?”北柱说。
老顺说:“谁都那么说。谁知道呢?唉,不长成一块也得活呀,没钱总不成呀。白狗,你爹也不粜粮给你说媳妇?”
“我还想多蹦哒几年呢。娶个婆姨上个绊,养个儿子套个罐。我才不干呢。”
憨头不声不响地赶着驴车走了。老顺腿有点困,就坐在粮袋上。这时,各种声音又钻进耳朵弄大他的脑袋。他看到两个男人为了争斛一扑一张的,像斗鸡。“无聊。”老顺想,“真无聊。早抬一斛晚抬一斛有啥关系?粮又少不了一颗,争嚷啥哩?死神催住脚把骨了?真是。”他又看到一个老汉和一个姑娘抬着满装粮食的斛上了粮山。脚下的木板颤着,他们的腿也弹簧似的。老顺真为他们捏把汗呢,心差点从嗓门里跳出……他又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操一个小伙子的妈”,三条大汉扑上前要打他。干部气势汹汹地问:“我没骂你们,你们干啥?”大汉说:“老子们是亲兄弟。你敢操他妈,我们就敢揍你……”老顺笑了。
忽然,他听到白狗压低的笑。转过头,见北柱正和白狗抬着一斛粮食过来,放在他的粮袋旁。他张嘴要问,北柱却挤挤眼,白狗正警觉地望过秤人。
老顺明白了,这帮家伙原来不学好,竟干这种勾当。听人说过,有人在粮站上捣鬼,把上过秤计过斤数的粮斛又绕个圈子抬回来,再过,再称。一斛粮食能卖个十来八斛的价。他不信。粮站上的人又不是吃屎的,能叫人喂抓屁。可现在,不由他不信。他望望白狗。白狗的脸虽然有意绷得很紧,但掩饰不住肚里的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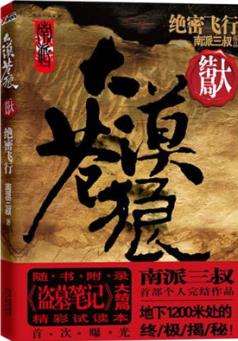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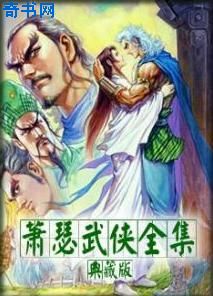




![[综漫]咎恶祭典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8/82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