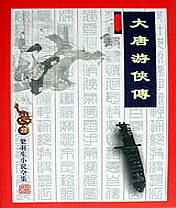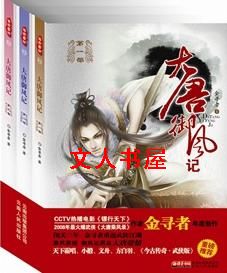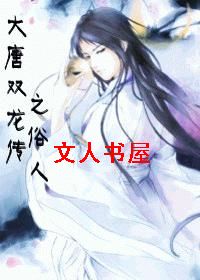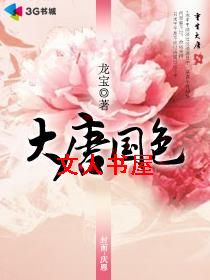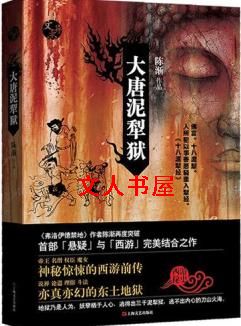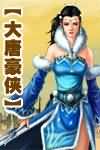显耀大唐-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何能自降身份,亲临下邦小国?更何况陛下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若是到那苦寒之地,一旦病情加重,岂非我大唐之大不幸哉?微臣忠直之言,难免冲撞,还请陛下恕罪。”
许敬宗这么一说,王德俭、袁公瑜、侯善业等武后党人也都纷纷附和,有过激的甚至以头戗地,磕得头破血流。
许敬宗当然不仅仅是关心高宗身体那么简单,而是关心高宗亲至辽东后是否会乘机控制军权,所以这才竭力劝阻高宗。
而接下来更加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帝党的刘祥道等人竟然也随之劝阻高宗,他们既担心高宗的身体状况,同时又担心在高宗离开之后,武后会乘机对付他们,所以也是附和许敬宗的意见,死命的劝阻。
许多年以来,朝廷百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竟然出奇的意见一致,而且还是连续两次!这样的一幕绝对是创造了历史。
就在群臣一致反对的声音下,高宗那意气风发的神情终于被打消了,可是他却仍然有些不甘心,还打算来个一意孤行,却没想到武后也当面谏止,并罗列了一大堆理由,比如高宗身体不好,比如御驾亲征规格太高,高句丽不配,比如皇帝亲临容易干涉军政,不利于战争等等。
不管这些理由是不是牵强,总之武后的态度已经亮明了,群臣也都是一副高宗不同意取消御驾亲征便誓不罢休的态度,高宗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心中开始动摇了起来,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便对一直沉默不语的李绩问道:“李爱卿,依尔说,朕是否当亲征高句丽?”
却听得李绩缓缓上前,躬身说道:“微臣以为,皇后殿下与诸位同僚所言不错,陛下乃万金之躯,实不宜出征高句丽,然则微臣亦深知陛下之意,以圣驾亲临北疆,鼓舞军心士气,三军将士用力,自可一鼓作气,攻下高句丽,故此,微臣以为,莫若采取一折衷之办法,陛下委派一位皇子代替陛下出征高句丽,如此一来则鼓舞士气之目的能达到,陛下亦不必受舟车劳顿之苦。”
“爱卿言之有理,便是这么定了。”高宗见李绩给自己找了个最好的台阶下,自然是满口答应,不过他随即又问道:“可是朕又该派哪个前去北疆耶?李卿可有人选?”
李绩却是微微躬身道:“郇王素节向来聪慧,又是陛下亲子,臣闻彼最近又作《忠孝论》,想来忠诚可嘉,不如便派郇王代陛下前往高句丽,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郇王李素节是高宗第四子,母亲是萧淑妃,乃是高宗诸子之中,最令武后讨厌的,李绩提出这个建议自然就是在等着后党众人否定的。
果然,李绩刚刚说完,便听得西台舍人袁公瑜上前说道:“陛下,老臣以为此事不可,老臣向闻郇王身体不好,前一段时间陛下还关照郇王,令其不必频繁入宫朝见,如此说来郇王之病应当不轻,既如此,又如何能代陛下出征?”
“既如此,那杞王上金如何?”李绩假装皱眉,然后提出了高宗另外一个儿子,向高宗问道。
到目前为止,高宗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其中长子李忠被处死,次子李孝病死,剩下的也就是三子李上金最大了,可是由于并非武后所出,所以甚为武后厌恶,虽然此子身体素质和能力都可以担当这次代替高宗出征的重任,后党众人也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万一此人借此掌握了兵权,岂不是武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所以,李绩的提议自然也遭到了后党众人的一致反对,甚至连武后都亲自出面否决,理由很简单,李上金并非高宗嫡子,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众臣见高宗仅存的两个庶出儿子全被否定了,那么剩下的也就是武后所生的四个嫡子了,而在四个嫡子之中,李弘是太子,自然不可能冒这种风险,而豫王李旭轮又实在幼小,所人选就只能在沛王李贤和周王李显之中选出一个了。
而在大多数大臣的眼中,这一次被派往北疆代替皇帝出战的,定然是沛王李贤无疑,毕竟李贤自幼就有贤德之名,再加上年纪比李显大两岁,相对也更合适一些。
所以这一次不待李绩再说,便有大臣举荐沛王贤,而这个举荐者,乃是帝党之首刘祥道。
这并非是刘祥道讨厌李显,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认为李显年纪有些小,不太适合,同时也知道李贤和武后关系不好,便想着让李贤借机掌控一部分兵权,以制约武后的野心。更兼刘祥道过去曾做过沛王府长史,与李贤关系甚好,想着等到此事之后主动与李贤联系,联合太子共同制衡武后,或许能够遏制武后的野心,令高宗更加好过一些。
可是武后又是什么人?她怎能眼睁睁看着权柄落入与自己一向不和的李贤手中?所以便示意许敬宗带头反对。
许敬宗乃是武后的心腹,自然深知武后之意,当先便带头反对道:“微臣以为不可,沛王虽贤,然而性情太过刚强,于征战或许无碍,然则此次征战高句丽,须当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以剿为用,周王性情柔顺随和,更加适合。”
“不然。”刘祥道当即反驳道:“许相虽言之有理,周王亦甚贤能聪慧,然则周王年纪尚幼,读书又是不多,恐难担此重任,沛王虽性刚,然则颇通经史,又素来仁爱,只需陛下派遣一老成持重之士佐之,定能圆满完成陛下所托。”
这时候却见详刑寺正侯善业冷笑着说道:“如此说来,刘公是嫌周王年纪幼小、文采不好了?然则刘公莫非不知,周王年纪虽幼,却是身高七尺,比沛王还高出半头,不仅武艺出众,文采更是非凡,如何去不得北疆?”
“呵呵,莫非是道听途说乎?吾可是听说周王这几年来只懂舞枪弄棒,不喜读书,不著经史,尔说周王文采非凡,不知有何证据?”刘祥道一向瞧不起靠溜须拍马而得富贵的侯善业,如今见对方竟然用如此啼笑皆非的问题诘难自己,不由得哑然失笑,开口驳斥道。
但见侯善业一脸不屑地说道:“下官本以为刘相身为司礼太常伯,当朝宰相,定然对天下许多大事尽皆知晓,如今看来,实在是名不副实啊。”
“尔此言何意?”刘祥道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对方如此鄙视,不由怒气渐生,沉声喝问道。
只见侯善业呵呵笑道:“刘相之前为沛王府长史,如今想办法为故主多谋些功劳,下官亦理解,然而刘相却不能因此而随意污蔑周王啊,刘相岂不知,数年前,周王仅仅七岁,便做出一首诗,此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却又工整,写景抒情完美交融,意境浑成,堪为绝唱,如此诗作唯有大才者方能作出,如何被刘相称作读书不多?”
“哦?不知是何诗作?竟然被尔如此推许,本相倒是想要领教领教。”刘祥道早已见惯了这阿谀拍马者的嘴脸,所以自然是不大相信,于是冷笑着问道。
却见侯善业也不着恼,缓缓念诵道:“诗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狂生去,萋萋满别情。”
刘祥道闻言一愣,随即哈哈笑道:“尔说甚?哈哈,真是可笑,这首诗乃是最近流行于文坛之内一首绝品佳作,据说乃是一位神童所作,尔竟然将这首尽人皆知之诗作推到周王头上,亦不知是成全了周王还是害了周王乎?”
却听得侯善业也是嘿嘿冷笑道:“这歌刘相恐怕就有所不知了,此诗乃是周王当初戏弄一位狂生所作,只不过当时周王乃是微服出访,未免麻烦,故此才未透露身份,此事当时李公府上长孙敬业亦在场,公若不信,只问李公便是。”
第64章议征高句丽(四)
“李公,此言果当真否?”刘祥道听了侯善业的话,心中还是有些不信,便转过头来询问李绩。
只见李绩点了点头说道:“确实不错,当初我那不孝孙敬业便在周王身旁,其时敬业与李义府之子李湛正在酒楼之中吟诗取乐,一位狂生口出不逊,言道彼等所作之诗犹如狗屁,敬业等不服,便令对方亦作一首,不料那狂神出口成章,诗曰,行止皆无地,招寻独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露白宵钟彻,风清晓漏闻。坐携余兴往,还似未离群。其实这首诗之文采亦不俗,怎奈这狂生口出狂言,引起周王不满,便与其比诗,那狂生见周王年纪幼小,要求周王只需胜过敬业等便可,于是周王口占离离原上草,狂生拜服,乃退。”
“原来此事竟有这等原委,只是不知那狂生可留下了姓名?如今正在何处?”刘祥道闻言顿时感兴趣,连忙问道。
“此人名叫杜审言,祖籍襄阳,后迁至巩县,据说乃是晋征南将军杜预之后,历次参加科举,却因李义府等权臣阻挠,多次未能中举如愿,至于其如今所在,李某亦不清楚。”李绩抚了抚颔下长髯,轻轻叹道。
“唉,有李司空作证,下官亦不敢不信周王具大才,然则李司空认为周王堪任征战高句丽之诗否?”刘祥道现在没有了办法,只能妄图借李绩之口来否定李显。
却听得李绩说道:“此事李某如何敢评论?自有陛下与皇后殿下圣裁。”
以李绩的老辣,自然不会自己明着推荐谁,但是他现在根本就不用说,大家都很明白一件事,能有这等才华的李显,当然能够轻松胜任安抚之责,而至于武略么,大家彼此比一下身体素质就可以了。
更何况李绩也知道武后心中会向着谁,以李贤和武后之间这种关系,武后除非是疯了,才会同意让他去,而高宗这懦弱的性子,在大事上一向是唯妻是从。
所以,李绩这话一说完,其实已经代表着今天的事情有了定局,那就是,最终的得胜者一定会是周王李显。
果然,经过武后与高宗的一番低声商议,最后高宗决定:“以周王显为右武卫大将军、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代朕出征高句丽,以英国公、司空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长史,总督辽东诸战事,又以司列太常伯郝处俊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又诏令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由积利道,刘仁愿由毕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