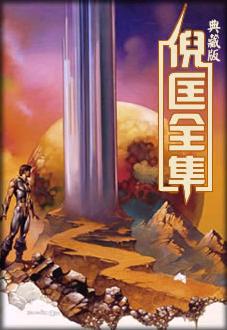尘世间-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廓,透着隐隐的暮气。他伸手抚一下脸颊,那面孔上的沟壑一日深似一日,他蓦然发现自己已然是个六旬多的老人了,那满头的花发在发根处浅浅展露出银亮的迹象——那是府里打理头发的匠人专门为他染就的,可再怎么染,总也遮不住那奋勇争先、独占鳌头的发根儿。
他不禁唏嘘,悠长的叹息静默着穿渗出墙壁去,贴着一阵疾风,盘旋着激起了树枝上的鸟,也将激荡起这世间未知的命运。
有人来回禀道:“原御前孙大夫来看过了,说四少的病并无大碍,不过是长期劳累兼之急怒攻心,导致的浓痰淤堵了肺窍。不过吃上几服药,调养一段时日,便可望好。”
他听后顿时放下心来,对着玻璃上自己的身影苦笑一番,便敛起衣袖,坐在案桌前,缓缓地提起笔来,那手腕却忍不住微颤着。有小丫头子过来研磨,那徽墨在砚台中轻微的厮磨着,墨汁在水中洇开去,一分一毫的吞咽着。那笔尖刚落在纸上,手微微一抖,一滴墨滴落在铺好的宣纸上,如此触目分明,他将笔搁回在那笔架上,猛地将纸张拽在手里,几下撕了粉碎。那小丫头子不敢说话,研完墨便小心翼翼的退了出去。他沉默良久,又缓缓地展开一张新纸,将笔拿在手里,深吸一口气,极慢的写下一个字去。那第一个字纵然带着犹豫,但之后便行云流水写就了一番。写完后他又细细看了一遍,从贴身的绣囊里掏出了一枚已经磨没了棱角的滚圆田黄寿山石印章,在旁边印泥上使劲摁下去,又重重的印在了纸上。他本要将那印章再仔细的收起来,可是转眼一想,这张纸今日若是传了下去,他这印章还能有什么用处?他想到这里,索性将那印章随手扔在案桌的一角,长身而起,双手拍拍身上的长袍衣襟,只觉得无比轻松起来,甩手走了出去。
陆少倌醒转来的时候,老太太正坐在他床前的榻上静静垂泪。房间里正点着檀香,细细嗅来,是上好的红皮老山檀碾成的细碎的屑,气味沉静甜郁,那抹子香甜直直的飘到人的心里,一丝一缕的晕散开,如云雾般一丝一缕的沁进去,让人觉得安逸许多。
陆少倌睁开了眼睛,看到老太太正在身前,忙费力的开口叫一声:“奶奶。”
老太太看他醒了,只觉得满心欢喜,可是那泪水更加汹涌出来,她忙握住他的手,只是任着那泪水落下来:“好孩子,你终于醒了,你再不醒,可就要了奶奶的命了!”
陆少倌看她如此伤心,辗转联想到心事,也忍不住眼圈红起来:“孩儿不孝!”
老太太忙去颤巍巍的掏出身上衣襟里别着的苏绣手绢,帮他擦拭着泪:“你是好孩子,你是好孩子,你拿命去做大事,却把自己带累成这样,奶奶心疼啊,你娘去的早——”说到这里,语气更是哽咽起来,旁人想劝却都不敢劝,早就有人出去请当家的二姨太。
老太太抽泣一会儿,只看着陆少倌眼睛含着泪,目光却只凝伫在那床幔垂着的烟青色穗子上,不言不语,便忙敛了伤心,絮絮的问起他在外面的事情来。这一问,陆少倌更想到了前尘往事,他心中大恸,只觉得一股子温热直涌上来,他拼命地去压制,却怎么也压不住,终于那温热喷出来,老太太只觉得眼前一红,再定睛一看,之间那枕边的床幔上赫然是一口鲜血。
陆少倌只觉得迷糊起来,他喉咙翻滚着,直直的喊着:“快叫人来,去灭了那匪徒,灭了那匪徒!”整个人在床上佝偻起来,翻滚着,像只虾子,却怎么也摁不住。
她唬得直叫了大夫来,那大夫本来也没有走远,忙又匆匆的赶过来,略一评脉,只是捻着胡须沉吟道:“少倌体内沉郁甚重,怕是心情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如此,我便再加几味安神的药罢,只是病人自己还要放宽心才好。”他不过略施了些针法,那陆少倌便缓缓地回过神,心内慢慢澄明起来。
大夫走了以后,老太太的表情敛然沉静,她吩咐一声:“都出去吧,我要与少倌说话。”
下人们全都悄悄地退出去,留下一室静谧。
老太太凝视着少倌,那眼神透亮豁然:“你如今年岁大了,我也在后面呆久了,前儿我突然想起来,你旧日里跟着师傅们读的《大学》,日常里常念给我听的那几句,可还记得?”
陆少倌见她目光里皆是炯然,便说道:“孙儿记得。”
老太太转一转手中的佛珠,道:“那你再背给祖母听听。”
陆少倌嘴角沉重,却又极缓的念出来:“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
老太太笑一笑:“难为你还记得。你自幼母亲去的早,养在我膝下,素日里我教导你,用尽了我的百般心思,你是知道的。”
陆少倌的语气平和,听不出任何的涟漪起伏:“孙儿自幼多得祖母教导,感铭在心。”
老太太点一点头:“你是个有孝心的孩子,我心里是明白的。你们这些孙子辈的脾气性格,我都是清楚的,你是嫡出,也是我孙子辈里面最喜爱的一个。平日里他们背后说我偏心,我只当没听到,我这把年纪,何以还用看旁人脸色过日子?可是,孙儿啊,如今你祖母却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了。”
陆少倌躺在床上,听闻此话,惶恐入心,忙要从床上坐起来磕头,却是怎么也挣扎不动,那整个身子都是昏沉的,像是身上压住了一块千百斤中的大石,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他这一番挣扎着实用足了力气,一口气噎住便气喘的厉害。他轻咳着说道:“您这样说,岂不是将孙儿放在油锅上煎?”
老太太忙摁住他,淡淡笑着,用一只手沾一沾眼角的湿润:“你原也不用这样激动,你心里藏着的事,我是知道的。那报纸上写的那样清晰:少夫人亦英雄,这少夫人是谁?我们离得再远,也都打听得明白了。你父亲虽然未说什么,他心里也是默认了的。她既然在咱们府上住过一段时间,我也是见过她的。那个孩子我当日看着就是好的,长的细发白净,看着温顺,但眉眼里也有着倔劲儿和灵透,我心内是喜欢的,原说要给她做个媒人,没想到你们两个却走到一起。你们在前面打仗的时候,我也找人打听了下她的家庭,虽不是什么大门大户,但也是规整人家。我心里虽然觉得你娶她,身份上是委屈了点的,但你们两人情投意合,我也就存了成全你们的心。可是昨日看你这样回来,我便找了黄宁来问,黄宁便把前因后果细细的告诉了我。孙儿啊,她竟然做出这样的背叛之事——”
陆少倌忙着急的打断她:“奶奶,她原是为了义气——”
老太太的语气陡然森冷起来:“不管她为了什么!但她既然已经跟了你,就要跟你是一条心。如今却做出了偷用印章、私放匪徒、投奔草寇的事情,纵然有再多的隐情,你俩也是不成了的。”
陆少倌紧紧地攥住手边的一条幔子,嘴角强挤出一点笑意:“奶奶,她虽然做了这些事,可是她最后随了那匪徒走,亦是为了解孙儿围困之难。”
老太太冷冷的笑一下:“若不是这最后一步着实救了你,我也不会与你说这么多劝慰的话了。你若是有什么差池,我早已经让你父亲出兵去剿了那齐匪的老巢。我要把那孩子带到跟前来好好问问,我陆府上下哪里对不起她,让她死也能死个清白。”
陆少倌心中大恸:“奶奶,那土匪灭不得,你不要派人去,我不要让她死。”
老太太沉声道:“你刚刚不是还叫着,要让人去灭了那匪徒?”
陆少倌心内像是有无数的蚂蚁啃噬:“孙儿、孙儿原也说的不过是气话。”
老太太眼神微敛,一字一句的缓缓道:“你也知道你说的是气话!那些匪徒原本就是些流离失所的贫民聚集而成的,纵然亦有可恶者,咱们各地军阀间亦有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不作乱,我们便容得他们过活。现如今你若是为了她去剿灭那帮山匪,岂不是落得剿杀百姓之名?将来你何以立足于世?你父亲这千秋大业如何才能安心交予你?更何况,现在赣地刚定,东北虎视眈眈,南方动作不断,你却要分了神,为了一个女人,巴巴的大张旗鼓的剿灭一帮山匪,这要是传出去,于天下人岂不是笑话?这天下难道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陆少倌在枕上费力的仰起脸来,那眼角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她心如刀割,那手背因为使劲泛起了请进,四肢百骸连同五脏六腑都麻木起来。老太太的这些话就如刀子一样锋利,将他心里的伤痛剖开来,他不想听,也不要听,可是哪里由得了他?那一字一句,虽然轻声细语,但却字字千钧,只压得他动弹不得。他哀声泣道:“奶奶,她不是别的女人,我只要她。她不是这世间最好的,可是她就是孙儿心里想要的,是孙儿心头上喜欢的人啊。别人我都不要,我只想要她啊。”
他长这么大以来,从来未曾这样失态,那哭声像个年幼的孩子,老太太看在心里,只觉得心内无比的怜惜:“孩子,今日我也把话放在这里,她纵然回来,也是进不得咱们家门了。我唯一能帮助你的,就是告诉你父亲,以后见了她,不与她为难。”
陆少倌心里清楚的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可是他的心依然如被撕扯成了千百条,静静的垂荡在那里,每条缝隙里都吹过簌簌的风,那血和肉僵冷起来,竟像是一块被冰冻住的坚硬石块,触手冰冷。那屋里温暖和煦,如春天一般,可是却没有一丝热气能渗进这石块里。
他侧转身子,伏在那里痛哭起来,那宽厚的背部轻轻颤抖着,犹如一只受伤的烈兽,只能将最悲伤的心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昔日种种,皆落入前尘,来日碌碌,皆恍如新世。那些逝去的光阴,到头来都是枉然,肝肠寸断,却生受着今生无缘。无穷无尽的悲凉袭上来,他清楚的看见了自己,数十年后的自己,孤独的漂浮在那岁月酝酿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