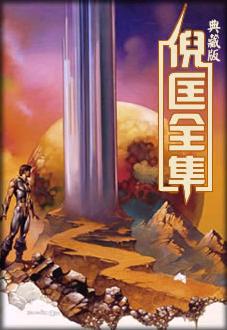尘世间-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伸手来握住她的手,两人并肩站在亭子边上,借着灯光,在月色下看向这浩瀚清波的湖光山色。
此情此景,亦真却突然想到了《玉簪记》,她不禁叹口气,声音有些飘渺:“帘卷残荷水殿风,人在蓬莱第几宫?”
陆少倌闻言,笑答道:“闲庭执手看明月,私语应胜玉簪情。”
亦真掩口而笑。
突然间,亭子里的灯光暗了下去。只见那远处的湖水中缓缓升起了点点繁星似的光亮,辉映着湖中娇艳的荷花,细细看过去,那些光亮竟然是一行大字:灼灼吾心,此生不离。
亦真看得有些震惊。
陆少倌低头看着身侧的她,眼睛里满满都是爱怜
亦真轻挽的发丝被风吹散,有一缕长发带着清香的味道,随着风儿挑出了发梢,直抚过他的眼睛。
他像是看不够似的,笑道:“山为媒,水为证,你我良缘,缔结于此。”
亦真心里受了极大地感动。她断没有想到,少倌竟有如此的布置。
她侧头看向身旁的人儿,眼睛里闪着星子般的光芒。
两人就这样带着沉静的欢喜,静静的站着,唯有那手与手指尖的温度,传递着无限的轻易。此时,他们唯愿就这样一直两两相望下去,直望到那天长地久去。
在人生的很多时刻,人们恨不得一夜白首,才对得起自己当时许下的誓言。他们的初心是那样的美好纯净,然而夜长梦多,世事多变,结局往往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回想起当时的情境,心内都有一场海啸汹涌而过,可是他们早已学会熟练的将其镇压,那微笑着的面部轻微颤动,只不过是是镇压时太过用力的表现。
良久,亦真轻轻地松开他的手,她缓缓退后几步。隔着这几步的距离看着他,才能看到他眼睛里的情意绵长。在这样幽然的灯光下看过去,苏绣衣裙上的孔雀绣纹,有着银亮的光芒,衣袂被风儿吹起,那袖口展开宽倨如蝴蝶的双翼。她略微福一福身,眉梢挂满娇俏,开口唱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此良人何!”
陆少倌闻曲听意,笑意更深,弯腰作揖回唱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两人相视笑起来。
陆少倌凝视着她的笑颜,轻轻问道:“这样的战况,若我娶了你,岂不是害了你?”
亦真盈盈笑着,唇边的梨涡缓缓展开,她斜睨他一眼,说道:“你既瞒着我费心准备了这么多,巴巴的将我接了出来,现如今又这样说,可见心思坏。”
陆少倌笑叹道:“我怎敢对你坏?不过是忐忑不安的纠结中,心意胜过了理智罢了。”
她伸出手来,柔柔向他的脸上抚过去:“惟愿生同寝,死同穴。”
陆少倌深深的感动起来,他只觉得,原来如此呛俗的话,从心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竟然这样动听。
亦真见他只是看着她,并不答言,她轻轻捂嘴笑起来:“这样老俗的话,我竟也说得出口。”
陆少倌面色动容,眼睛里竟似有润湿之迹,他走过来,几步的距离似有雷霆之重,他如同捧着珍宝般,将她的手贴在自己脸边:“这世间再没有更动人的话了。”
三娘低头笑道:“如今军情紧急,我们还在这里做这样的傻事。”
陆少深情的看着她,答道:“为了你,我愿意做这样的傻事。”
回到行辕,夜已经深了,陆少倌将亦真送至门口,他在门前停下,盯着她的眼睛说道:“我走了。”
亦真低着头,低低答一声:“晚安。”
她站在门前看他走下台阶去,便要转身,他突然回转身来,将她搂至怀里,旋一个圈,只听咔嚓一声,他们已经在屋子里,那门就关上了。
她尚未反应过来,只得用手揪住他的衣领。她无力的挣扎着,喘不上气来。他却不顾了,仿佛那明日即是末日一般。兵临城下他顾不得了,那身上的伤也顾不得了,他只有她是真实的,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抓住。他的呼吸急促的拂在她的耳边,她浑身酥麻起来,沉溺在他的气息中,仿佛漂浮在那满是莲花的湖水中央,不停地浮上来沉下去,又像那洒满在亭子里的梅花瓣,被风儿带着冲上来落下去,一点点的散开、再散开,毫无保留的绽放在他的怀里。
不知是谁,今日竟在房间里点了红烛,映得一室滟滟流光。那烛台上的烛泪暗暗垂落,点点绛红,滴滴凝结。那帷帐全放了下来,帷帐一角委垂在地上,像一张巨大的网,将两人紧紧的裹住,丝丝相缠。
又过几日,援军仍未有动静。而城外的赣军因着休整了这几天,似乎又有蠢蠢欲动之势。城内粮草只不过能撑得一个月,倘若援军来不了,他们纵使以困挡攻,也撑不了多久。
陆少倌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眉头深锁。
亦真两日未见他,知道他为着战事殚精竭虑,便亲手做了些家常点心,一路端着送过来。
刚走到门口,尚未进去,恰听得议事堂里有人气愤的说道:“这陈年、陈建章父子真是忘恩负义。咱们老帅待他那样好,他竟然领着精锐部队叛归赣军!”
陆少倌道:“叛已然叛了,说这些何用。”
又有人道:“少倌,你当日之事,做的也着实鲁莽了些。不过是欺负了一个女子,尚且未遂,你又何必要削掉陈建章的军职。惹得陈家恼羞成怒,才有今日之祸。”
亦真听得此话,心内一惊。
她听出来说这话之人乃是陆少倌的老师,孟先生。
陆少倌用脚使劲一踢沙发前面的理石桌子:“那畜生我早就看不顺眼,况且还在我陆府欺负人!”
亦真的心猛然被抽紧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脸颊烫人的紧,掌心里满满都是冷汗,她用手去摸下面孔,每触碰到一处,都是灼烧的疼。她浑身冷一阵,热一阵,不过几分钟,那身上的夹衣就依然湿透了。风从后面吹来,她只听得耳边是嗡嗡的回响,风哨声和耳鸣声相合相伴,浑身的温度落在地上,簌簌有声。
原来又是她,她已然害过了一个人,如今却又害了少倌。
她心内满满都是内疚和自责,脚步浮动起来,急急的向后面退出几步去。她觉得她此时不能见他,忙要离开,一转身却撞到匆匆而来的黄宁身上,那点心撒了一地,青花瓷的盘子跌了粉碎。她也顾不得见,只是匆匆的踉跄离去。黄宁不知道她听到了什么,忙在她身后喊:“姑娘——”
里面的人听闻动静,忙都跑了出来。陆少倌看着亦真离去的身影,心里琢磨她到底听到了多少,极不放心,便跟在后面追过去。他抬脚前瞪了黄宁一眼:“叫什么姑娘?少夫人!”
黄宁吓得不敢吭一声。
亦真跑回房间,坐在床边,只觉得心上有一把刀子,在细细的磨着。
她坐了一会儿,却又突然站起来。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
那一颗心急遽下降,仿若在平地上走着,脚下去突然踏空,落下的竟然是万丈悬崖,幽黑漆漆,深不见底。
她身子颤抖着,几乎要晕倒在地上。
陆少倌跟进来时,正看到她站在窗前,整个人呆呆的,没有丝毫生气。他忙走过来,从身后圈住她,问道:“可是生我的气了?这两天忙的昏头转向。”
亦真脸色煞白,低低的垂下泪来,她轻轻的擦着眼泪,强笑道:“没事,我只是想家了。”
陆少倌帮她擦着泪,笑道:“待过几日援军一到,我们打了胜仗,就可以回去了。”
亦真抬头看向他,满脸满眼都是担忧。
陆少倌温柔的笑起来:“丑媳妇担心见公婆了?”
亦真被他哄得笑起来。
陆少倌将下巴放在她的发间,嗅着发香,他低低的笑道:“可是我这个人呢,单单就喜欢丑媳妇。”
亦真含笑着白他一眼。
亦真决定将此事放在心内,虽然这件事像绳子一样悬在她的心上,时时刻刻荡悠着,每荡一下,就将血肉厮磨的生疼,可是他不提,她就只作不知。
他就这样静静地揽住她,两个人相拥着,听着窗外风声萧瑟,有小石子被风带起,啪一下打在窗子的玻璃上,像是身处极远的荒野上,飞沙走石,天地间都是动荡。
☆、【十】
这几日,城外赣军已有攻城之势。
派出去的人传来飞信:“刘树贵援军已经行至褐水河边,不过两日就到。”
陆少倌放心不少,他本是少年就与父帅在战场上走惯了的,现在又是青年为将,心中有胆略,胸中有沟壑。这场战争本是筹备多年、胜算极高的,但不曾想陈年率精锐部队叛变,让他措手不及。
这几日,天色阴晦,铅云低垂,天空断断续续的下着雪珠子,打在玻璃窗子上沙沙作响。到处是一片白茫茫,进出院子里的梅花砖上,风呼啸卷过,露出花白的青色,从屋里看去,竟像是一幅青花瓷图雕。雪霰子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
房间里笼了地龙,生了炭盆,正燃着银丝炭,那炭块烧的如红宝石一般,偶尔哔剥响一声。亦真坐在床边,只盯着那炭火看,心思辗转千回。已经是上夜时分,陆少倌还在前头,她知道如今军情到了极度危急的时刻,就如那墙角放着的一把古琴,那琴上弦子绷的紧紧的,仿若轻轻一拨,就能断开来。
本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同生共死。可是如今,当她知道了陈年叛变之事后,她如何还能坦然的要与他同生共死?她的罪过重如磐石,而他不然。她蹭一下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有那样大的抱负,她怎么能让他受她的带累?
她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着,只盼着那援军早点到。
陆少倌回来的时候,她正和衣躺在床上。
她其实并没有睡着,心里将他的动静听得真切,可是却迟迟没有睁开眼睛。陆少倌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帮她盖好被子,在她身边躺下。
她听着他睡过去了,便缓缓地睁开眼睛,望着房间南墙上那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