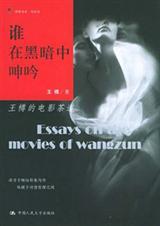谁在思念旧时光-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乖乖照办爬过去,嘴里却说:“我们又不是没睡过一张床,那时你怎么不赶我?”
他放下手机,像看白痴一样看我:“小姐,那时我们一天画八个小时画,再去不停刷四小时盘子,为省两块钱,走一个小时路回家,每天到家都是半夜累得像狗。别说你睡我旁边,就算你睡我上面,我都不会有任何想法。”
他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
过了半个小时,他躺了下来,关灯睡觉。
我心里有事,翻来覆去睡不着。
于是我轻声叫他:“李时,你睡着了吗?”
没人回答。
又叫了两遍,没反应。
我隔着被子,用脚动了动他的被子。还在装睡。
于是我曲起腿,把脚伸出去,挠他的痒。
这下他终于忍不住了,不知被我挠到哪儿,只听他闷哼一声,抓住我的脚踝一把塞回被窝,无奈道:“说。”
我稍微整理了下思绪说:“我们出发前一晚,我画室来了个女人,孙雪莉,我在C大的同学。我之前在医院碰见的,留了我的地址电话。”
“说重点。”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她是C城人,这么巧嫁到了H市,还生了个女儿。”
“重点!”
“她跟我说,四年前她嫁给了钱伯寅,跟着他回到H市生活,两年前离婚了。”
李时抓重点一向很快:“你是说,她嫁给了你那个初恋?”
“对。”
“哦,然后呢?”
“然后我目瞪口呆啊。她说当年我去法国以后,钱伯寅留在C城,她毕业后进了他工作的公司当美工,两人接触之后开始交往。钱叔叔生病后,钱伯寅和她回H市接手家里的厂子,并且结婚生子。但最终厂子没能挽回,钱叔叔的病也没能拖很久。而他们一起过了两年发现性格不合,过不下去了,办了协议离婚,现在孩子跟她过。”
李时咦了一声:“她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她说前几天钱伯寅去看婷婷时心情有些低落,加上她在医院碰到我,就猜是跟我有关,猜是我回来了但不能接受他结过婚的事。”
我翻了个身,侧躺着继续说:“听她的意思,钱伯寅心里一直有我,而且他们的婚姻已经是过去式,希望我不要介意,如果我们复合,她和婷婷一定不会妨碍。”
李时啧啧称奇:“这样的中国好前妻世间难寻呐。你那个初恋不会眼瞎吧,竟然会跟她离婚?”
我心里也觉得孙雪莉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钱伯寅更不用说了,两个这么好的人走到离婚的地步必然是有不得不为之的原因。
“你真介意这些?”李时不相信地问。
“这还用问吗?”
“那你还等什么?”
“……他妈妈恨我。”
李时好奇心上来了,追问为什么,我支支吾吾不肯说。我们俩又扯了一阵,可能是因为憋着的话说了出来,我心里轻松了不少,慢慢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李时以地陪的身份,带我去四处观光。有一条山溪从村旁蜿蜒流过,本来沿着溪水走肯定没问题,李时偏以为自己还是山里人,带我走山路看什么洞,结果差点迷路。幸好遇到了采蘑菇的村民。
李时的叔叔和婶婶很热情,每天都给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不停给我夹菜,直把我的碗里堆得冒尖。另外,午饭过后,我就给自己要了条电热毯,不用再跟李时挤一张床了。
不出两天,我就习惯了这种闲散安逸的生活,每天唯一的正经事就是到处走,挑个喜欢的地方写生。因为进村的交通不便,这个山村还保持着原始淳朴的自然风光,尤其粗糙朴素的土房,特别有画面感。村里里不来外人,村民一开始还对我很好奇,后来看见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据说偶尔有写生的学生会到这里来,李时说他六七岁的时候,跟着那些来画画的学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画。
画够了风景,我跟李时提议去周边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看看,去画点人物民俗什么。原始粗犷充满野性美的少数民族群众一直是画家们的最爱之一,这也是西藏题材久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没想到李时说这个村子就是民族聚居地,这里一大半人都是彝族、纳西、白族的,他掏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我看,上面竟然写着“苗族”!我看了看周围与汉地一般无二的砖瓦房,又看了看李时那张与汉人无异的脸,不禁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李时说:“你那是什么脸?怎么着,还想让我给来段歌舞吗?”
我问:“你会吗?”
他说:“我要是会,不用刷盘子,早去卖唱了。”
“那你会什么呀?”
李时考虑了一会儿:“非要说的话,我会采菌子。”
一听“菌子”,我的眼睛都亮了,李婶炒的菌子鲜美爽滑,我每次都能多吃一碗饭。
李时告诉我,现在虽然离野生菌子大量上市还有一个多月,但山里已经长出一些了,自已吃足够了。于是我俩花了一个下午采了一筐牛肝菌和青头菌,拿回去给李婶过目,因为有些菌子有轻微毒性,得小心一点。李时说他小时候吃了菌子就能看见小人国,一排排在他肚皮上打仗,非常过瘾。
晚上,我们吃了李婶挑过的菌子,和腊肉一起炒,果然比之前的更好吃,鲜爽清甜,还有一种清新的滋味,绝对称得上山珍级别。
像往常一样,吃饱喝足,和李叔李婶聊了一会儿天,我们就回去睡觉了。
这一觉,我睡得格外久,也格外沉。
作者有话要说: 本章过渡,明天推进情节。
☆、第十章
没有美术生不爱外出写生的。
钱伯寅学建筑的,对素描和色彩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系的活动他也陪我去过几回。而第一次去的是陕北的安塞。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境内沟壑纵横、川道狭长,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本来一行人主要目的是去看安塞腰鼓,去了才知道,除了过年的时候,电影里那种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的腰鼓舞一般是看不见的,大家不禁有点失望。
我们在黄土塬上画了三天,有几个同学对梁涧沟谷失去了兴趣,决定继续北上。我和孙雪莉还有两三个同学留了下来。当然还有钱伯寅。
安塞风沙大,穷学生们住的小旅馆里不能洗澡,我们每天回来就去街对面的公共浴室。高原民风淳朴,那时商业也不发达,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收拾干净,随便吃两口晚饭,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艺术生到底自由烂漫一些,恋人自然地住在一起,没有人大惊小怪。
我躺在床上翻钱伯寅的相机看,他则靠在他那边床头看书。照片拍了不少,刚开始是一些风景建筑,后面就全是我了,大多是我坐在那里写生的背影。翻了半天,终于看到一张正脸,是一个大爷坐在岩石上抽烟的照片。
我记得他,唱着酸曲赶着羊群从我们身边经过,声音又高又亮,走出老远还能听见。
我想钱伯寅在C市呆得比较久,能听懂很多方言,于是问他那个大爷唱了什么。
他放下书,想了想说:“有些我也没听懂,只懂几句。有一段是……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刮个东风水流西,看见人家想起你。”
我一听笑了:“我还以为信天游唱得都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呢,大爷还挺有生活。还有呢?”
“还有一句……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
他的脸红红的,不知是白天风吹的,还是在想什么别的。
我掀开被子,把睡袋拉链也拉开一半,向他招招手,“过来。”
这个睡袋是他去野外时用的,来的当晚,就铺在了我的床上给我用。
他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我,最后穿着T恤长裤钻了进来。
这些天,我们虽住一间房,但是各睡一张床。他是个自律的人,平时亲吻拥抱点到即止,抱着我的时候,手从来没越过我的腰线。
而我则不同,远没有他的克制,我会尽我所能地亲他,直到他气喘吁吁地把我拉开。在我的观念里,性是通往爱情的必经之路,对美好肉体的渴望是人性的本能,不应被忽视和压抑。很多艺术家的创作激情正是来自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恋爱。试想,没有了激情和快乐,我们应该在画布上画些什么呢?所以,我对这件事,有的是好奇和期待,并不忌讳也不害怕。
两个人挤在单人睡袋里,四目相对,一时无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记错了。”
他疑惑地看我。
“后半句应该是‘面对面睡着还想你’。”
他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我没好意思说。”
“我也想你。”说完,我亲了亲他的嘴唇和脸颊。
他笑着回吻我,温柔地,没有一丝攻击性。
渐渐地,吻着吻着,我不自主地靠近他怀里,整个身体和他的紧紧贴到一起,今天的他似乎更加禁不起撩拨,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身体一点点的变化。没多久,他握住我的肩膀,轻轻推开,弓起腰往后缩了缩,但因为睡袋的包裹,并没有如愿和我拉开距离,腰部以下还是贴在一起。
他粗重而灼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我知道他在努力克制自己,额头都冒出细密的汗了。
我抬手抹去他头上的汗珠,又要亲他,却被他拦住了。
他握着我的肩膀不让我靠近,眼底满是压抑,声音低哑地说:“小川,我不想和你第一次是在这里……”说完,眼珠转动,示意我看看周围。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剥落的墙皮,破旧的门窗,坏了不知多久的小电视……
但我哪在意这些,对他灿然一笑,说:“是你,在哪里都没关系。”然后就要去抱他的脖子。
他看着我有些失神,但很快反应过来,捏住我的手腕,又说:“我想等你过完十八岁生日。”
“早几天晚几天没区别。招兼职的都没你查得严!”
不等他反应,我全身一用力,翻到他身上,重重地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