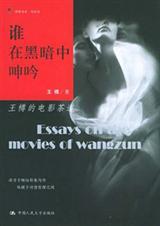谁在思念旧时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庆祝我的进步,我决定恶心恶心他:“你听说过呕吐画家吗?”
他摇头我继续说:“伦敦有个姑娘,发明了一种新的画法,把染过色的豆奶喝下去,然后催吐,吐在画纸,”我指了指他洁白如雪的翻毛外套,“或者衣服上,吐一幅可以卖好几千英镑呢。”
“吐之前还要禁食一天,以免吐出什么奇怪的东西,也真是良心画家了。”
果然,听完他脸色就变得很奇怪了,八成是在脑补那画面。
过了一会儿,他咽了咽口水,说:“你们也真是够拼的。……有点变态。”
我解释道:“别害怕,不是所有画家都这么疯的。有的虽然另类却也很有美感,比如有用嘴唇画画的,唇上不同颜色唇膏,印到画面上的,有用手涂抹的,有用拳击手套的……还有就地取材,女画家用胸部,男画家就用……”,我想了想,找了个含蓄的词,“自己的器官。”
我平时跟同行在一起更直接,人体的结构是基础课程,我们早过了羞于启齿的阶段。
他听了嘴角一勾:“这个有点意思。”
接着我们又聊了些很多。我发现他虽然不懂艺术,却对艺术家的奇闻异事知道不少,有些我都没听过,加上他似真似假地描述,我听得入迷。
车停在熟悉的冬青下,我恍然发现已经到了。
我解开安全带,向他道谢。
他说:“别再给我钱了。”拍了拍口袋,挑眉说:“你上回给的还没花完呢。”
我让他别省着,使劲花。
“说真的”,他换了种口气,转向我,左手搁在方向盘上,正色道:“小川姐,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吞吞吐吐地,“其实……你…唱…歌…真…的…要…人…命!”
我认真地听他嘴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的话,就笑得几乎趴在风挡前。没错,我的歌声属于自己听了都害怕的那种!五音不全已经不足以来形容了,根本没有五音;跑调更不是问题了,我都不清楚调在哪儿。
那一晚真是难为他了。
好容易缓过来一点儿,我抹了抹眼角笑出的眼泪,挥挥手,准备下车。
忽然,我的手腕被他一把握住,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转头对上他的眼神。
他脸上完全没有了刚才嬉笑的模样,定定地望着我,表情温柔,深邃的眼睛里流露出难以言明的情绪。
他慢慢倾身向我靠近,我没有动。
直到我们鼻尖对着鼻尖,气息交织,他才又低低地开口:“可是,你笑起来……更…要…人…命。”
这个调情很到位。
高明的调情其实无关话语,气氛营造地好,哪怕不说话,眼神和呼吸都能撩动神经,让人心旌荡漾。
嘴唇一软,他的吻落了下来,蜻蜓点水般很轻,如懵懂少男少女间的试探。
但他一点之后并没有离开,转而亲了亲我的嘴角。温暖的手抚过我的脸颊,拇指指腹轻扫他吻过的地方,有些痒。
“每次看你笑,我就想这样……”
说着再次贴上我的嘴唇。如果说刚才那一吻是小孩子过家家,那这一吻就是成人级别的,还是进阶版。他用自己的唇摩擦我的,直到我觉得嘴唇发热,才伸出舌头探入我双唇之间的空隙,舌尖轻挑,越过我的牙关,进一步撩拨。这样富有情趣又技术高超的吻恐怕很少有人能拒绝。很快他停止了挑逗,深深地吻我,每次我被吮得舌根发麻时他就会松开一些,只含住舌尖轻轻咬。
如此反复几次,我有些招架不住。
车里没有开灯,昏黄的路灯光透进来,晦暗不明。夜已经深了,四周很安静,我的耳边只有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和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昭示某种不受控制的欲望呼之欲出。
这个漫长的吻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气喘吁吁。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下摆,手掌温暖,在后腰游移,像保暖贴片,很舒服。我倚进他怀里,抬起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他低头吻着我露出的锁骨,同时顺势往上单手解开我的内衣扣子,绕到前面,握住一边开始揉捏,我的呼吸彻底乱了,嘴里不断发出无法压抑的声音……
作者有话要说: 新手写文,不知道这种尺度算不算违规,怕怕的。我保证,这已经是最大尺度了,不会超过。
☆、第三章
那晚,周东亭的车在门口停了一个小时后离开。
在车里的时候,窗玻璃上全是白色的水汽,看不见外面,下车才发现,雪已经落了一地。
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世界被一片白茫茫覆盖,纯洁无瑕,虽然只积了三四公分厚,这在H市已经算是十年难得的大雪了。
我看了看时间,想给两个学画的学生打电话,说雪大就别过来了。拿起手机一看,已经有好几个未接来电。我一向睡得浅,稍有动静就会醒,昨晚这一觉睡得真是黑甜。
原因不言自明。没有什么比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更能纾解身心的了。我活动了一下身体,觉得除了腰背和膝盖有些酸疼外,全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神清气爽,好像连常年僵硬的肩膀都松快了不少,不觉一喜。
安排好学生的事,我简单吃过午饭。心情不错,打算趁着雪停未消,出去走走,收集点素材,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电话是我堂姐打来的,一接通就问我在哪儿,要我马上去派出所一趟,语气很急。
我平时跟我爸那边的亲戚来往很少,他们一般也不太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还突兀地提出这种要求。我有些纳闷。
接着她向我说了件事。我姑姑姑父开了一家生产摩托车配件的小工厂,她舅舅——也就是我爸,这两年在厂里帮忙。因为效益不好,欠了隔壁的电厂半年的电费,昨天电厂拉了他们的电闸,今天上午,我爸就去找电厂的人,说了几句就打了起来,当场就把其中一个人打得满脸是血。有人报了警,他被110带走了。现在厂子里一团乱,他们应付不过来,要我去派出所领人。
我说我有事,去不了。
她一听,冷哼一声,接着只用一句话就击败了我。她说:“你不去,那我就只好给小江打电话了。”
小江新婚,作为唐家的上门女婿,多少双眼睛看着,尤其他那老丈人,始终对他不满意。这件事,现在他办起来可能更容易,但是对他自己,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我只好答应下来。
到派出所的时候已经快下班,派出所里靠墙的一排椅子上坐满了人,有男有女,都带着手铐,看来这一带治安不太好。扫了几眼,我要找的人不在其中。
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不太清楚办事流程,转了几圈只领到几张表。
正填表,就觉得有人在看我,抬头往四周张望,意外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是上个月跟我相过亲的魏子昂。他穿着警服,戴着警帽,手里拿着文件夹,乍一看还有点正义化身的感觉。我知道他是公务员,倒不知道他是警察。
“俞小川,真是你啊。”走到我跟前,他笑着说道。可能不再是相亲对象的关系,他对我放开了些,不再文绉绉地叫我俞小姐。
“该不是来找我的吧?”这句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我干笑两声,把来意告诉了他。他听完点点头,也不多问,就带着我就去找办案的民警。
我今天的任务是取保侯审,把人带回去,结果我连人都没见到。办案的民警告诉我,这个案子的嫌疑人现在不能取保,因为对方伤得很重,现在还在昏迷,能不能醒过来还不好说。他们看了电厂的监控,是我爸先动的手,下手还挺重。
我心道不好,本以为就是个打架,这弄不好就成了杀人了,虽然我跟他没多少感情,但想到可能他后半辈子要在牢里度过,不禁心情有些沉重。
那民警看了看魏子昂,像在猜测我是他什么人,然后问我要不要见他说几句话,等正式立了案要见就没这么容易了。我说不用了,没什么要说的。
魏子昂把我送出门口,嘴里说着客气的套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脑子里乱得像一团毛线疙瘩,再塞不进一点东西。不知是不是我敏感,总觉得魏子昂表情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感。我心知他以后应该都会躲我远远的。
没想到,三天后,他给我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过去。
到了派出所,他们告诉我,被打的那个人醒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定了轻伤,休养一段就能好。姑姑他们立即去做工作,可能事先已经和电厂的领导沟通过,花了半天,就和他们达成了和解。所以现在,我爸可以走了,没事了。
我有些懵,这一切发生地太快,剧情的大逆转让我应接不暇。就好像我突然中了五百万,一边半信半疑,一边暗自狂喜,这时有人跳出来指着我说,哈哈骗你的,傻瓜!
直到看到他从里头一扇门里出来,警察解开了他的手铐,我才确信这是真的。
他慢慢朝我走来。
上回见他是在小江的婚礼上,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穿着样式普通的毛呢外套,头发是刚焗过的,黑的发亮,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延伸进了鬓角。我很难把他和我印象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因为他一直吊儿郎当的烟不离口的小混混形象。那一刻,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时光的魔力,无声的岁月把他变成了一个稳重可靠的中年人。
今天,他看上去很邋遢,头发乱蓬蓬的,眼窝深陷,眼里布满血丝,满脸胡茬,有些已经白了。
他看见我,并不意外,咧嘴笑了笑。不是苦笑,不是讪笑,是那种极其自然的笑,是你早晨出门买菜时碰见熟人的那种笑。
他打了个哈欠,问我:“有烟吗?”
我摇摇头。
我们俩走出大门,我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包利群,抽出一支递给他。
他掏出打火机,点上,吸了一大口。
很快,一支就完了,我把剩下一包都给他。
他随即点着了第二根,“有钱吗?”
问这话的时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