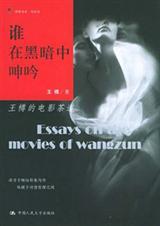谁在思念旧时光-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钱伯寅表情未变,还是微笑着,但并没有立即接话。周东亭好像知道什么似的,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好戏。
“抱歉,过几天我要去外地出差,到下月中才能回来,恐怕去不了了。”
“这样,那真是可惜,我想我妈要是见到你,就不会再让我姐去相亲了,是吧姐?”
话音刚落,钱伯寅诧异地望向我,不敢相信我还在相亲。
周东亭还嫌不够乱,说:“小川姐,你最近在哪儿相亲呢,不去湖西路的餐厅了吗?”
这下,连裴爽也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我被两人一唱一和弄得头大,随便找个话题,急忙把他们打发走。
重新坐回位置上,我想解释,他却捏着我的手,摇摇头,让我不必说,他明白。
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心意相通也会让人觉得苦涩。我们对这件事的同一判定,表明我们对这段感情的未来都不确定,都没有做好为此跟亲人斗争的准备,除了用笑容掩饰心里的无奈和无力,没有更好的办法。
十六年前,我十二岁,一个陌生女人来到我家,当着我和小江的面,将我们本就寒酸的屋子变成了彻底的废墟。我看着她疯子一样的摧毁所有能拿起来摔下去的东西,抱着吓得直哭的小江,躲在角落里。
我知道她是谁,也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她家以前住在我们家隔壁,早在我们家住进来之前就搬走了,只有男主人因为工作原因,时常回来住。不知几时起,晚上我写作业的时候,就能听到二楼阳台后门开合的声音。我们家和二楼隔壁的阳台是相通的,绕过一面围墙就能到别人家的后门。
这个声音几乎每天同一时间出现,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我常常不敢睡觉,在黑夜里竖起耳朵,总要听到第二次门开合的声音才能闭上眼睛。
后来,我妈时不时会给我一些以前从不会买的东西,有时是书,有时是衣服。那时的我经常穿她不知从哪里拿回来的旧衣服,虽然心里胆战心惊,可对这些漂亮的礼物并没有多少抵抗力。我们默契地从不讨论这些东西的来历。
但这个女人的出现,正式将一切美好的表象撕破。我永远忘不了她拿出刀子对着我和小江时的场景,她脸色惨白、眼睛血红,眼珠快要瞪出眼眶,怒视着我们,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小江哇一声开始大哭,她就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我带着小江朝门口跑去。
我颤抖着手去拉动门把,门却纹丝不动,像是被人从外面顶住了,让里面的人出不去。
我们使劲拉门,突然听到背后哐当的刀子落地的声音,那把水果刀就扔在我的脚边。我惊恐地回头,还没看清就被人死死抓住领子,接着,一只纤瘦的手就朝我抡了过来……
我记不清这场全武行持续了多久,最后,她累了,站起来,走到门边,敲了两下,打开门离去。
当我妈下夜班回来看到面目全非的家和墙上那个用刀子划出的“贱”字,半天没说出话。我让吓呆的小江去睡觉,自己和妈一起收拾剩下的垃圾。令我没想到的是,那晚,她像没看到我肿起的脸颊和发青的额角,只用一种很冷的眼神看着我,还带着怨恨,对我的怨恨。我意识到她在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这里的一切,我是直接受益者,却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羞耻和惭愧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无法说出一个字,耳边回响的都是她临走前的话:“你和你妈一样,都是贱货!”
花了一个多星期,家里才勉强恢复了原样,甚至还多了一件对我们而言的“奢侈品”——全自动洗衣机。这次,我妈直接对我说:“这是你钱叔叔买的,算是补偿。”
此后,她的事对我再不是秘密,她仍然避着小江,但不再避着我。我拼命地画画,告诉自己: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去想。
家里陆陆续续多了一些电器,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方便了很多。而我和我妈的交流越来越少,很多时候我不敢跟她对视,害怕看懂她的眼神,让自己心惊心寒。
之后的两年,我有时会在学校门口附近见到钱叔叔的太太,那个纤细瘦长的女人。她在等我。但幸运的是,她再没有对我动过手,只是极其鄙视和仇恨的目光盯着我,直到我低着头走出好远,我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冷意牢牢粘在我背上,随时准备切开我的身体。
两年后,钱叔叔突然退出了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再来往。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能理解命运的幽默感,兜兜转转,偏要把不该再见的人送到一起,大概是嫌以前的闹剧还不够荒唐似的。
钱伯寅毕业的那年夏天,钱叔叔到C城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一下认出这个在我青少年时期留下不可磨灭记忆的男人。这次重逢带来的震惊不言而喻,我和钱伯寅开始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看是否能够接受我们之间共同的过去。
钱叔叔知道了我们的事,找我谈过一次,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此生永别。
年少的爱情天真无邪,以为爱情能够代替一切,能够破除世界上所有阻碍,只要能在一起。我们决定,以后留在C城生活,与H市保持最低的来往,打算此生相依为命。
我们对彼此做出了承诺,却都没有办法实现,不是因为别人,而是高估了自己。
我们俩都变了。
从前在一起的呆着,半天不说话,只觉得自在;现在却无法忍受五分钟的沉默。他常常对着我出神,小心翼翼地挑选话题,不去触碰彼此的过去。最后,我拿着画笔长时间地呆滞,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画画,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唯一的坚持就要完蛋了。
终于等来了他幽幽的一句:我们分开吧。
不是不爱了,是不想毁了对方。
一别八年。
再次见到他,我满心欢喜,偷偷期待时间已经替我解决了一切问题。可此刻以情侣的姿态坐在他旁边,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未来和八年前一样危险而脆弱。
满心失落的我没有心思应酬,连柳开文过来也不能让我提起精神,他可是我的衣食父母之一。幸好陈姐不在,没人指使我。
柳开文和钱伯寅说了什么,我没听,反正就是交待工作的事。然后他注意到我,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钱伯寅的肩膀,转身离去。
渐渐地,理智终于回到了我的思维中,喜怒无常、阴晴不定不是我的性格。
我哄回自己,问起婷婷的情况。在我们的关系中,这是个无法回避的人,之一。我总是要努力做出尝试的。
钱伯寅脸上立即浮现起父亲的慈爱,是我从没见过的,如很多普通爸爸一样,想起孩子时的真心的喜悦。他告诉了我很多婷婷的事,从小到大,让我对这个小女孩产生了好奇好感。分别的时候,我们约好,下次带婷婷一起出去。
☆、第十五章
春雨缠绵,如丝如线。
我把一本本大小不一的速写本摊在桌上,按照时间排好,看上去像是连环画的草稿。时间跨度很大,有的纸页已经发黄,有的墨迹还没干。
我的两个学生在帮我整理出这些之后,便离开了。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来这里,经过柳家的事后,我完全体会到了合格的助手的意义。
中国的预备艺术家们,因为考学的需要,往往会先去画室集训,再进入大学学习。
欧洲则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毕业后才进入画室。那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而是选择志同道和的老师和朋友,开展职业化的创作。在那些画室里,学生和助手的区别是很模糊的,或者说没有。老师付给少部分的报酬,以近乎剥削的价格让学生为之工作,誊写、描摹、测量以及各种琐碎的事情。成名的画家往往有优秀的助手,并且不止一个,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画家的工作有时候相当繁重。
刚毕业的学生在这种时候处境相当尴尬,满心欢喜进入首屈一指的画室,跟着心仪的大画家,看着老师和得力的助手激烈地讨论灵感和草稿,你却只能整天做着最琐碎的事。唯一的能做的就是像一块海绵一样,面对无比丰富的资源,拼命吸收你想要的知识和经验。
我就曾是海绵之一。
顺便说一句,欧洲的艺术氛围很好,画廊艺术馆博物馆遍地,但要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生存下去,并不容易。
好在我熬过了那段生活艰难、灵魂充实的岁月,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段每天只吃一个面包的日子,也不觉得苦,只觉得胃隐隐反酸。
总之,学生在画家完成一幅作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越是随着画面尺寸和画家年龄变大,越是如此。安格尔的传世名作《泉》,一直有人怀疑是由76岁的安格尔指导他的学生完成的。
于是,我象征性地收取少量的学费,教授这两个学生技艺的同时,也抱着让他们充当我的助手的期望。只是他们始终停留在当“学生”的心态,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真正的帮助,当我踩在梯子上画高处的画面时,帮我调出恰当的颜色都很困难。
我让他们最后帮我做的事,就是把还没来得及整理的一箱速写本分类整理,并让他们各自挑选一本当作纪念。
这些速写本是我从上大学起攒下的,从来舍不得扔,有三十多本。有些有着精美的皮革封皮保存完好,另一些则散成一页一页的,只用皮筋固定,这些本子如实地反映了我的经济状况——长期拮据,偶尔宽裕。
速写内容差不多全是铅笔或钢笔素描,少部分用油彩上了色,几乎涵盖我的生活,卖菜的小贩,抽烟的男人,海边的夕阳,橱窗里的面包……都是我所见过的风景和人事,有点像片段式的日记。
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国时期的本子。不过,看他们的表情,也许更愿意要一幅画室里的画。
送走他们,我回到桌边翻看满桌的回忆,很快不能自拔。
李时打电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