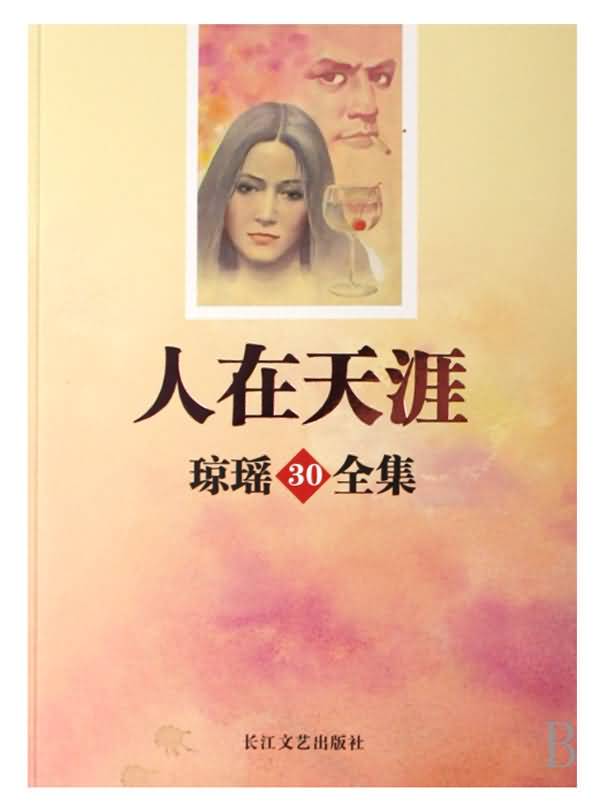曾在天涯-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