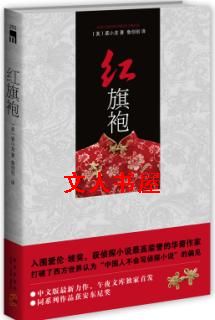蓝旗袍-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香衣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她看看宝柜,青白色的脸,头发眉毛和胡子茬上都结着一层白霜,双眼紧闭,和死了没什么分别,不由的滴下泪来,千不好,万不好,现在她只记起宝柜的好来了。
炕渐渐热了起来,宝柜脸上的霜雪融化了,凝成一层小水滴,香衣拿一块手巾,轻轻地给他擦去。玉翠呼哒呼哒地使劲拉着风箱,通红的火苗子冒出灶口老高。炕更热了,宝柜的头上升起一团氤氲的白气。
村长听说宝柜冻僵了,也赶了过来。进屋看到这个阵势,铁青了脸,大声喝斥:“你们想要了宝柜的命啊!这是谁的主意?”
屋里的女人和男人们都低下头,没人敢答话。
“快把火灭了!”村长吩咐着,一步窜到炕上,一把扯下盖在宝柜身上的被子。
玉翠提起水桶,把里面的半桶水全泼进了灶里,灶里反扑出一股白烟,呛得她打了几个大喷嚏。
村长喘了口气说:“冻僵的人得慢慢暖和过来才行,你们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这个宝柜也实在不太像话,整天喝得狗熊不认料勺,我就知道迟早要出事。白老师,你今天就不用去学校了,在家照顾他吧。”
白香衣的眼泪叭哒叭哒地掉下来,心里翻腾开了。如果宝柜真的死了,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好容易经营起一个家,难道老天爷就这么不开眼,说毁就毁了?
村长他们几个男人,被白香衣哭得心里也酸溜溜的,实在看不下去,就嘱咐“有事喊一声”,各自回家了。再看玉翠,也早已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中午,孔宝川从邻村请来一个老中医,开了方子,说宝柜要能熬到明天出太阳,或许还有救。她们熬好了药,可宝柜紧着牙关,她们折腾了半天也没灌进一滴去。两个女人守着宝柜,眼瞅着他的脑袋和手脚肿大起来,傍晚的时候几乎比正常大出了一倍,摸摸他的身子,炭一样烫手,他的呼吸也时有时无,这光景看上去,说不定哪一会儿就要过去了。村里的女人三三两两走来探望,提出一些灌药的法子,一个个试了,却没有能行得通的。
后来,白香衣用最笨的法子,用调羹一点点往宝柜的嘴里灌,大部分黄褐色的药汁流了出来,只有少量的药渗进了他的牙缝里。这小小的成效,也让白香衣有了些安慰,她一刻不停地灌下去,心里祈祷着药汁能多渗进去一些。
夜一丝一丝地过去了,眼看天就要亮了,听听宝柜的呼吸,似乎有力气了些。两个女人看到了希望,一夜的劳累便像漫天的大潮涌了上来。
第一章 宝石蓝 雪花白 麦子黄 08 弥天
白香衣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哭哥哥,她打了个机灵,醒了,看见宝橱探着头瞅着宝柜干嚎,数落苦命的哥哥被人害得这么惨。
宝橱已经很久不登宝柜家的门了。起初宝柜收回地,宝橱觉得天经地义,没当回事,可是禁不住胡桂花天天在他耳边数落宝柜两口子的不是,听得多了,宝橱也觉得宝柜两口子确实对不住他家,就懒得过来串门了。听说宝柜快不行了,兄弟之情顿生,心里有三分疼,七分惦记,就急火火地赶了过来。
白香衣悔恨交加,悲从心来,也哭出了声。
玉翠也醒了,听了宝橱的话不忿了:“宝橱,说啥呢?你哥还没有咽气呢,就忙着欺负你嫂子。”
“俺说的不对?不是嫂子把俺哥赶出去的?嫂子呀嫂子,你也太狠了!”宝橱一百个不服,梗着脖子说。
“你嫂子没有赶他,是他自个儿出去的。别在这里嚎,你要心疼你哥,就别吵得你哥不消停,耽误了病!”
“张玉翠,俺说不过你。”宝橱恨恨地转向白香衣,“俺哥有个三长两短,俺和你没完!”说完,在屋里转了一圈,气呼呼地走了。
玉翠搡了一把哽咽着的白香衣,说:“别哭了,还没到哭的时候。”
“嫂子,千不该万不该,我真不该摔了他的酒瓶子。可,可我心里憋屈得难受。”
“又来了,净说没用的。宝橱来了给俺提了个醒,万一宝柜不行了,你心里得有个决断才行。”
“宝橱也是心疼他哥,我不怪他。”
“你真是活菩萨!你以为宝橱真那么心疼他哥?他才不挂心宝柜的死活呢,他惦记着那二亩地和这位宅子呢。他一撅腚,俺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蛋儿。”
玉翠沉吟了片刻,问:“你到底怀上孩子没有?”
“没。”
“怀上了孩子还好说,没有孩子这事儿就难办了。”
白香衣也担忧起来,心慌意乱没有了主意,只得向玉翠投去求助的目光。
玉翠忽然一拍大腿,把心一横说:“你就说你已经怀了孩子。”
“可这也只能瞒过一时,迟早要露馅的。”
“瞒过一时说一时,以后的事容俺想法子。记住,一切听嫂子的,这个时候你只要错一步儿,这里就没了你的立足之地。”
白香衣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点了点头。这时候好像听见宝柜说话,两个女人一阵欢喜,忙凑上去细听,宝柜含含糊糊地说:“水……水……”
玉翠说:“老中医说的真准,看来宝柜没事了。”
她们不约而同望望窗外,初升的太阳撒了半院子黄橙橙的光。
高原是上课前听说宝柜出事的,知道自己闯了弥天大祸,无心给孩子们讲课,就布置他们写生字做算术。回到宿舍,想蒙头大睡,可蒙着被子,脑子却越来越清醒。
自从白香衣为他包扎伤口,他以为白香衣对他有了点意思,高兴得许多天睡不成安稳觉。可是,过了几天他发现,实际上白香衣却离他越来越远,瞧都不瞧他一眼,仿佛没有他这么个人,实在没办法和他说话时,也是不咸不淡,简明扼要。他恨不得亲口问问白香衣,要他怎么样做,才能令她满意。可是他不敢,怕把白香衣吓得更远,只好迂回曲折,委曲求全,期望能慢慢靠近白香衣。
白香衣的冻疮,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无意中听别人说麻雀脑子治冻疮很灵验,晚上就满村子里掏麻雀。冬天的晚上麻雀爱钻墙洞子,有时候几只挤在一起取暖,并且一旦钻进了洞子,多大的动静也不肯挪窝,很容易捉。高原的运气不好,走了大半个村子,却一无所获,忽然记起村外打麦场那儿有间场院屋子,墙上千疮百孔的,又僻静,一定有许多麻雀在那儿过夜。于是他直奔村外。果然不出所料,他掏了几个墙洞,就收获了七八只麻雀,估计够两天用的了,就系好装麻雀的袋子,边往回走着,边盘算着怎么给白香衣送去。
离村子不远了,他突然听到前面的柴禾垛里窸窸窣窣地响,好像有人在里面,以为遇到了贼,便躲在一边看个究竟。不多会儿,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钻出来,缩着脖子向村子走。高原越看越像贼,就悄悄地赶上去,不分青红皂白,拳脚相加。那人杀猪似的嚎起来,小高听声音很熟悉,仔细一瞅,却是孔宝柜。小高扭头便走,想趁宝柜还没认出自己之前离开。
越怕偏就被认了出来了。宝柜嚷道:“小高兄弟,你凭啥打俺?”
既然已经被认了出来,高原索性走回来,和孔宝柜面对面站着,装作才认出孔宝柜的样子,“哎哟!是宝柜哥呀!我以为是个贼呢,你跑柴禾垛里干啥?”
“喝醉了,迷糊了一觉。”
“打哪儿了?没伤着你吧?”
“亏俺命大,还以为你想要俺的命呢!”
“宝柜哥,看你说的,我是真没认出你来。”
“你别糊弄俺,你的那点儿心思俺还不明白?不就是为了那个小娘们。你找俺喝酒,也是为了那个娘们,灌醉了俺,你好和她亲热。俺有酒喝,就乐得装糊涂!”宝柜很自以为是地说,仿佛他的醉眼早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小高被他戳穿了心事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又听他说什么亲热之类的话,心中很为白香衣不值,一股火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孔宝柜,你还是人吗?怎么能这样说白老师?”
“俺自己的老婆,爱咋说就咋说,你管得着吗?俺就看见你和她眉来眼去了。她就是一个千人骑万人压的,今天还敢和俺凶,哪天俺没酒喝了,还要拿她换酒喝呢!你们还姐姐弟弟呢,你还真以为是俺小舅子啊,多管闲事……”
宝柜说得正得意,冷不防被小高踹了一个趔趄。“我是管不着,这会儿我也管不住自己的脚!”小高说着不解气,又结结实实踹了宝柜几脚。
宝柜抱着头缩成一团,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你个杂种?偷人家的老婆,还要揍人,明天俺就把你们那点儿破事抖漏出来,让老少爷们评评理。奶奶的,你敬着老子点,说不定俺还给你吃口剩饭。小杂种,你算是完了,以后甭想打俺媳妇的主意!”
小高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哪里禁得住这样的污言秽语,冲上去,又一阵乱踢。
宝柜嚎叫不止,嘴里仍旧不干不净。“俺老婆当年是头牌婊子,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和她睡过。你算那根葱?那根蒜?最多也是喝人家的洗脚水……”
小高也记不清踢了他多少脚,直到宝柜不出声了,才停了下来。
“哼,别和我装死,你要再敢满嘴放屁,我就废了你!”说完,不解恨地又踹了宝柜一脚,扬长而去。
到了学校门口,他很想去见见白香衣,又怕被宝柜回来撞见,彼此尴尬,便闷闷不乐地回了宿舍。躺到床上,他开始庆幸自己没去,孔宝柜的话在他心里起了作用,白香衣很有可能就是孔宝柜说的那样的女人,要不然她怎么会嫁给孔宝柜?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他多费心思。可想想和白香衣这段时间的接触,她又不像那种水性扬花的女人,一定是孔宝柜喝多了酒,满嘴说胡话。可是哪有男人这么骂自己老婆的?这不是明明承认自己是乌龟王八蛋吗?
昨天晚上没有想明白的事,今天小高也不会想明白。事情的发展已经使白香衣是什么样的女人变成了次要的事情,小高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孔宝柜真要死了,自己就成了杀人凶手。
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