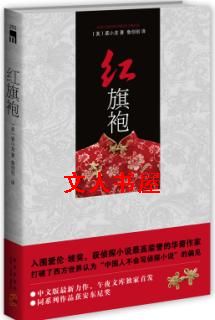蓝旗袍-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碎了,疼得眼泪更加汹涌澎湃,不等春生吹,就连声叫:“好了!好了!撒手!撒手!”
这一天放学后,曹子安在回家的路上挨了黑砖,大半个月没来学校,再来学校的时候,眼角的青还没有完全消退。有人问起来,他只说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
这一跤跌得好,白香衣最有理由喝彩,因为曹子安经这一跌,本分了许多,尽管注视她的眼神仍然炙热,但望而却步,再不敢明目张胆地骚扰她。
白香衣对土地的迷恋仍旧没变,她打算在校园的空地上,开出一块地来,种点儿蔬菜什么的。说干就干,星期天她借来了铁锨,翻起地来。她力气小,欺不住活,地没翻多少,出了一身透汗不说,细嫩的手上还拧出了几个水泡,一碰火烧火燎的疼。她拄着铁锨把子休息,心里犯开了愁,照这种干法,猴年马月也干不完。
中午散了工,吃饭的时候,春生听玉翠说白香衣要开荒种菜,胡乱吃了几口棒子面饼子,就扛着铁锨,赶到学校,抡开膀子干了起来。等白香衣发现,地已经翻了一大片。白香衣看见春生光着膀子,油亮的皮肤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子,就拿了一块毛巾,给他擦汗。春生红着脸躲开了,瓮声瓮气地说:“俺自个来。”
白香衣愣了愣,不由暗自发笑,眼前这个浑身腱子肉的小伙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孩子了,自己却还老拿他当小孩子待承。她忽然记起玉翠嘱咐她的话,就搭讪说:“春生,今年有二十五了吧?”
“嗯。”春生擦了把汗,把手巾搭在肩膀上,又抡起了铁锨。
“该成个家了,村里和你一般大的,就剩你一个光棍了。相中了哪家的闺女,告诉老师,我给你说去。”
春生只顾埋头干活,半天没有言语。
白香衣以为他害羞,就鼓励他说:“一个大小伙子家,别羞羞惭惭的,长大了,谁还不娶媳妇生孩子?”
春生还是闷声不响,把铁锨抡得虎虎生风。
白香衣见一会儿功夫,春生的身上又密密麻麻滚了一层汗珠子,怕他口渴,就进屋端了碗水出来。她铁定了心要让春生表个态,也好给玉翠嫂子回个话。“春生啊,今天你非给老师说个准话,找还是不找?”
春生的脸憋成了猪肝的颜色,把铁锨往地上一插,拔腿就走。
白香衣在他身后喊:“要走也得喝口水再走啊。”
春生远远的站住,说:“不了,俺上工去了。白老师,剩下的活你别干,等俺散了工再来。”
白香衣看着春生的背影摇了摇头,难怪玉翠老骂他犟种,真是一点儿也没屈枉了他。
曹子安在教室里,装模作样地守着一摞作业本,却密切关注着外面。他看出了一些暧昧,春生对白香衣暧昧,白香衣对春生也暧昧,越看越暧昧,他觉得抓实了白香衣的小辫子。
白香衣回屋去了,曹子安盘算着过去,和她交流交流思想。拿定主意,站起身,却瞥见校门口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正是他不想见的二妮,急忙开了后窗,跳出去藏了起来。他听见二妮亲热地叫了几声“子安哥哥”后,没了动静,但他为了稳妥地躲开二妮,就继续藏着没动。
白香衣坐在屋里,批改学生作业。学生的作业本五花八门,有草纸的,有烟盒纸的,花花绿绿,大小不一。学生的字也各有特色,有的大大咧咧,伸胳膊横腿没有规矩;有的一溜歪斜,好像要斜上云天;还有的小如绿豆,扭捏着藏着羞涩。看一本作业,就仿佛看到一张生动可爱的娃娃脸。
“咣当”一声,门开了,白香衣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形门扇横在门口,虎视眈眈地望过来。
二妮没有找到曹子安,怀疑曹子安在白香衣屋里,不由醋意大发,撞开门准备发威,但是她只看见白香衣一个人,就转怒为喜,笑了。“白老师,还认得俺吗?”
白香衣看到堵住门口的胖闺女来势汹汹,正迷惑不安,忽见她阴转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个名字便从心底跳出来。“你是二妮?”
“就知道白老师还记得俺。”二妮对白香衣能够叫出她的名字,很满意,晃着肥胖的身子扭进来,坐到床沿上,床不堪重负吱哑了一声。
白香衣笑着说:“二妮都成大闺女了,长得真富态。”
二妮有些娇羞,扭捏着说:“白老师也觉得俺俊,是吧?子安哥哥说了,俺像杨贵妃呢。你知道吗?古代有四个大美人,杨贵妃是最俊的一个!”
“我看也是,不过杨贵妃是封建剥削阶级的美女,二妮却是咱劳苦大众土生土长的美女,杨贵妃还比不上你呢。”白香衣教过二妮,记得她缺心眼,就捡好听的话说。
“白老师,你看俺急着出来,脸都没来得及洗呢。”二妮听得受用,说胖立马喘。
“这就够俊了,再洗了脸还了得?把太阳都比下去了!”白香衣打趣说。“那你急着出来干什么?”
“俺跟你说了,你可别跟别人说。俺是来告诉子安好消息的,俺爹俺娘同意让他娶俺了。”二妮掩饰不住的兴奋。
“那敢情好,找了个好女婿。”白香衣说的言不由衷,心里骂曹子安作孽,连二妮这样的傻闺女也要招惹。
白香衣却不知道,这可不是曹子安招惹二妮,而是二妮自己送上门来的。一天在大街上,二妮和曹子安擦肩而过,二妮闻到曹子安身上的香皂味儿,就鬼迷心窍喜欢上了这种清爽的味道,爱屋及乌,也喜欢上了这味道的主人,主动投怀送抱,而曹子安也不是个东西,居然来者不拒。
“俺可吃了苦头了,你看你看。”二妮捋起袖子,露出胖胳膊上的一些青紫印子,有些炫耀的意思。“俺爹俺娘不让俺跟子安哥哥好,俺爹骂俺不要脸,俺娘就掐俺,可俺就是非和子安好。俺跟他们说了:‘不让俺和子安哥哥好,俺早晚死给你们看。俺就要学习李双双,自己找婆家!’可他们不让俺出门,俺就看见剪子摸剪子,看见绳子摸绳子,吓得俺娘不敢出工,一天到晚跟着俺。这不是,今们俺娘终于想通了,使劲掐了俺几把说:‘傻妮子,俺再不管你了,是死是活,都是你自找的!’俺一听,就高兴了,他们不管俺,俺才舍不得死呢,先跑来告诉子安哥哥,让他也高兴高兴。”
二妮说得眉飞色舞,白香衣的心里却有些黯然,估不透等待二妮的是祸还是福。
“白老师你咋了?不高兴吗?”二妮见白香衣脸上淡淡的,就问道。
“高兴,高兴。”白香衣忙笑笑。
“俺还以为你不高兴哩。”二妮痴痴地笑着说:“俺还以为你也看上子安哥哥了,就不高兴了。”
“你是我的学生,当老师的,怎能抢学生的女婿?”白香衣哭笑不得。
“你不跟俺抢,俺就放心了。咱村里,俺看着除了俺,再就数到你白老师还能配得上子安哥哥了。”二妮很自负。
二妮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没有看见曹子安的影,对站在门口的白香衣说:“他可能家去了,俺到他家里去找。”
白香衣轻轻吁了一口气,回到屋里,感念了一会儿二妮,又集中起精神,批改作业。还没有批完一本,听见曹子安在门外问:“白老师,有开水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曹子安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走了进来。白香衣自他规矩起来后,对他的态度改善了不少,提起暖壶,给他倒上水。
端着水,曹子安却站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白香衣。
白香衣被他盯得不自在,就揶揄说:“曹老师,刚才你去哪儿了?二妮来找过你。”
“咱不提她好吗?咱也不提春生,就谈谈咱俩的事。”曹子安拿定了主意,破釜沉舟,和白香衣说个明白。
“你这话我不明白。”白香衣冷淡地说。
“俺知道,你为二妮吃味呢!可就算俺有二妮,你也有春生啊,咱们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谁也不用嫌弃谁……”
“等等。”白香衣打断了曹子安的话,诘问道:“这话更不明白,你和二妮怎么样,碍不到我什么,我吃什么味?再就是拉扯上人家春生干什么?”
“咱们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和二妮只是逢场作戏,现在是真心想和你好。你和春生勾勾搭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俺看得明明白白,春生因为你,还打过我一顿,我是为你挨打啊!”
白香衣气得脸色煞白,一指屋门说:“滚出去,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醒醒吧,咱们俩才是一类的人,都是文化人,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事业。二妮和春生都是满头高粱花子的庄户人,跟咱们走不到一块的……”
白香衣气懵了,顺手抓起墨水瓶砸过去,嘴里狂喊:“滚,滚……”
墨水瓶打偏了,打在墙上,迸溅出一个红艳艳的大花。
曹子安见白香衣动了真怒,似疯如狂,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临出门,仍不死心地说:“白老师,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你好好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现在我就明白告诉你,就是世界上的男人都死绝了,你也没戏!”白香衣对着曹子安的背影歇斯底里。
曹子安没敢在学校停留,慌里慌张地回了曹家庄,他知道这次的漏子捅大了,春生一旦知道,非把他活剐了不可。他没想到,家也不是避难所,二妮正热情似火地等着他呢。一见二妮,他就没有好气,往外赶二妮,二妮赖着不走。他就摩拳擦掌想动粗,却反被二妮撂倒在地上,压上一对大屁股,使他上半截呼吸困难,下半截臭屁滚滚。
恶人自有恶人磨,二妮人虽然不恶,却正是一小盅子卤水,对付曹子安这碗小豆腐绰绰有余。
二妮成了曹子安的影子。曹子安上课,二妮就坐在教室门口纳鞋底儿,或者找白香衣说话;下课了,她立刻赶到曹子安身边。她要守着来之不易的好女婿,防备被别的女人抢走。
没出一个月,曹子安缴械投降,和二妮举行了婚礼。白香衣送给他们一块背面作喜帐。在挂满喜帐的新房里,一身红衣服的二妮抑制不住兴奋,情不自禁唱了几句吕剧《借年》里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