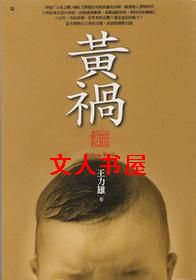黄祸-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宗教意识本身做为审美追求的最高层次之一,再没有比它更适合做为绿色未来与大众百姓之结合点的了。
开始他曾受到鼓舞。
在这种生死渺茫的环境里,灾民的宗教情绪一点就燃。
然而当他反复说明“绿教”没有神,没有来世,没有升天,不需要仪式﹑和尚道士,也不需要磕头烧香的时候,就怎么也深入不下去。
灾民以畏葸献媚的方式与他僵持,终于突破他做为“立教者”的权威,弄出了这个偶像。
虽然也用草皮树叶贴成绿色,虽然他们把它叫成“美”,可在狂热的膜拜中,叫的却是从“玉皇大帝”到“关公爷爷”,还有人叫出的竟是“毛主席”。
这偶像是最后一块砝码,使天平彻底定位。
他明白了,宗教意识虽然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但对物质人,最终不会成为精神审美,依然囿于他狭隘的功利愿望,为保佑现世,为死后上天堂,或为来世投好胎得好命。
他们懂得眼前的大水是报应,惩罚他们忙于挣钱,忘了敬神。
神是明确的,一还一报,赏罚分明。
“美”是什么,他们却搞不懂,也无从产生敬畏之心。
'文'太阳被地平线吞没,凉气一下便升起了。
'人'白雾从水面上悄然凝聚,精灵一样飘来。
'书'欧阳中华想起北京,陈盼那个温暖的小窝。
'屋'出发前,陈盼说他一定会成功,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他从不像陈盼那样把“人民”二字奉若神明。
与其说他来求成功,不如说只是求一种证实,以使自己问心无愧。
如果物质的“人民”不能转变成精神的“人民”,世界只有毁灭。
他做了努力,虽然他早就认为毁灭不可避免。
如果说以往这种认识还只是对客观趋势无奈而冷静的推测,那么在黄水包围的此刻,则显露出另一种新的意义。
毁灭和绿色未来携起了手,连结着那两只手的是死亡。
在死亡中,他看到了把握未来的点……“城里大哥,该吃饭了。”那怯生生的声音像每天一样来到身边。
姑娘小心地捧着一把出芽的麦粒和一块空投饼干。
拜神已经结束。
人们排着队从最老的那个男人手里领自己的晚饭。
第一份照例先送给欧阳中华。
欧阳中华用草帽接下了。
姑娘没有马上离开。
她有多大了 他始终没问过。
十天前,他从一座快要倒塌的房架上把她救下来,他以为她只有十四﹑五岁。
现在,她那对在小背心下鼓起的乳房那么丰满,他相信她总该有十七﹑八了。
“城里大哥……我没跟他们去磕头。
我看着太阳……我真地感到了你说的: 美,就在我心里……”姑娘眼里泛起泪光,突然扭头跑开。
欧阳中华深吸一口潮湿的空气。
一个灵魂尽管只燃起小小的火苗,也能烫得人心头耸动一下。
她能证明什么吗 他有些不安。
证明她的乡亲们能转变 证明他们不该死亡吗 不。
他无声叹息。
她只是黑夜坟山的一星磷火,照亮不了黑夜,只能随黑夜而消失。
他舀了半饭盒水。
想起水中飘浮的那些尸体就隐隐作呕。
最后一片净水片被捏碎扔进饭盒。
细密的气泡从水底急速升起。
他后悔药品和净水片带少了,可即使再多,也不够这么多人,何况还有其它高地上的灾民呢。
他开始机械地咀嚼麦粒。
这几天逐渐失去了饥饿感,但他知道必须把这些如同木屑的东西咽进去。
每天,他划着橡皮艇在淹没的村庄上飘泊,挨门逐户地潜进水里,从被泥沙掩埋的缸里囤里掏出这些失去了味道的粮食。
靠他的野外生存知识﹑勇气﹑药品,靠他的橡皮艇和一身游过长江﹑黄河﹑莱茵河和大西洋的游泳本领,还靠他的威严,玄若天机的说教,他成了这一带灾民的救星,传说中的神和至高无上的领袖。
他建立了“部落”﹑分配制度﹑劳动组织﹑秩序﹑甚至法律。
十几天来,他那本厚厚的防水笔记本剩得越来越少。
试验重点已逐步从“绿教”转到在毁灭中求生存的组织和方式上了。
他曾是一个颇为走红的小说家,投身绿色运动后便放弃前途无量的文学创作,只写理论著作了。
然而文学之火仍然时时在他心中燃烧。
无论用多么逻辑性的语言做记录或分析,他眼前出现的却永远是带着颜色和激情的图景。
无边的黄水在白色阳光下粘稠地伸展。
老鼠在露出水面的大片高粱穗上跳行。
抢捞浮财的盗贼枪口冒着青烟。
一船船刚剥下的死人衣服。
泡胀的尸体白发糕般变软腐烂。
今天,他看见一只来游览的船。
没遭过水灾的城里人一看见尸体便兴奋地大呼小叫,嚼着口香胶使劲照相。
一个小伙子问他撸了多少块表。
他咬牙克制着才没有把那混蛋掀下水。
他发觉环境刺激使自己有了过多情绪化的东西。
每当他划着橡皮艇给各个高地的灾民送去水底捞出的粮食时,那些可怜的人们围着他欢呼甚至跪拜,太平天国的诱惑就不断从脑海里升起。
他相信如果他把自己宣布为“绿教”的神,举臂一挥就能拉起一支百万灾民的暴力大军席卷天下。
若在一百年前,他会毫不犹豫地揭竿而起。
但是现在,他只能在心中感叹。
时代已经不需要草莽英雄,那种肚子逼出来的大军只能暴烈一时。
在他的生命中,义薄云天的侠客豪情必须让位给为人类挑起指路明灯的哲学思考,唯有把一腔滚烫的血强咽下去。
他只能想,只能写,至少是现在。
他不能与那些民主战士去分夺风采。
翻案也好,民主也好,谁上谁下,党派宪法,都是“炒锅”里面的事。
整个锅都要被砸烂了,都要被烧化了,忙着在锅里去抢几颗豆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历史要的是在升腾的烈火上安置一口新锅,把人间的一切重新铸炼。
他明白,历史已经给了他这个使命,那口新锅将首先产生于他的大脑。
毁灭来临之前做不好这口新锅,一切就将在烈火中永恒地化为乌有。
光线已暗淡得看不清笔记本上的字。
一弯细细的月牙在水面升起。
他看见男人蠕动的脊背,女人高举的腿,东一处西一处在微光下闪烁的皮肤。
随着天气好转,体力恢复,这几天男女乱交的行为越来越多。
他对此不干涉。
在他的笔记本上,详细记载的观察分析表明,乱交有利于目前这种部落生活的融合﹑协作和稳定。
相反,凡是夫妻同时在高地而不参与乱交的,都有明显的离心倾向,自私﹑算计,被集体排斥。
他准备好好睡一觉,明天要划一整天的桨。
他要回去了。
新的理论已经在头脑里燃烧。
他要赶回到北京的书斋奋笔疾书,回到陈盼的床上,回到咖啡﹑香水﹑电器与音乐的世界。
这里的人将自生自灭。
既然终将毁灭,既然只有毁灭才能新生,那就让毁灭尽早降临吧。
促进毁灭就是推动历史进步。
既然他们终将死,既然只有物质人的大灭绝才能为精神时代开辟道路,这些人的死就有了一种冷冰冰的命定,救他们就成了和历史背道而驰。
他打了个哈欠。
“城里大哥! ……”一个女人闷着的喊声从水边坑洼处传来。
他起身迈过迈过各种形态的性交者。
两个男人按着那个送饭姑娘的手脚。
另一个光光的男人正在往她身上爬。
“你们放开她。”他说。
三个男人吓得立刻站起。
“如果她不愿意,你们没有权力强迫她。”
中间那男人双腿打颤,阴茎抽得小小的。
“你们走吧。”他挥了一下手。
地上的姑娘抽泣着。
赤裸的身体在黑暗中像只白羊,只有两腿中间的三角区朦胧一团。
欧阳中华扶起她。
她紧紧抱住欧阳中华。
“……我还是个姑娘……我只给你……”她失声哭诉,像片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热的泪流在他胸上。
他的手沿着她的脊背向下抚摸,停在那圆润滑腻的臀部上。
他看向月牙,看向土地上沉溺在交媾中的男男女女。
他想,生命死了许多,还将再死更多……
March 28; 1998
北京
仅靠一个“逐级递选”就能改天换地,一百个字符就能把复杂万千的世界重组经纬,怎么也让人有说梦的感觉。
陈盼烦透了,虽然她经常受滋扰,已经练出一套“标准程序”,几句话就让多数纠缠者灰溜溜地走开,可架不住一会儿一个。
从十八九岁的小流氓到白了头发的老花花公子,全用不是看正经人的眼光色迷迷地打量她。
一个精心打扮的女人独自在公园里盘桓,很难不引起男人的非份之想。
陈盼后悔穿这件水绿色的丝绸旗袍,过于柔软合体,衬托出来的东西太多。
可欧阳中华教她要打扮得迷人。
“这是你的武器。”他说。
“你让我出卖色相! ”她当时撒娇。
“只有相,没有色。”他搂着她,咬她的耳朵。
“你的色只给我……”
天很阴,中山公园里的高大古树在灰色光线中像没有生命的布景,纹丝不动。
欧阳中华让她见石戈,却不许专程拜访,只能“偶然相遇”。
他常有这种令人费解而且似乎矫情的安排。
不管多古怪,陈盼全都照办。
她清楚欧阳中华对身份的注重,尤其和权贵打交道,绝不能有“求”或被“施恩”。
秘书也得遵循这个原则,何况她还是他的情人。
这使有些原本简单的事复杂了了许多倍。
欧阳中华已经走了这么多天,她仍然没见到石戈。
这个人似乎永不给人“偶然”,全部活动和程序都在硬梆梆的“必然”中。
她在那个没有出入证连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十六号机关外边连续等,直到感觉自己像个没人要的妓女,遏制不住地想放一把火把他烧得屁股冒烟跳下楼。
他凭什么睡觉吃饭一切全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