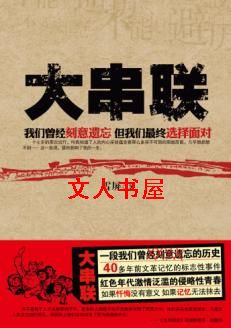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我听说他要举办个人影展,我很想跟着大家一起去布展,可是,走到展览馆门口,我又退缩了。
最终,郑建国的影展还是没有如期举行,原因是他死了,被一辆北京吉普撞死了,没等120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就咽气了,他的死简单而干脆,一点儿不拖泥带水。
我特别想知道在他即将要展览的作品中,有没有我们当年大串联时的一些镜头。
没人给我答案,只有郑建国自己知道,然而,他带着他的秘密走了。他大串联时拍的那些照片究竟在哪里,也就成了一桩破解不了的无头案了。
他有一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妻子。
从下乡的第一天他见到她第一眼开始,他就开始暗恋她了,他自卑,一直不敢跟她表白,整天陷入在痛苦的折磨之中,直到有一天,她掉进了冰河里……
她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这时候,他才向她倾诉了他的爱,她不信,怀疑他是出于同情,他就将他永远也不打算寄出的情书和给她偷拍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被感动了,于是,这段插曲就成了他们三十多年婚姻生活的前奏。据说他们俩和美半生,遗憾的就是没有孩子,但是郑建国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反而对妻子愈发的疼爱有加。郑建国死后,许多老同学纷纷前去吊唁,他的妻子居然一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这么多年,老郑从来没提过他的同学,问他,他也不说。郑建国究竟在回避什么?几个同学凑一块儿反复琢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白费半天劲儿。
我也琢磨不透。
他的葬礼我没赶上,等我知道了消息,已经晚三春了,这件事上,我觉得我挺差劲儿的。
想着想着,我竟睡过去了。
等我在汽车的颠簸中猛然坐起来,望望窗外,已经是转天早晨了,李全缃又变得精神抖擞了,车子开得很快,却也很稳。你超速了吧?我提示他。他回一下头,问道,醒了伙计?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黎彩英了。他说,怎么这么巧,我也梦见她了,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既聪明又伶俐。
是不是回到北京,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她?我说。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李全缃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俩推算,最多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结束这次旅行了。
你开慢一点儿吧,否则咱俩没等见到黎彩英,就先一命呜呼了,我警告李全缃。
你这个胆小鬼,一辈子都是褪着脖子做人,尽管李全缃嘴上在挖苦我,车速却明显地放慢了许多。由许昌到郑州,早已有了高速公路,原来的那条柏油路,已经不见了踪迹,记忆中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喜欢回顾往事的人应该知道,时隔多年再去访旧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它除了叫你失望,不会再给你别的什么了。我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心里满是苍凉。
41
郑州到了,你们快看!到中原这座中心城市已是黄昏时分。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登二七纪念塔,破电梯往上走的时候,钢筋嘎啦嘎啦响,我真担心突然断了,掉下去。不过,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能纵观整个郑州城,还是有豁然开朗之感,难怪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呢。郑州城的上空烟熏火燎,仿佛笼罩在一片浓雾中,大家俯视着它,默默无语,好像在观看一场黑白电影。我想,要是清晨在这里眺望日出,一定会更有意思些。下来之后,接下来要去哪里,众人意见不合起来,有的说该去洛阳赏牡丹,有的说要去开封寻找古汴梁遗迹,还有的坚持到黄河边上转一转,就回去,持最后这一态度的只有我一个。结果,我的意见被一分为二,到黄河边上转一转的建议被集体采纳了,而回去不回去就没人理睬了,给搁在了一边。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一班人摸索着找到了邙山,站在山腰上,极目眺望,黄河跟我想象得太不一样了,感觉很不真实,不免有些失望。
我想象中的黄河,应该是风在吼,马在叫,河水在咆哮,而眼前的这条河,太驯服了,太老实了,水流缓慢得要命,而且几近干涸,岸边露出很大的一片滩涂。哎呀,黄河怎么这样狭隘呀,我说。杨军说,它要真的发起脾气来,周围几百里就成黄泛区了。话是这么说,那些照相的、画画的都不怎么兴奋,既不照也不画,可能也觉得大失所望吧。有人唱起了《黄河谣》,杨军赶紧捂住他的嘴巴,这个歌不能唱。那人问为什么?杨军说,反动。那人不服,非要问,哪儿反动了?杨军说不上来,只是坚持说不能唱就不能唱。这些人马上分成了两大派,一派说能唱,一派说不能唱,鸡一嘴鸭一嘴地辩论起来。我嫌吵得慌,就走到一旁,冲着黄河拼命地喊了一嗓子,他们似乎觉得这样表达情感的方式更稳妥,比唱歌省事,也不惹麻烦,就都将两手圈在嘴边,跟公鸡打鸣似的叫起来,惹得其他人都拿白眼球瞅我们,还有人干脆捂住了耳朵,烦我们。
找到接待站,已经是夜色深沉了,好歹垫补垫补肚子,就匆匆召开个讨论会,讨论明天的去向,分歧依然,话不投机,很快就吵了起来,最后,只好举手表决,十七票支持去洛阳赏牡丹,九票反对,六票弃权,而我却没有参与意见,我总归是个外来人。
一个集体就这么轻易地四分五裂了,一部分去洛阳,一部分去开封,如果我想有人跟我就伴一起回北京的话,只有在弃权的六个人当中寻找了。可是,很遗憾,六个人当中竟没(W//RS/HU)有一位愿意回北京的,他们是玩野了。杨军挽留我说,跟我们去开封吧,人多势众,凑一块儿也热闹。我说,我着急,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告诉家里,他们不定多担心呢。杨军说,你要半道上给他们写封信就好了,生气归生气,但起码不着急了。我说,是啊,都怪我考虑不周。临睡之前,我谢谢杨军和杨军的伙伴在危难之中搭救了我,杨军说,谢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他乡遇故知,要是在北京遇见,还兴许会为你踩我一脚,你挤我一下,大打出手呢。我想想也是,什么缘由都没有,莫名其妙地就打一架的事情,不是常有吗?等我们俩困得实在是睁不开眼了,才睡下,这时候,天边早已经露出了淡淡的鱼肚白。
我是被人家揪着耳朵起来的,正在做着的梦,一下子都忘干净了。眼前是一群陌生人,杨军他们早走了。别再睡懒觉了,我们赶路赶得都三天三夜没阖眼了,让让地方吧,来人说。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说他们是锦州的。我说,锦州的也不能不讲理呀,他们跟我瞪起了眼睛,目光犀利得仿佛一把锋利的匕首,不讲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半梦半醒的我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胆子,梗着脖子说,我要教育你把军阀作风改正过来。对方啪地给我了一个嘴巴,我突然间就清醒了,脸色苍白,变得毫无血色,没等我及时作出反应,只见一个人跑过来,攥住对方的手,说了一句,有话说话,凭什么动手打人。跟着又转过身来,拉着我的手,把床让给他们,我们走。我们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才听见锦州人在后边说,有能耐别走,咱们比划比划。我们没有再答理他们,也没停下脚步,一口气跑出接待站。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助我一臂之力的居然是杨军的一个伙伴。我问他,你不是要去洛阳,怎么没走呀?他迟疑了一下说,我突然又不想去了。我问他,你是特意等我一起回家吗?他点点头,我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走出这么远来,所以……我赶紧说,我也是,有人做伴,心里就踏实一点儿。我们随便在路上吃了口东西,就奔车站方向走。走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其实,是因为我昨晚做了个梦,今天才决定回家的。我问他,做个什么梦,说来听听。他说,我梦见我爸我妈从农展馆的房顶上跳下来,跳下来的一霎,还在呼喊着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模糊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难受的时候,秀园总是羞我,我却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刚刚结识的朋友,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终于把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看我一眼,又赶紧将视线收了回去,对不起,他说。我极为勉强地笑了笑,没什么。
郑州火车站比我想象得要拥挤,要嘈杂,我们俩不再聊天了,因为在候车室里不大声喊,根本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突然,我刚刚结识的朋友咬着我的耳朵说,注意,有人跟踪我们。我一愣,谁呀?一颗刚落地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儿。我朋友警告说,别回头,一直往前走。我们快步走到候车室的一个角落,这里的墙壁上满是涂鸦,闪电般地一转身,跟踪我们的人正好和我们撞了个满怀,仔细一瞧,竟是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也许十一,也许十二,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十三岁。你为什么总跟着我们?我的朋友责问她。她说,我看你们俩像好人。我朋友不禁奇怪了,像好人你还穷追不舍?小丫头说,我想求你们帮助我。为了一探究竟,我们俩只好蹲下来听她说。她要我们把她带到邯郸,她奶奶在那,没人带,列车员不让她上车,因为她没钱打票。看她的样子,似乎不是在恶作剧。我的朋友征求我的意见,你看怎么办?我说,带上她吧。谁能拒绝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可怜呢?
她的眼睛就像个眼睫毛是粘上去的洋娃娃。我们俩将她夹在中间,挤过检票口,我们跟兔子似的跳上车,这年头要在火车上找个座,显然是妄想,我们没那样的野心,我们只想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有个立足之地就知足了。安置停当,我的朋友问小丫头,你去奶奶家,父母怎么也不送你?小丫头凄婉地说,他们都死了。明知道我追问下去,会勾起她一肚子的伤心事,可是,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他们是怎么死的?我问。他们喝农药自杀的,她说,之后就嘟噜着脸,不言语了。我的朋友比我还没眼眉,他补充了一句,你父母是不是出身不好?小丫头嗯了一声,他们说我爸解放前开过铺子,算剥削阶级,就天天斗他,押着他游街。看来,小丫头的父母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