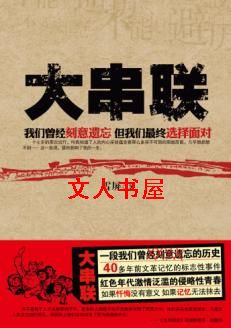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这个我不能要,我拼命地想把钱塞给她。
路上买个馍,喝碗胡辣汤,再打张票,这点儿钱怕是没富裕,穷家富路啊,她劝我说。没等我开口,曹大哥就用嘶哑的声音说,嫂子,我代这小子谢谢你了。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曹大哥的朋友说。他们两口子告辞以后,曹大哥望着我,又伸手摸了摸我的耳垂,小子,回去好好混吧,你耳轮大,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的眼圈里盈满了泪水,鼻子也一阵阵发酸。曹大哥说,别难受了,你小子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脆弱加上胆小。我说,我知道。曹大哥又说,往后你的性格得改,眼下这个形势,多愁善感的人可是吃不开呀。我一句话也没说,却使劲儿地点点头。
起床吧,第二天我还睡着就让曹大哥喊醒了。桌上早已摆好了火烧和浓稠的胡辣汤,是给我的。赶路要趁早,快点儿准备,曹大哥把我拽起来。
要不然,我明天再走吧,突然我有点儿不舍得他了。我的话曹大哥并没搁在心里,还磨蹭个什么劲,男人,做事就要讲究雷厉风行,他几乎是呵斥着我,把火烧吃下去,然后将我推出门去。
我沿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走,也不管它是东南西北。走你的,现在就只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嘱咐自己。但是,虽然一再给自己壮胆,我仍然摆脱不掉那种孑然一身的孤独,还有凄然和无助感。走来走去,我就走迷糊了。
曹大哥现在干什么了?我想。
屋子里光剩下他一个人转磨磨,腻味不腻味呀?
也不知曹大哥的朋友给他送吃的没有,桌子上倒是有块馍馍,可是咸菜吃没了……我走迷路了,干脆堵着人家门口坐下来。
嘿,好狗还不挡道呢,偏巧门里出来个闺女,比我大不了多少。
我挪挪屁股,给她空出走道的地方来。
你干吗堵在我们家门口啊?那个闺女掐个腰质问我。
我迷路了,我耷拉着脑袋,看也不看她,随口嘟囔了一句。
你是外地人吧?那个闺女上下打量了我半天,问我。我说是。她似乎很会察言观色,又问我,是北京来的?我还是说是。她很爽快地说,你把地址给我,我送你一趟。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曹大哥朋友家的所在地告诉了她。你等等我,她返身进了屋,很快就推着一辆自己用铁管组装的自行车出来,上来吧,她说。这辆车一看就结实,驮几口袋谷子高粱没问题。我跟骑马似的坐在后倚架上。坐稳了没?她问我一句。我嗯了一声。她脚下一使劲儿,自行车悠悠地蹬起来,蹬得飞快。
怕不怕,要怕的话我就慢一点,她挑衅似的问我。
这算什么呀,再快一点才好呢,我说。她就蹬得更快了,幸亏这个小城清静。
我走了多半天,她不到半个钟头就又把我送了回来,看来,这多半天我没少走冤枉道。
是这里吧,她把车子停下来。
不错,就是这,我跳下车,冲她摆摆手,谢谢你呀。
你怎么进去呀,贴着封条呢,她没走,指着门说。这时候,我才发现,不知多咱这个小院被封上了。我顺着门缝往里瞅,没见有什么异常,就拍打着门板高声叫喊,曹大哥,曹大哥开门。隔壁的院子的门吱扭响了一声,探出个脑袋来,向我招手,我走过去问这里发生了什么,隔壁住着个大婶,她把我跟那个闺女让进屋,小声说,一大早,来了一群带红箍儿的,把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把人逮走了。我问来的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人逮走,大婶说不知道,只知道是房主把人带来的。难道是曹大哥的朋友把曹大哥给出卖了?
我跟大婶说,我不信,我绝对不信。大婶叹息一声,你那个朋友临被绑走的时候,也是说他不信,他绝对不信。虽然我不敢相信,可是事实摆在这,又不能不相信。
他们两口子过来了吗?我问大婶。
来了,可是没进屋,两人就站在院子外头,大婶轻轻摇摇头,平时跟他们两口子来往,瞅着挺好的,知书达理的跟谁都和气,特别的讲礼貌。
他们俩就眼睁睁地看着朋友被抓走了,一句话都没说?我又问。
大婶说,人被抓走以后,那男的给了那女的一个嘴巴,女的就哭了,说你本来正被审查,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叫人家一连累,岂不是雪上加霜病上加病吗?也许我们这么一反戈一击,你就此被解脱了也说不定,另外,我也要替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原来,曹大哥朋友的老婆已经怀孕了!我历来最恨叛徒,不知为什么,我对她却恨不起来,只是想到曹大哥再次落入虎口,饱受严刑拷打、游街批斗之苦,不禁一阵酸楚,连宽慰自己的心情都没有了。小伙子,赶紧走吧,以后别再来了,这地方不保险,大婶提醒我。我条件反射似的点点头,疾步走出隔壁房间,仿佛危险随时会到来一样,到门口,我又站住,问大婶,他们动手打他了没有?大婶说,当时倒没有。许是心理作用,我心里踏实了一点,就怕他们把他押回武汉,我喃喃地说。到了街上,失魂落魄的我愣半天,等抬起头来,才发现那个拿自行车驮我来的闺女还在我旁边,眼神却不大对劲儿,冷飕飕的像一把刀子。我奇怪地问她一句,你瞪着我干什么?她把辫子一甩说,你心里明白。我更糊涂了,我又没亏心事。她怒冲冲地说,没做亏心事,干吗人家逮你们?我说,这年头,逮得人多了,你能确保他们都做过亏心事吗?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当然能确保,现在阶级斗争多复杂呀!我拍着胸脯说,你睁大眼睛瞅瞅,我像个坏人吗?她撇了撇嘴,又哼了一声,人不可貌相,满大街谁能一眼认出哪一个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你可以现在就去告我去,我被她的嚣张激怒了。
跟你说,告你太容易了,我哥就是造反骨干,她骄傲地说。
我浑身一激灵,刚才看上去挺顺溜的一个女孩,这时候怎么看怎么别扭,她脸上的线条太硬了,硬得简直没有一点儿性别感。她注视我的眼神,也充满了敌对,恨我恨得牙齿都在打架。我想,那时候的我们俩,就像一对随时扑向对方的饿狼。
你去招呼你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我说。心想,你只要一走,我就趁机溜号,叫你上天入地也找不着。
我才懒得跟你这号人较劲儿呢,她咬着嘴唇,把脸转向别处说,你赶紧走,要是不走,我真的叫人把你抓起来,顺便再告诉你一句,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叫什么名字,该死的我突然又好奇起来,问她,能不能告诉我?
你走不走?她恼了,真恼了,恼得以至于连脸上的雀斑都凸显出来了,你要是不走,我走!
我拦她没拦住,她骗腿上了车,脚下一使劲儿,嗖地蹬跑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便道,跟个痴呆儿童差不多。
我也走了,这个小城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我知道隔壁的大婶在透过窗子看着我,我故意走得从容不迫。
拐了一个弯,我突然就疯跑起来。我很怕,既怕逮曹大哥的那拨人来捉我这条漏网之鱼,又怕那个驮我来的女孩出卖我,正因为两者兼而有之,我就越想越怕。
跑得我实在挪不动步了,我才站住,弯着腰呼呼地喘,我想,我这时候的架势可能就更像个通缉犯了。远远的,过来一驾马车,车把式是个六十开外的老汉,他叼着个旱烟袋,连头都没抬他就知道我在瞅他,便从容地吆喝住牲口,是想搭车不?我嗯了一声。车老板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挪挪屁股,在车辕边上腾出个空来。我坐下去,两条腿耷拉着。车上堆满了鼓鼓囊囊的麻袋,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这是茶,这是刚当年的毛尖茶。
往什么地方送啊?我问他。他说送驻马店。我感叹一声,这一趟道不近呀。他说,可不。我又问,怎么不拿卡车送呀?他嘟噜着脸子说,卡车忙着斗人呢,腾不出时间来。说半截,他突然掉过头来问你,你这是——我迟疑一下,告诫自己说话要慎重,一旦露出马脚来后患无穷,就说,我来走亲戚。他哦了一声,愤愤地说,这人呢,度荒过去了没几年,刚吃上几顿饱饭,就又闹腾,厂子,厂子不上班,茶农,茶农不出工,忘了那些死去的人了……我不禁随口问了一句,谁死了?车老板说,死得人太多了。我又问,怎么死的?车老板说,饿死的呗。我的眼球转了转,说道,我听说度荒时饿死过人,但不知道饿死过多少人。车老板使劲儿吸两口烟,精神似乎进入了极度萎靡状态,饿死的人数我们这多,上边说大约有几万人,可是要我看一百万也打不住,谁家亲戚朋友没有饿死俩仨的?我不大信,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想谁要是告诉我这个,叫人知道了,非得把他抓起来不可,说他造谣。可是,车把式的表情又非常认真,不像是瞎掰。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怕惹祸,我决定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少多嘴,就说,我们把着眼点搁在往后。
这么折腾,车老板脖子上松弛的皮肤都涨红起来,往后饿死人还得多,不信,你就走着瞧。
突然,他望望头顶上的天,骂了一句操蛋,就把牲口赶到一片蓖麻地的边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要变天。我说,不会吧,青天白日的?他拿苫布将茶包都遮个严严实实,还拿绳子捆牢靠了。说话间,云彩果然上来了,远处已经传来隆隆的雷声,我指着前方说,那有个树林,到那避雨不是很好吗!车老板皱着眉说,你是想叫雷劈了咱俩?我傻了,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了。紧跟着就是电闪雷鸣,雨点劈里啪啦地掉下来,车老板从车辕底下抽出一块油布来,我以为他是给我们俩挡风遮雨的,他却给牲口盖上,宝贝疙瘩,你要是淋病了,咱就搁在半道上了,他对那匹老马说。
我们怎么办,难道就这么淋着?我想。车老板不知又从什么地方找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塑料布,抖开,铺在大车下边,然后钻进去,还叫我,快进来,别淋着了。我跟他一样,也钻到大车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