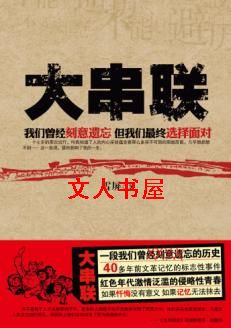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这时候我才知道奶奶抗战的时候,是个著名的堡垒户,那些八路军游击队的伤员都隐藏在奶奶家,到夜里,奶奶再将他们送到白求恩医院。那几年,奶奶救过的人有好几十位。可惜,奶奶在世时,从来没跟我讲过。她还嘱咐我爸说,就是家里再难,也不能去麻烦人家,人家现在都是公家人,忙。奶奶在乡下是五保户,国家该养着她,她却不干,我有儿子,又不是绝户,凭什么叫人家养着,于是,就到北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她没有城市户口,也就没有口粮,这些年,都是家里拿细粮跟街坊换粗粮,可以多换一点,奶奶总觉得拖累爸爸,总是能少吃一口是一口,尽量节俭,不糟蹋一粒粮食。我要是掉桌上一个饭米粒,奶奶都是赶紧捡起来,搁嘴里,对我说,祸害粮食是罪过……
奶奶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我扑在她怀里,拼命地哭,拼命地叫,奶奶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我说,别闹了,叫我踏实一会儿。我仍然哀求着,奶奶,你别走!她却再也没言语。那么喜欢训斥我的奶奶这次居然没有再训斥我。平时,我跟奶奶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嘴就没闲下来过,没完没了地骂我,好像每天不骂我一顿就睡不安生似的。我读书,她骂,骂我一个男子汉跟个娘们儿一样天天捧个书本,我说我爸我妈让我读的,她说读个屁,大了,就乖乖地给我当兵去,上阵打仗。晚上,作业没完成,我要拉晚,她就啪的一下把灯关了,不叫我点灯熬油,我说我要不完成作业,老师就要找家长,她说,让老师找我来,我是家长的家长。在她心目里,一个小子,不当兵,等于白活,读书做学问都是闲扯淡,见到戴眼镜的同学来,她就说,可惜了的,打枪连瞄准都不行了,废了。
我从小泪腺比较发达,一哭,我奶奶就拿脚踢我,谁欺负你了?她一边踢我一边问。我告诉她某某某抢我吃早点的钱,去买烟抽了。我奶奶从柜子里拿出我爸的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平时扎在腰上,遇见抢你钱的小子,就解下来抡他。果然,这玩意儿抡起来,呼呼带响,抽得抢钱的那小子哇哇直叫。后来,老师把我爸叫到学校,告了我一状,我爸回家找我算账,奶奶往我们爷俩儿当间一站,是我叫小磊这么干的,怎么着吧?我不能叫我们老石家出个窝囊废!我爸没招了,气得脸红脖子粗。我妈也不敢搭话,她一搭话,奶奶就说,这是我们老石家的事,外姓人少掺和。等时过境迁,我对我奶奶说,其实,你也不姓石,也算是个外姓人。她无言以对,干瞪眼说不出话来,突然脱下鞋来,照着我的屁股就掴打起来,我就拼命跑,嘴上嚷嚷着,没理了,就动手,算什么英雄。奶奶说,我十九岁守寡,一个人把你爹拉扯大,还娶了妻生了子,我不是英雄,谁还是英雄?我每年清明都去给奶奶扫墓,不知为什么,她越讨厌我哭,我就越爱在她跟前哭,只有在她跟前我哭起来才痛快,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冤,总是一齐涌上我心头。哭痛快了,我临离开奶奶墓地的时候,仿佛总能听见她咬牙切齿地说,小王八羔子,你是成心给我添腌臜,滚。我不禁破涕为笑,对奶奶说,叫我滚,我就滚,可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还来,还要哭一场……
35
树林里有一种带锯齿的植物,跟刀子一样锋利,谁挽着裤腿,谁的腿肚子就被刮得伤痕累累。
最惨的要数杜亦了,裤子被挂了个大口子,露出了屁股,臊得她赶紧蹲下来,找针线包,缝缝补补。
我们也趁此机会休息一下,背靠在大树上。
不歇还好,一歇下来,两条腿觉得又酸又疼,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折腾一晚上了,真想有个荞麦皮枕头,裹上一床续了新棉花的被子,睡一觉。想几点醒就几点醒。
嘿,下了这个山坡有长途车,负责侦察的杜寿林报告说。
我们强打起精神,穿过树林,往公路上赶。这里的长途车随叫随停,只要你招招手,车就停在你跟前,几乎没有进站出站的概念。在车上,我们才听售票员说,昨天有一队造反派,半夜去偷袭对手的司令部,结果人家早有埋伏,被人家一锅端,打得屁滚尿流,除了一个小头头,其余都被俘虏了。今天早晨一上班,造反派就把这辆车征用了,搜索偷袭他们的那个小头头。你给我闭嘴,再这么啰唆,我就不跟你一辆车了,司机冲着售票员直嚷嚷。售票员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吱声了。
我马上联想我们刚才碰见的那个伤者,就问售票员,后来,他们逮着那个小头头没有?售票员咬着我耳朵说,没有逮着,不过他们找到那个小头头的家,包围个水泄不通,只要他一回家,准得落网。难怪司机对这个售票员不满,她简直是太爱说了,唧唧喳喳,一刻也不停,仿佛是无所不知,幸好车上的乘客不多,除了我们十来个,当地人只有三四位,其中一位居然提溜着四只鸡,也许他是串亲戚去,我猜。车上的乘客来自四面八方,像她这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售票员自然消息灵通。
我说,那伙子老八路撤了没有?有个当地人问售票员。
没呢,看来他们是要在这地方安营扎寨了,她说。
这里有老八路?尤反修显然对这个心直口快的售票员颇有好感,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她问道。
这里有个老八路的公墓,解放那年建的,售票员说。
远吗?我们能不能去看看?杜寿林说。
远着呢,离这十几里地,又在半山腰上,售票员的话,仿佛一盆凉水,叫杜寿林打消了念头。
你们去了,也得叫老八路给你们赶出来,他们都拿着猎枪呢,听说枪法准得很,百发百中,那个当地人说。
谁招惹他们了?我好奇地问道。
造反派呗,售票员插嘴说,造反派说死者中有漏网的叛徒,要把坟刨了。
那些个老八路说,我们跟死者枪林弹雨里并肩作战过,谁是好人谁是坏蛋,我们比你们清楚,那个当地人又补充一句。
老八路们就组织起来,保护墓地,告诉人们谁敢刨坟,他们就跟谁玩命,售票员说。
造反派是怎么办的?我问。
造反派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老八路眼珠子都红了,真动起手来,崩一个两个也说不定,那个当地人说。
真是一物降一物,我想。假如我爸也遇到这种事,他会怎么样?为战友,他也会这么做。我奶奶在他十三岁时就把他送到部队上,他跟战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奶奶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
这群人也是老糊涂,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了,江晓彤说。我听他这话,觉得特别刺耳,就反驳他,要是没有这些老糊涂,你恐怕现在还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呢。
我又没说你爸,江晓彤还还嘴。
说谁也不行,我说。
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起来,争执得十分激烈,尤反修他们赶紧过来劝架,几个人拉着他,另外的人拽着我……
司机吱地一声踩了刹车。这时候,我们俩已经抱成一团,扭打起来,司机把车门打开,命令售票员,把他们都给我赶下去,出门在外还不老实。售票员还想替我们求情,可是司机毫不留情,连推带搡,把我们轰下了车,然后,一踩油门,汽车呼的一声擦着我们身边开走了。
我跟江晓彤相互对了对眼,突然一起笑了起来,尤反修他们以为我们精神分裂了,直瞪眼,我告诉他们,他们没管我们要票,我们白坐了这么半天。
可是,可是离终点站还有三站地呢,尤反修说。我说,我们不是还长着腿了吗?尤反修走了两步,突然转回身来,对我和江晓彤说,我觉得你们俩脸皮真够厚的。
跟你一样,我也这么觉得,江晓彤附和她道。
咱们的经费要是够用,打死我,也不耍这个滑头啊,我说。
下面我们还要脸皮更厚一点儿呢,江晓彤说。
你们还想做什么,尤反修警觉地问道。
偷棒子,烧着吃,当中午饭,我嬉皮笑脸地说。
你要是脸皮太薄的话,可以不跟我们来,自由行动,江晓彤故意这么对她说。
凭什么不带着我,我也饿着呢,尤反修说。
我们钻进玉米地,在地当央踩出一块空地来,点着了树枝子和半干的秫秸秆,掰些个头大些的棒子扔进火堆里,很快,玉米的香味就弥漫开来,闻着馋得慌。
柳纯沛又拿出本子来要写诗。
操,你真有两下子,做个贼你也要抒情,我冲他说。
我倒是觉得挺富有诗意的,柳纯沛兴致盎然地说。
烤煳的棒子,弄得我们一人一个大花脸,特别滑稽的是女生,都跟长出胡子来差不多,不擦还好,一擦竟涂得哪里都是,我们笑她们,她们也笑我们。
临走,打扫打扫战场,江晓彤说。
大伙儿一边把火踩灭,一边把踏倒的玉米扶起来,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咱们要挨家待着也不会招这份欠。
别得便宜卖乖了,我说。手脚麻利着点儿,要是叫民兵逮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扣咱一顶捣乱破坏的帽子,哥几个吃不了得兜着走。
大伙儿分头溜出玉米地,装作谁都不认识谁,各走各的,到了公路才集合起来,扎堆一块儿行动。
我爸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非打折我的腿不可。
我奶奶则可能会说,偷几个棒子,偷了也就偷了,总比饿着强。
柳纯沛说,我们现在算不算出生入死的阶级弟兄?有了这样难得的经历垫底,再大再厉害的惊涛骇浪恐怕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大伙儿平时听他说话都觉得云山雾罩,这句却中听多了。
行至荆州,我们遇到两辆大解放,见到我们,他们就在车上问,你们奔哪儿?江晓彤说,奔武汉。车上的人说,要是你们肯帮我们一点忙,我们就送你们去。江晓彤问,那要看你们叫我们帮什么忙了,提前声明,犯错误的事我们绝对不干。车上的人笑了,看来你们的觉悟不低呀,我们的条件就是沿路替我们撒传单,怎么样?我们拿起传单来,见上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