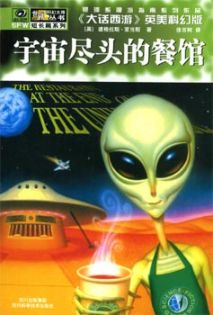卅街档案馆-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他连头都不回一下,大步流星地直奔小西天方向而去。我见他倔的像头牛,只好巅这碎步不停地围在他左右,连连说道:“班长,班长,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毕竟……”
郝班长见我絮叨不止,最后不耐烦地骂了一句:“你小子要是他娘的害怕,就给我滚回城里!老子今天是非去小西天不可!”
(133)
就这样,1946年大年初八上午,我在心里极其复杂的状态下,随着郝班长倔犟的脚步再次来到小西天山脚之下。那天的天空万里无云,像是一块刚刚织染好的新鲜蓝布。阳光涂抹在崇山峻岭之间,积雪变得不再那么汹涌,而是温和的如片片奶油。眼前的小西天山寨一团寂静,而我的内心显然无法跟这份景象匹配,它是否预示着暴风雪前的宁静?
让我和郝班长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放哨的崽子。这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前两次都是二膘子满面春风地相迎,这次就算没跟秦队长在一起,他们也不至于见人下菜碟连理都不理吧?我和郝班长又等待了大约十分钟,见仍然没有崽子出现,索性自行向山寨走去。沿路我们一直观察四周的茂密的树林,仍然没有见到半条人影。快要行至山腰的时候,我有些绷不住了,忙问郝班长:“我怎么觉得心里有些慌?会不是山寨出了什么事情了?”
郝班长停下身来,一脸疑惑的撇嘴道:“这山寨葫芦里卖的啥药哇!半个放哨的人都没有,这要是我军过来剿匪,还不直接端了他们的老巢?”
我和郝班长面面相觑了一阵子,下意识地把背在身后的步枪卸了下来,推弹上膛,端着枪继续缓步前行。这下气氛就紧张了起来。一点儿的风吹草动我们都要驻足停上一会儿,只是达到山寨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见半个人影。山寨寂静得像一具死尸一般,郝班长用力地咳嗽了两声——没有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连风都停止了吹动。
我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山寨跟我们离开时没什么两样,独独不见往日穿梭的人群——难道百十来口子人会无缘无故像水一样蒸发掉了?这个想法出现在脑袋里之后,我不禁自嘲了自己一下,这怎么可能呢?只是一夜之间,就算真的蒸发哪有如此迅速的道理?
郝班长缓缓走到一间屋前,伸手敲了敲房门,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郝班长看了看我,索性推门而入,门是虚掩着的,里边空无一人。我伸手摸了摸土炕,还有残存的余温。我们走出屋子,接连推开了七八扇房门,结果仍旧没有发现人的影踪。我想到了秦队长住的屋子,连忙逶迤地跑了过去,这次我在门前发现了一小撮已经干巴成褐色的血迹。我没有直接推门而入,而是用枪把虚掩的门缓缓地捅开,于此同时,我轻声叫了一句:“秦队长你在吗?”
我见屋里没人应声,索性走了进去。郝班长紧跟在我的身后,他冷不丁地拍了我肩膀一下,我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手中的步枪正顶住我的胸口。我不可思议地看着黑洞洞地枪管,张大的嘴巴里挤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眼:“班长,你……你这是?”
(134)
这份卷宗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我望着有些酥脆的稿纸上圆珠笔写就的最后的一个问号,足足楞了好一会儿。由于书写者的字迹多为繁体,我竟然用了差不多半个晚上才阅读完毕。我推开窗子,借着含糊不清的夜光眺望被烧得惨不忍睹的卅街,一种被阉割的情绪搅得我心烦意乱。四天四夜,卷宗里记载的内容到像是一段离奇的故事,而显得不那么真实。难道小小的通化城竟然有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
但是当我看着卷宗封面鲜红的“慎”字印章时,又马上否决了最初的怀疑。在鲜红的印章下端,透露了这份卷宗的一个关键信息:
本卷共(2)册 本册共(89)页
也就是说,这份卷宗本来有两册,而遗落在我脚底的只是第一册。那么,找到第二册不就可以知道最终的谜底了么?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深陷其中,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意已经被卷宗里的人物驱赶得支离破碎,秦队长、郝班长、冯健、黄三……还有小西天山二当家九枪八的枪法和满是脓包的脸,这些影像抓挠着我的床,令它变得咯吱乱响。最后我“嘭”的一声窜起身来,推开窗子抑制不住地吼了两声,对面的窗户马上亮起了灯,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汉子哐当一声推开窗子,手里拎着一把笤帚,指着我骂道:“这大半夜的你他妈的搁这得瑟啥呢?再嗷嗷我废了你!”我连忙合上窗子,直到天亮,我依然没有睡去哪怕一小会儿。若干年后,我回忆当时的那个夜晚,常常会想起街口妇人翻烙大饼的情景。
亢奋的情绪直到翌日仍然没有削减,那是我一天到我市公安部门上班。家里托了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废掉了好几沓“大团结”,足足跑了半年才弄到一个名额。我原本以为我就此便可以成为一名除暴安良、璨璨生辉的刑侦干警,手持五四手枪,头顶黑沿大盖儿帽,一扫从前吊儿郎当的形象。可是没想到,他们迎面给我泼了一盆凉水,擦桌子漆茶扫地晾抹布,没一样是我愿意干的。更要命的是,与我搭档的居然是一位瘪的像具干尸的小老头儿,整日满身酒味,浑身上下唯有那只通红的酒糟鼻子还有点生气。
队里的人都叫他老印,可是每次我跟他出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谁偷了谁的两块钱,谁往谁家院里扔了一只死猫,谁偷看大姑娘洗澡时,他都让我叫他印老。他说毕竟我是毛头小伙子,要懂得尊重前辈。我嘴上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其实心里恨得直骂娘。可是后来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伙计,最终帮助我找到了那份卷宗的第二册。
(135)
在此期间队里接到一宗案子。可能是警队长刚刚喜得贵子心情好,居然破天荒地让我和老印也参与抓捕疑犯的部署会议。由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临其境地面对命案,还像模像样地准备了纸笔,后来为这事我的老伙计没少嘲笑我。警队长大致陈述了案子的经过,在我市东山的防空洞里发现一具无头裸尸,死者是女性,作案者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一类的痕迹,只是在一堆焚毁的衣物间留有半截字条,字条上歪七扭八地写着一个地址。警队长将案子的材料给了与会人员人手一份,并言说要着重从字条上留下的地址入手,迅速出击,显我警威,三日内将真凶缉拿归案,狠狠打击隐藏在社会主义里的无良败类!警队长字正腔圆的信誓旦旦让我激动得坐立不安,而老印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打起了鼾声,结果我和老印被命令留守队里接听群众提供此案的线索。
如此得来不易,显我警威的机会就这样在老印的鼾声里报废了,我当然气氛至极。待警队里所有被安排任务的人员都行动之后,我一把薅起老印,不由分说地埋怨起他来。老印则睡眼惺忪地冲我摆摆手:“赫子,就算我不睡觉,队长他也不会给咱俩任务的。”
我一脸茫然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咱俩任务为什么还让咱们参加会议?”
老印咯咯直乐:“我来这里快十年了,队长换了好几任,案子却从来没有接过一个。他们信不过我,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他们已经把我这个酒鬼当成了一团空气,只要我不拿枪对着他们的脑袋,他们由着我做任何事情。”
我撇嘴道:“都十年了,你就没升个一官半职的?靠工龄你也不至于混这么惨吧?”
老印说:“这些不重要。当年我何尝不是像你一样意气风发,我是我们那一拨里边最有前途的一位,可是世事弄人,我也想不到我的下半生会是这幅德行,天天要靠酒度日。”
我在心里想老印说他意气风发?简直是个笑话!他那躬成虾米样的身子一阵风就能吹折了,他的唯一前途就是最终躺进黑漆的棺材板儿里。我打趣道:“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生活作风上的错误?”
老印被我逗得苦笑了两声,接着叹息道:“我这一辈子只稀罕过一个女人,此后就孑然一身了。要是我有儿有女,怕是也跟你差不多大啦!”
我见他有些感伤,但还是忍不住问道:“你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现在在哪里?”
老印指了指脚下:“好人,在这里睡着呢。”他顿了顿,似乎有意地想撇开这个话题。他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堆分发的材料,说:“你不是想破案嘛,咱们虽然不能亲临现场,不过凭着这些倒是可以分析分析。”
我不屑地说:“就靠这堆纸片?别扯淡了,我没兴趣!要破案得拉出去溜溜,憋在队里能找到什么线索?”
老印说:“笨蛋才不明方向就瞎闯乱跑。你想想,杀人者如果知道毁灭作案时留下的脚印痕迹,而且让警方根本找不到一点线索,这本身就表明他心事细密。这样的人有可能留下半截没有烧掉的纸条吗?”
听到老印这么说,我一下子来的精神,忙道:“难道你是说杀人者故意混淆视听,误导办案人员,以此赢得更快的时间逃脱?”
老印打了一个哈欠,面无半点惊喜:“我猜准了你会这么说。不过,我宁愿你没说过这句让我很失望的话。”
(136)
我被他噎得一时语塞,心想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竟在这儿跟我充大个,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于是我问道:“印老,那你说作案者留下这张纸条是为什么?”
老印捡起一张照片递给我,他说:“你仔细看看这具裸尸的照片,先不要急着回答我,仔细的观察看看有什么发现。”
我并不情愿地接过照片,潦草地用眼睛扫了两个来回,然后懒散地说:“尸体的脖子处伤口参差不齐,好像不是用刀切开的。身子上有一些细碎的抓痕,应该是跟凶手搏斗时弄伤的。除了这些真看不出还有什么。”
老印苦笑着摇头,突然说了句:“赫子,你就没有注意她的胸部吗?”
听到老印这么问,我心里想嘿哟你这老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