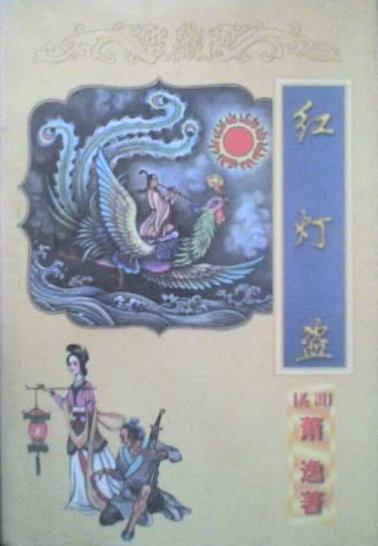红灯区的国王-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威德尔·埃彭多夫
译者:黄明嘉
声明:。
序曲
慕尼黑。春季,一个和煦的日子。大学区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傍晚,他们似潮水一般从各学院大楼里涌出。首批渴盼阳光的人已在街边咖啡馆占据了几张桌子,尽管太阳钻入云层后马上就显得阴凉了。
罗伯特·克朗佐夫上完了弗塞尔教授的民法课。该教授讲课讲得饶有兴味,让学生兴奋。但罗伯特的好友拉尔斯在上课时则感到紧张,脑子麻木得像双脚似的。他攻读法律完全是他父亲的心愿。父亲曼弗雷德·菲舍尔博士是汉堡声名卓著的法学家。拉尔斯好不容易挨过了课堂上的时光,现在终于可以同女同学调情,可以晚上约会了,这才变得活跃起来。罗伯特喜欢研究法律,喜爱法律那明晰而冷酷的世界。他想将来当法官,让法律发挥效力,控告所有践踏法律的人,把胆敢以身试法、干隐蔽和肮脏勾当的人全逮进监狱。
罗伯特在汉堡的圣保利长大,但他再也不想回这个地方了。他十六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波顿湖畔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父亲不希望他回家,包括寒暑假和圣诞节。假期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旅行去了,假如没有拉尔斯、菲舍尔博士及其第二个妻子蕾吉娜亲切邀请他到位于哈维斯吐德的豪华别墅去度假,那么,罗伯特就只得孤苦伶仃地留在人去楼空的寄宿学校里。夏季,两个小伙子完成了学校作业便在阿尔斯特湖上泛舟,要么从私家船库里用力推出赛艇来,然后在阿尔斯特运河里转悠数小时。当他们浑身湿透、又累又饿地回到家里时,蕾吉娜早就把晚饭准备好了。曼弗雷德·菲舍尔拍拍罗伯特的肩膀,称他是“体育迷”。
罗伯特十分钦佩这位律师。这正是他心仪的男子汉:光彩照人,深思熟虑,通达睿智,口若悬河,极富涵养。罗伯特决心日后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他的伟大榜样是曼弗雷德·菲舍尔,而不是自己那位专制的父亲。父亲是死顽固,是个没有幸运女神眷顾的赌徒,在圣保利,人们都叫他“色子鲁迪”。他拥有一幢老房子和一个表演脱衣舞节目的夜总会,名叫“蓝香蕉”。这是他生活的中心点。他是个不倒翁,生活艺术家,为人老奸巨猾,巧取豪夺,从不屈服,昂首挺立,备受三教九流尊重。但他同儿子却从未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父子关系。儿子不喜欢他,更谈不上爱他。
罗伯特又回忆起孩提时代。这回忆虽然有些退色,但仍旧历历在目。父亲根据自己的设想,试图把他培养成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还把这种培养美其名为“能应付一切生活”。
有一次,父亲卡住他的脖子往下按,并叫嚷:“你自卫呀,反抗呀,你,软蛋!”说得轻巧,做起来难,他气喘吁吁,以为自己快要窒息了。这个难于相处的人,偏偏就是他的父亲。
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在“戏台广场”附近的老游泳池把他突然推到水里。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茫然不知所措,在水里胡乱扑打,像丑陋的野狗行将被淹死。“你能游泳!哎呀,游嘛!”在喝下半池子水之后,他终于会游泳了。
这些回忆深深地扎根在他心中,有时,他真想学浑身湿透的鬈毛狗,耸身一抖,将回忆摆脱。然而,昔日的情景一再重现,尤其在夜间无法安眠之时。圣保利那种特有的气味这时会突然飘然而至,除了马路上雨水入口处的臭味外——那是天气变化的原因造成的——便总是弥漫着这种气味,即附近啤酒厂散发出来的麦芽浆的甜香。啤酒厂就位于繁忙海港的视线范围内。
圣保利——一种人生感受,一个品流复杂之区。妓女,老鸨,行凶犯,毒贩,敲诈勒索的歹徒,小市民,幕后操纵者;亮光闪闪的灯箱广告,潮湿的墙壁,墙纸上霉斑点点;小商人,离职的海员,没有任何幻想、靠终老财产过活的人,从海外漂泊来此的人——这些人一看便知其身份,他们颇感孤寂。当然也有能顶住风险的人:鼻子闻到的是鱼腥味,耳朵听到的是自由港传来的拖轮嘟嘟声,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故乡情感。总归是故乡,尤其是那幢房子,凸肚窗,窗上方的三角楣饰,还有大门上方那淫荡的霓虹灯广告——一只蓝色香蕉,分明象征着坚挺的男性生殖器。这夜间的色情灯箱标记倒映在被雨淋湿的石砌街面上。傍晚时分窗前呈现活跃的交际情景。可以清晰听到那些老练的讨价还价的话语,声音或高或低,取决于天气情况。女郎身上的吊带挎包就已给贪欲的嫖客以强烈刺激,接下来就是迫不及待的肉体交易。几百米开外的埃尔普大街旁停着大型冷冻车,内藏挪威来的鳕鱼、鲽鱼和鲑鱼,地中海区域的金鲭鱼,美国缅因州的活螯虾和大西洋沿岸产的牡蛎,一些寡言少语的工人对鱼类快速处理,容易变质的水产品必须冷藏。工人们系着油布围裙、脚穿胶靴在干活。他们中间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头发花白,蓄着山羊胡子。此人就是这个充斥鱼腥味地区的第一号人物,商业巨子。他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和以经营鱼菜为主的为数众多的餐厅。这个无所不为的大亨名叫格拉夫,是个不可侵犯的权威人物。谁胆敢忤逆他,必自取灭亡。他犹如一种隐性的威胁悬浮在空中,就是说,谁要做人,就得对他低眉顺眼。黑暗的仓库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它设在这幢庞大的建筑物里,楼房是砖结构,已经有些风化,像是为永恒设计的。大亨那四周全是玻璃的办公室也设在楼上。他在此运筹帷幄,指挥他的王国:众多的酒吧、餐厅和妓院。他的“爱神中心”与“色子鲁迪”的房子后院毗邻。
罗伯特的童年如何?窗前、窗内到处是妓女。她们在生意清淡之时,尤其在月末,就给罗伯特这个流鼻涕的脏小孩“启蒙”:“你还是处女吗?老实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看得出他每夜都干。所以,他也就不会做家庭作业,而且手无缚鸡之力!”她们开心,尖叫,小罗伯特则像一个被逮住的罪犯,脸红到耳朵根,哑然无语,浑身不自在。
凡是遇到问题的人都去找格拉夫。他好像无处不在,但又不大招眼。他是监护人呀,就这么个理儿。“色子鲁迪”十分清楚,钱,他不能捞得太多,赌博必须常常让格拉夫小赢,以照顾其情绪,这是立足于圣保利的最大保障。不遵守这一条,就得马上退出比赛,有几个人已被永远剥夺了参与赌博的权利。
老克朗佐夫就这样免遭灭顶之灾,从未沉沦过,也就这样悄然步入了老境。在绿绒毡赌桌旁,在那些吊灯拉得很低、空气里充斥香烟气味的昏暗后房里,克朗佐夫曾一再受到灭顶之灾的威胁。
有时,罗伯特晚间坐在大学生宿舍那拉低的台灯下,煞费苦心地攻读,也会想起妈妈。妈妈现在怎么样了?他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却不在,正如爸爸一样。他惟一记得起来的是妈妈吻他的情景,她那柔似丝绸的发辫把他的脸刺得痒痒的。父亲和母亲是在滑雪时相识的,妈妈后来随丈夫迁居圣保利。她在这个城区大概从来没有感到过快活,人们说她始终是个外乡人,没有融入这个社会。有一天,当小罗伯特放学回家时,妈妈已经离家出走了。没有留下书信和问候,带走的也只是几件衣服和首饰。银质大镜框内乐融融的全家福照片再也看不到了。她的香水在各个房间内还摆放了两天,这就是一切。父亲再也不谈妈妈,对妈妈讳莫如深。
罗伯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潜心钻研起功课来。他永远也不想回圣保利了,此外就是随遇而安,当然也期待着实现自己的梦想。
鲨鱼时代(一)
晚上,人们在特奥吐佩游艺俱乐部的绿色毡绒上掷色子。鲁迪·克朗佐夫最后只掷了个四点,真该死。他下的赌注是三万五千马克,后来又翻倍。可是在关键性的一轮中,他只掷了个四点!土耳其人梅默特却掷了个五点。鲁迪要是掷个六点该多好啊。
鲁迪脱掉茄克衫,把衣袖卷得老高,浑身大汗淋漓,用花围巾擦额头。他流泪了。昏暗的地下室,气氛残酷。
梅默特以怜悯的心态打量着鲁迪,一面收色子。在低悬的灯光里,梅默特小指上那质地纯洁的宝石熠熠生辉。
“先生①,鲁迪先生运气不好。”
①原文为法文。
他在德国虽然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说出的德语仍然差劲儿。但他却是个机巧的赌徒。人们私下传说,他是为格拉夫效命的,可详情谁都说不清楚。
赌桌边的第三者——白皮肤、淡黄头发的男子——沉默,发愣。鲁迪·克朗佐夫不认识他,此前从未见过面;这个陌生人问是否可以参赌,鲁迪同意了。陌生人开始时赢了,稍后又输掉了所赢的钱,在关键性的一轮中则放弃了参赌。
鲁迪站起来,十分疲惫。土耳其人对其仰视,愕然:“怎么,不想再赢回来了?”
鲁迪摇头。“今天够了!”他咕哝道。
梅默特将赌债相加:“七万。你,现在付?”
鲁迪·克朗佐夫转身朝大门走去,说:“下星期。”
淡黄头发的陌生人飞快地朝土耳其人丢眼色。梅默特从抽屉里拿出发票本,说:“行。你得签个字!”
鲁迪慢慢地转过身来,土耳其人举手,以示安抚:“别误会,鲁迪先生。这是规矩呀。”
鲁迪·克朗佐夫把身子沉重地支在赌桌上,呆视着土耳其人的脸:“钱少不了你的,梅默特。鲁迪·克朗佐夫从来都不欠债。”
他在欠单上潦草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哑然离去。
一个面颊凹陷的男子从隔壁的暗房里走出来,淡黄头发的陌生人向他微笑着点头说:“‘色子鲁迪’准保喘不过气来啦!”
圣保利无人知晓这个面颊凹陷者的名字,此人是格拉夫倚为股肱的左右手,是他的会计和心腹。大家都管他叫“耳语者”,因为他说的话全是秘密,所以总是对人说悄悄话。
土耳其人对“耳语者”欠欠身,以示恭敬。“格拉夫会满意吗?”他满怀期待地问道。
“耳语者”从他手里拿过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