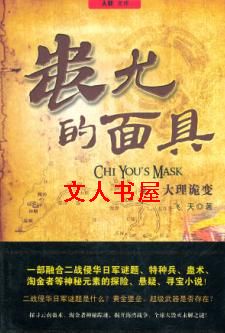流浪的面包树-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笑了:“我也没有自私到那个程度!”
“你还是不自私的。”我说。
“你也不自私。”
“太失败了!自私一点是比较快乐的。”
“就是啊!”
我们相望微笑。
然后,她拿起身边的鱼网,说:
“我们去捉比目鱼吧!”
我们赤着脚走到海里,月在水中,主宰着时间的流逝。在布列塔尼,人们喜欢把事情分成上帝做的事和魔鬼做的事,马是上帝创造的,驴是魔鬼创造的。太阳是上帝创造的,月亮是魔鬼创造的。那么,谁创造男人,谁创造女人?人也许是唯一有上帝和魔鬼合作创造的。我们既是上帝,也是魔鬼,在爱里,有时伟大得自己也没法相信,有时却自私得认不出自己来。
生命该是上帝创造的吧?那么,死亡便是魔鬼创造的了。据说,上帝根本是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意见太多了,常常拖慢了事情的进度。魔鬼独来独往,当他要带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或许连告别也来不及。
12
水上飞机在海面上隆隆起飞,离地愈来愈远了。
“好玩吗?”葛米儿问我。
我们坐在“海龟航空公司”一架只容得下四个人的水上飞机里作环岛游。
“我小时候常常玩的。”她说。
我们变成插上翅膀的鸟,在维提岛上空飞翔。
在斐济的许多天,并不觉得这里的人很多,可是,一旦在天空上往下望,却发觉海滩上挤满人,像蚂蚁一样,浮生若梦。
“演唱会的日子已经决定下来了。”她说。
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演唱会便意味着告别的时刻来临。
“没想到这么快可以再开演唱会!这一次,我可以唱《花开的方向》了。”她天真地说。
“是安哥的时候唱吗?”
“现在,这首歌又好像不太适合唱安哥,太惨了,我怕我会哭。”她朝我微笑,说:“假如林方文还没有死,那该有多好?他可以为我写一首美丽的挽歌,那样才算是完美的。”
“世事根本没有完美,追求完美的人,是很笨的。”我说。
她笑了:“你是说你自己吗?你一向也追求完美。”
“我是吗?”我惊讶地问。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笑笑:“所以我知道完美是不可能的。”
“你已经有一段很完美的爱情。”
“那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失去的,便是最好。”
“嗯,一旦离开了,便成为永恒。我也将要成(奇*书*网^。^整*理*提*供)为永恒。”她向往地说。
我笑笑:“真妒忌你啊!”
她笑起来:“你看我妈妈,满脸都是皱纹,虽然那些皱纹很可爱。可是,你们永远没机会看到我的皱纹,也不会看到我松弛的身体。”
“你再说下去,我都不想活了。”
“可是,这不是我的选择,就像出生一样,只是一个偶然。”她苦笑了一下。
黄昏的时候,夕阳没入海里,飞机开始降落。乍然回首的那一刻,我惊异地发现一张熟悉的脸。
13
海上有一只白色的小船,船里躺着一个人,全身素白,随水漂流。
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看错了。
我不也曾经以为坐在家里那把扶手椅上的人是他吗?
我把脸贴着窗,想再看清楚一点,那只小船却已经不见踪影了。
“你看什么?”葛米儿问我。
我回头,惊惶地告诉她:“我好像看见林方文。”
“在哪里?”
“我看到他在一只小船上面。”我朝那个方向指给她看。
她往下望,什么也没看到。
“现在不见了。”我说。
“你是认错人吧?”她说。
飞机在海面上降落,激起了巨大的浪花。一只白色小船来接我们上岸。
林方文怎么可能还活着呢?他已经活到永恒里了。
14
留在斐济的最后一日,我一个人来到那天飞机起飞的海滩。
飞机不见了,海上满是鲜花飘浮。这天是印度教的节日,人们按照传统把鲜花投向海里,鲜红色的九重葛、粉红色的木槿和白色的鸡蛋花,缤纷绚烂,铺开了一片放眼不尽的花海,人们在花海中泅泳。
我把怀中的鸡蛋花抛到海里,愿望它化成一只白色的小船,航向永恒的思念。
我那天见到的,也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恋恋不舍的鬼魂,在将要道别的时刻,回头向我淘气地叮咛,然后倏忽消散。
我在天上,他在海里,隔着无法触摸的距离,我们再道一声珍重,唤回最凄绝的拥抱。
思念,如同洪水,泛滥成灾。
他便是这么可恶,总是要看见我流泪才肯罢休,却不知道我已经长大了,不再那么容易哭。
他忘记了,在时间的长河里,他没有长岁数,我却没他那么年轻了。
15
日已西沉,人们陆续离开了那片花海。有人在海滩上点燃了一个个火堆,开始烧烤食物。在扑鼻的肉香之中,弦乐器与鼓奏起,打人与小孩一块儿唱着歌,跳着舞,庆祝一天将尽,明年再会。
一个鬈毛的混血小女孩走来拉着我跳舞,我们围了一个很大的圈,还有美国和日本的观光客,一起忘形地跳舞。
我踏着舞步,驱身在海滩上乱转。蓦然回首,在影影绰绰的人群里,我吃惊地发现一张熟悉的脸。
他在火堆旁边敲着鼓,快乐地唱着歌。
隔着明灭的火堆,我们诧异地对望着。他的手停留在半空,刚才拉着我跳舞的小女孩跳到他身上,勾住他的脖子,让他背着。就在那一刻,一个红发的外国女人走到他身旁,亲昵地揽着他的腰,吻了吻那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淘气地用一双手蒙住他的眼睛,他拉开了她的手。
在最后一抹黄昏的余光里,我们隔着的,不是火堆,而是数不清的前尘往事,关山之遥。
他窘迫地望着失落了灵魂的我。
16
葛米儿坐在房子前面的石阶上,看到了我,她站起来问:
“你到哪儿去了?我以为你迷路呢!”
“我看见林方文。”我说。
“你是不是又认错人了?”
“他在沙滩上打鼓。”
“你会不会是见鬼?”她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他没有死。”我说。
她吃惊地望着我,我看得出她是不知道的。假如她知道真相,也不会叫我来斐济。
“你是说他没有死,而且还在海滩上打鼓?”
“是的。”
“不可能的。”她摇着头说。
“不是不可能的,出事之后,没有人找到他的尸首。”
“你带我去看看。”她拉着我的手。
“他不会再留在那儿的,他已经发现了我。”
“会不会是人有相似?”
“你以为我还会认错人吗?”
看到他的那一刻,我也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男人,甚至只是幻像,然而,当他回望我时,不需要说话,不需要任何的证明,我知道站在火堆旁边的,是与我有过一生中最热烈时光的男人。
“你有跟他说话吗?”葛米儿问。
我摇了摇头:“他已经有太太和孩子了。”
“太太和孩子?”她张嘴呆望着我。
“嗯。”
“那个孩子有多大?”
“四、五岁吧。”
“那不可能,他失踪了才两年。”
“总之,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女人。”
“那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他做事还需要理由的吗?”
葛米儿突然说:“那不是很好吗?林方文没有死!他没有死!你不是一直也这样希望的吗?”
“可是,葛米儿,”我恼怒地说:“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17
空中服务员把机舱里的灯调暗了,人们开始睡觉。
葛米儿最后的话在我心里回荡,我不是一直也希望林方文没有死的吗?
他没有死,我应该觉得高兴,为什么我竟然感到失望,甚至愤怒和伤心?
我终于明白林日为什么给我一笔钱,说是林方文的心意,她为什么骗我说去印度却来了斐济。
她是唯一知道林方文没有死的人。
我替他想了千百个理由,为什么他要假装死去,可是,没有一个理由是我可以说服自己去原谅的。
我在天空上看到的,不是一个鬼魂。
我跳到海里跟我爱的人告别,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笑的痴愚?
我朝思暮想的人,原来早已经忘了我,快乐地生活。
我恨他,我恨那个活着的他。两年来,我的心里供奉的、那段永恒的爱情,在重逢的一瞬间,已经彻底地破灭了。
18
飞机徐徐降落在我熟悉的土地上,我却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从前的生活。
我提着行李回家,门开了,一张笑脸在那里等我。
“你回来啦?吃了东西没有?我炖了汤,还有鱼和菜,你一定吃不惯斐济的东西。”杜卫平滔滔地说着。
我放下行李,低下头找我的拖鞋。
“你找拖鞋吗?在你房间里。”他微笑着说。
“喔,谢谢你。”
我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你是不是很累?”他关心地问。
我站在那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回头跟他说:
“林方文还没有死,我在斐济见到他。”
他诧异地望着我。
我们无奈地对望着,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在车站分手的那天,我以为,当我回来,会有甜美的新生活为我敞开,他也是这样相信的吧?我们在思念里等待着。我以为,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再不会怯场,我们会热烈地拥抱。然而,到了最后时刻,这种欲望却又失去了。
“我肚子不饿,你自己吃吧。”我疲倦地说。
19
我拧开门把,赤脚走进房间,扭亮了那盏等我归来的灯。
灯光下,我惊讶地看见了满床的粉红色毛拖鞋,一双靠着一双,全是一个样子的。那粉调的颜色,甜蜜了夜晚的房间。
一阵鼻酸涌上心头,我掩着脸,伫立在床前,无法描绘那种复杂的心情。
20
天渐渐亮了,睡眠就像往事一样,慢慢而无奈地漂来,我倦倦地合上了眼睛。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我走出客厅,拧亮了灯,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杜卫平说,他会离开几天,没什么的,只是很久没有放假了,很想出去走走。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