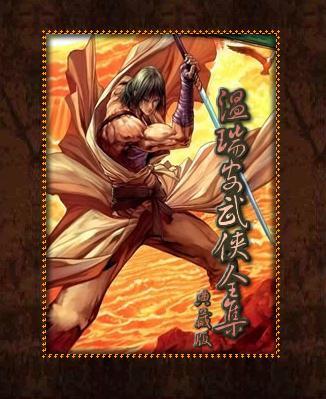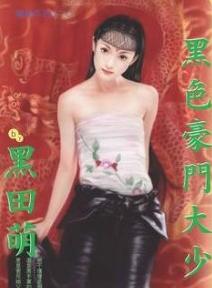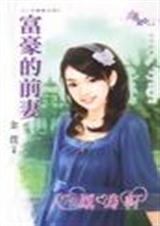民国大文豪-第1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直接把国防力量拱手让人,中国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
林子轩来到北平的时候,北平的报纸正在热议此事,一致反对日本等国的无理要求,抗议日本等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有人提出废除和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段祺睿政府则采取妥协的态度。
林子轩只有一声叹息,**可欺是西方列强蛮横霸道的根由之一。
他来北平一个是陪着冯程程故地重游,见一见往日朋友,还有联系一些作家。
推向西方社会的第二套新文学丛书以出版诗集和散文为主。
新月社是一个以诗人为主的文学团体,徐至摩和闻易多都是这个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这件事交给徐至摩处理,选出两本个人诗集和一本新诗精选集。
按照林子轩的意见,个人诗集要具有个人特色,也就是说诗人自身要有特点,而精选集则要具有时代特色,选取的诗歌最好能反应这个时代的声音。
他倾向于徐至摩和闻易多的诗集,一个是自由主义诗人,一个是革命主义诗人。
至于郭沫偌的《女神》,太过自由奔放,恐怕西方人不容易理解,还是算了吧。
在散文这方面,他有几个人选。
周作仁的小品文不可或缺,朱自青和郁达浮都是散文大家,他希望沈丛文写一些有关湘西的散文游记,带着奇特的地域色彩。
这些人的散文各有特色,有文化、有历史、有情怀、有感悟,包罗万象,熔于一炉。(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六章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北平还是那个北平,不过林子轩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子轩了。
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
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讲了一通大道理,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
这样做并没什么错,他和徐至摩是同学,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
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但礼不可废,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尊老是中国的传统。
这一次,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却和蔼可亲了许多,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
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浮浮沉沉数十载,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
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改革派。
时代变迁,几十年过去,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
这几年,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宣扬传统文化。
1918年,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
于是,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
在这方面,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
他愿意提供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
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
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担心林子轩太年轻。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特意叮嘱一番。
“我活了这么多年。看明白一件事,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都有私心,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梁启朝总结道,“不要相信他们,咱们还是要靠自己。”
林子轩点头答应。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是国家之间,利益才最重要,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
他和徐至摩离开。
经过年前那场“联俄仇俄”的争论,徐至摩名满京城,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
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
在《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后,徐至摩沉稳许多,做事更为内敛了,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
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误导青年。
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说出的话更有分量,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越是如此。越要谨言慎行。
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
此人叫做李达钊,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
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并写有《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让他压力倍增,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看一看,过悠闲的二人世界。
只是,这个想法有点奢侈。
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
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
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
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
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
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侃侃而谈,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
那些旧日的小姐妹,命运各自不同,有人如意,有人落魄,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感慨不已,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各种攀比和炫耀,令人不忍直视。
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
相比较而言,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
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
有了第一套新文学丛书的出版,他有了底气,虽然不算成功,但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影响。
不少学者都想搭上林子轩的关系,也能在国外风光一回。
所以,这一回林子轩颇为强势,要求所有的翻译工作都要交给万象书局来做,这是担心出现上次林羽堂的事情。
万象书局要成立编译所,招揽翻译精英,这批丛书刚好作为考题,来考核翻译者的水准。
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不仅因为和老三周建仁有过矛盾,还因为《现评论论》和《语丝》之间的论战。
《语丝》是周氏兄弟的地盘,《现代评论》由万象书局出版,林子轩最终定稿。
两本杂志都是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它们之间的论战不仅有个人的矛盾,还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和政治观点的不同。
《语丝》和《现代评论》都不是革命文学。
《语丝》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
《现代评论》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两者其实都提倡“自由”和“独立”的创作态度,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
林子轩一向抱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周作仁的散文写的确实好,这就足够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七章 血色黄昏
在北平,林子轩见到了孟晓冬。
两人吃了顿饭,聊了聊这大半年的生活经历,孟晓冬显得更为开朗和自信了。
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见识了外边的广阔世界,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孟晓冬在北平受到了欢迎,获得了成功,成为了真正的名角。
一旦出场,都是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
事实上,林子轩对她的情况了解的更为详细。
孟晓冬身边的两位精武体育会的女保镖会不时把消息传到上海,林子轩也会嘱咐北平的社会名流们对孟晓冬照顾一二。
她虽然名气大,但在刚开始演出时同样遭受过排挤。
比如排演的时候不合作,在服装和道具上做手脚,还有饮食方面故意刁难,放入辣椒等对嗓子有害的佐料,更甚者直接在舞台上耍花招,让人出丑。
在戏曲这个竞争激烈的行当,这种小动作是常有的事情,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微型的江湖。
别看名角们在戏台上光鲜,被观众追捧,台底下照样遭罪。
孟晓冬梨园世家出身,自幼在戏班生活,见惯了这种勾当。
如果在上海,她有自己的班底,对身边的人知根知底,在北平,她是个新人,周围都是陌生人,自然受到挤兑。
对你好的人不一定是真心对你好,对你冷漠的人或许才值得相信。
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都需要一场场打拼。
孟晓冬性子外柔内刚。不轻易服输,她等待时机。抓住他人的把柄,给予致命一击。从而树立威信,让别人知道她不是好惹的。
“北平太乱了,还是回上海吧。”吃完饭,林子轩劝说道。
冯羽祥的国民军和张座霖的奉军迟早会分出胜负,以后的北平并不安稳。
“再看看吧!”孟晓冬不置可否道。
他们走出饭店,在大街上看到来往的学生,这些学生举着标语,抗议日本军舰制造的大沽口事件,抗议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
在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