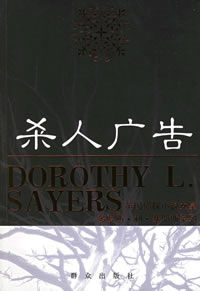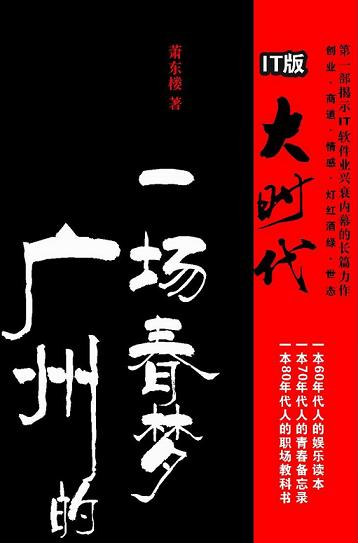逃离北上广-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是历史形成的,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说。军队宿舍的住房相当宽绰,将军多半住小楼,至少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也“不同凡响”,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当时二环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三里河地区是机关聚集区,房子好,住房也好,过去是最好的区。”任志强回忆说。
对于各个机关、单位“跑马占地”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王军的《城记》中这样写道: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新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们的社区——大院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社会的主体。
大院文化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
北京城的大院长久以来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云路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和作为“京都三部曲”的前两部《昼与夜》、《衰与荣》,才真正将高墙后面的北京揭开了一角:大院里的北京。人们看到了进出于大院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厅里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运筹帷幄,干部子弟的家庭沙龙,作家、记者、艺术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层北京的众生相。
大院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学校、科学院各研究所、剧团、医院等等。部门大院是本部门职工的集中居住区;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独立空间。
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力图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就相对较弱。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将之称为“本位主义”或“部门所有制”,但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部落主义”,应该说颇为传神。
围墙封闭的广大院落内,居住人数上千人至数万人不等。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设有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等等,有的则还设有幼儿园、小学、医院、粮店,以及邮电局、书店、储蓄所、附属中学、派出所等等。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单位包下,几乎都可在大院内得到解决,大院居民可以长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19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关于大院的“闭塞”和相对这座城市其他建筑而言的“难以包融”,《城市季风》一书中写道:“围墙所体现的戒备、排拒和防范心理,不能不说是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的文化遗迹,与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为比较,上海的围墙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较为低矮、单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篱笆是墙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华东局和市委机关大院、淮海路的宋庆龄宅邸也均为竹篱。与密不透风的水泥墙比,它显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大院不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承载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果不拘泥于大院的地理分布和各种具体差异——它至少包括胡同中的“深宅大院”、旧城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城外具有综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说,大院同时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区”,从中生长出的,是与胡同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异的“大院文化”。
等级和资历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杨东平这样介绍:“和四合院各种身份职业的居民杂处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他们在大院内的聚居方式并非在社会流动和迁徙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资历和等级分布。这在部队的院落最为显著。有将军楼、校官楼等等,以及与干部居住的楼房相区别的普通工作人员居住的平房。”
“工作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既添加了较多的人际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间添加了较多的工作和等级关系。同事关系转化为邻里关系,但这主要是‘同质邻里’,即资历、地位、年龄和住房条件相当的一批人。参谋和干事的妻子互相引为知己,正像大学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互为邻里。邻居谈天的重要内容,是一轮大院(单位)内部的人事;邻居的造访,很可能是次日的会议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级很少到上级领导家去串门;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邻里之间仍以职务相称;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长也要敬礼致意。”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