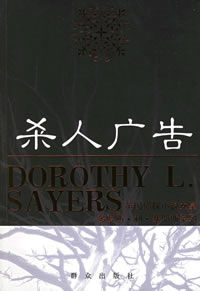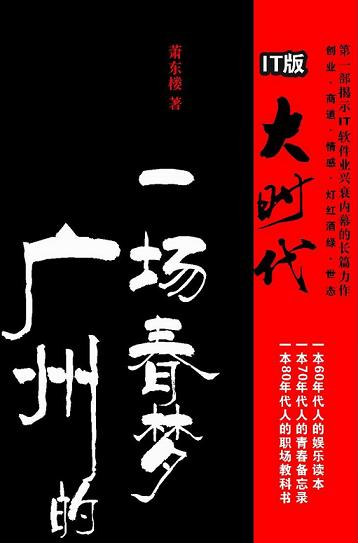逃离北上广-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服务落后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窜上来了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徐坤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