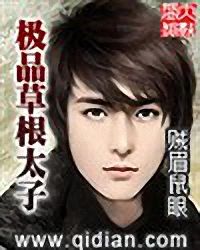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初中生”,虽说只念了一年就“文革”了,还比宋奎福只念小学一年级更有学问。加之宋奎久天生就喜爱和电打交道,电还真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一次,他私自安装了“电子防盗门”(自己做的,一开门灯就亮),被大队发现了,罚了款。可他痴心不改,继续“玩电”,不想因祸得福。
大队原来一个电工,玩不转日趋加剧的用电新形势了,就要增加一个电工来减压。老宋头听说后,经过上下打点,宋奎久当上了电工,也看他真能担当得起。
电工是棵摇钱树,也是聚宝盆。自己家用电随便,分文不拿。电炉子、电水壶……别人家用是要罚款的,变压器的容量小,上下都有规定,电工是特权阶层,没有人监督,何况监督者的耗电量比他还厉害啊。电工从各家齐上来的电费有数,上缴的也有数,前面的是大数,后面的是小数,差数就是电工的了。如果觉得差数太小,那么就提高每度电的基数,落到千家万户,可就是个大数了,剩下的差数自然不是小数。各个大队的电工都比着看谁的差数大,比来比去,电费就上去了,最高一度电2元4角钱,老百姓叫苦不迭。
那么,群众有反映,大队、公社就没有人管管吗?管!
大队书记开会了,说:线路不好,电损太大,此其一。二,五保户、困难户拿不起电费,大家摊,自从办电就是这个法则。三,上边要的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他说的话就是电工教他说的,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大队的会计,都和电工一样享受“优惠”,包括电工的至亲等等。他们的屋子比谁家的都亮,心比谁都黑!这就是农村高电费的根本原因,最高的村,一度电7元钱。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满地,刘二堡人要争气”,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家乡有了个体业户,用电项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工就更吃香了。谁家有事你得排号等电工,七碟八碗地伺候着,不然你还想用电不?
这年秋天,稻子黄了,金灿灿的,到处是一排喜悦情景。一些想干点大事的农民们,钱还没到手,买卖就开张了。老王家的酒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鞭炮齐鸣。为了快些把电送进酒厂,宋奎久在王家吃过晚饭,摸黑就去变压器合闸。
“酒后干事胆子就大,夜黑人静啥也不怕”,这话是说给做贼的,但让宋奎久实行了。他刚上变压器,头部就触到了高压电源,脚就接了“地”。刹那间,一声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宋奎久当即身亡,时年不到30岁。
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一声喘息,只见得老老少少不住的叹息和哽咽。
老宋头老两口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搓揉得半痴半呆,恍如夜游。没过一年,他去了,老伴也投奔了女儿家,儿媳领着二个孩子再婚,家破人亡,各奔他乡。
宋奎久死了,宋奎福来吊唁,也来调研。到了现场,他什么责难别人的话也没说,只是哀叹:“唉,挺聪明个人,怎么会干出这么傻的事来……”
宋奎久死后,埋葬在沈北大提以北一片荒从中,坟前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刘更彪之墓”。死后的他还了原姓原名,留下的两个儿子还小,依然姓宋。
大凡在大队混点差事的人,都算是“公务员”,所以不能白白地搭进一条性命。何况宋奎久为人很好,有求必应,他死后,两个孩子由全大队要养活到他们18周岁。
诸多农友曾经携手并肩,“生死与共”情谊难舍。话说回来了,共患难却不能同享福,他们大多说都是天年未尽身先死,死得不值,实在是可悲。李志民、李玉民死在麻将桌上,逍遥了自己卿卿性命。王凤成、王凤祥死在突发疾患,是落后的农村医疗条件,没给他们宝贵生命延续的条件。李风仁、宋奎久死得更惨烈,是无知与愚昧终止了他们的生存。呜呼,活着的人在哀叹,也在庆幸,庆幸死里逃生。可是,一想起往事,庆幸还有几分值得庆幸的了?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同行诸友。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3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人一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已是黄金时代的大半生了。所谓黄金时代,就是体现人生价值,用服务社会来衡量的吧。这样算来,我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会计、团总支书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年。对于我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