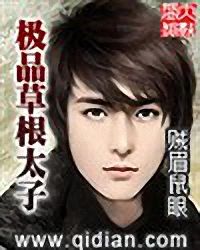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暑假了,我不再去团山子小学了,也没有见过王小孚,就想去看看他。谁会想到,还没等我迈出家门,西邻王小孚的伯父伯母就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问过才知道,王小孚淹死了。他和一帮孩子到辽河滩一个水泡子洗澡淹死的,已经有两个时辰了。听后,我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要去看看他,听人说他就躺在那个水泡子的岸上。我没有去成,早就被母亲看死了,因为我也去过那个水泡子洗澡。我们就这样生死永别,阴阳两世。
他的伯父伯母一生没有孩子,指望他日后养老送终。他走了,他们怎么会不哭得死去活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伯父伯母也带着悲伤离开了这个人世间。王小孚的哥哥后来我也认识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我想王小孚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和他回忆起王小孚,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慨叹了,是无情的时间磨去了悲泣,留下一抹深刻的记忆。
1 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1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深刻的记忆,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王小孚那一幕,就像大树的年轮,只要你活着,记忆就不会空转,一圈一圈地随着你的年龄生长着。
7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人们还没有扛着锄头下地,噩耗就沸沸扬扬了——刚过40岁的孟祥弟死了。我“啊!”的一声,不知所措。
孟祥弟父亲的舅舅,是我的姥爷,也就是说,他父亲和我母亲是亲姑表兄妹。孟祥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我叫他的父亲大舅,大舅叫孟繁文,别看他识字不多,但编歌谣可有一套,一套一套的,流传下来很多,可惜我手头上没有。大舅的手很巧,给丧家扎个纸人纸马什么的非常逼真,靠这一手也能挣个零花钱补充家用。
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孟祥弟也是会计。他没念过初中,但和我大舅一样的聪明,在众多会计堆里也算得上佼佼者。那时的大舅很称心,觉得孩子的对象不会发愁,会计在农村也是个文化人嘛。
到了“文革”的“文功武卫”的乱世之秋,心情平静的大舅突然间坐卧不安了,因为孟祥弟的心骚动了。他不甘心做他的会计了,凭他“里面三新”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偷偷地背起了枪,参加了“文功武卫”大队。
队员们整天荷枪实弹,镇守着公社大院,还真的与沈阳方面窜来的造反派交了几次火,幸好双方没有大的伤亡。但是,罗家房地区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战场了,人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大舅才知道孟祥弟原来是“文功武卫”的队员,日日夜夜为他忧心忡忡。他可是大舅的独根苗啊,说啥也得把他整回来才能安心。于是,大舅谎称病危,托人捎去口信。
孟祥弟请了假,一进屋就被大舅骂得狗血喷头,这才绝了他危在旦夕的险境。回家后,孟祥弟还留恋那里的生活和“前途”。他说,在“文功武卫”队里,猪肉粉条子、大米白面堆着吃,万一能闯出一条路来不比当会计强吗?
大舅听说他还没死心,也没动声色,使出了一条“美人计”。
第二年初春,大舅开始为他操办婚事了,企图栓住他的心。
爷俩原来住两间小草房,准备给他结婚就又接了一间,不然住不下。大舅求我来帮工,我和孟祥弟用手推车运土运石头,那时年轻,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告诉大舅,千万别做好的吃,这就是我答应帮工的条件。我们是实在亲戚,大舅也很实惠,没有买肉,我也不会喝酒,每顿饭都是秫米(高粱米)干饭,副食全是玉瓜英子炖豆腐。我想,只要能给大舅省俩钱比什么都好,办喜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吃喝算什么。来之前,妈妈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些年来,妈妈没少帮大舅做针线活,大舅也帮我们干很多妈妈不能干的庄稼活。
早年间,大舅家很穷,是姥爷出钱给大舅娶的媳妇,不想,大舅妈早早就死了,我还没有出生。姥爷为他的外甥操劳一辈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世了。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这些往事,我心甘情愿地帮大舅的帮,也是在帮姥爷的忙吧。
孟祥弟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大舅对我很好,喜欢我老实,说我憨厚。大舅会种香瓜西瓜,瓜熟了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随便地吃。每每想起那年那月,心里依然甜滋滋的。
过年的时候,苞米花是孩子们最好的小食品了,妈妈舍不得花一角钱的手工费,我就去雪地里捡崩飞的苞米花(现在也叫爆米花)。大舅看了过意不去,就帮我捡,他还对崩苞米花的人说:“你就不兴往雪地里崩一锅吗?让小孩子过个年!”
五一前,孟祥弟结婚了,也结束了20多年由男人操持家务的历史。嫂子很贤惠,对大舅就像对自己的爹那样。大舅整天就是一个乐和,他有了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孟祥弟的负担也一天天的加重了,忙得脸都没有功夫去洗,累得比原来的个子又矮了许多。他就是在劳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心有不甘,孩子仍是“嗷嗷待哺”阶段。嫂子不得已改嫁了,为了孩子。
多舛的人生,奈何又遇上了多舛的社会?“文革”的动荡,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人的生命就显得脆弱。同孟祥弟一样,郭祥玉在他死后的第五个年头,也瞑目于黄泉路了。
在孟家窝铺时,我家住在后街,郭祥玉、孟祥弟住在我家的前街,他们是邻居,郭祥玉居东。两家住的都是马架子,窄小黑暗,开门就是炕,冬不暖夏不凉。1954年,兴修辽河大堤时,孟家窝铺等七八个村子都搬迁到大堤南,他们两家也分开了,但住的很近。1960年,我家从外地搬回了德盛堡,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才有机会见面。
德盛堡,是个新村屯,是原来大堤外各村屯居民杂居的新村,有月牙河、孟家窝铺、董家窝铺、桑树子、王家街……几个堡子的人都到这里定居。
孟祥弟比郭祥玉有心计,日子还过得那么寒酸。郭祥玉是个“死做”的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少点理财算计的门道,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年不如一年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读书、住房、婚姻……哪笔开销能省得下?那笔开销不是天文数字?他忧虑成疾,先是双目失明,后来百病缠身。45岁的时候,他的生命之光彻底地失明了。他的死,虽然用不上“英年早逝”,但也是“年轻少亡”了。
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玩,他从来对我们都是“逆来顺受”,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忠厚老实人,有口皆碑的宽容风范。可是,上苍上天对他太不宽容了,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一生没有平安,天理难容啊。
比起这些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在我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我够幸运的了。我往往以自己“苟且偷生”来慰藉自己的幸运,痛苦和失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
1 同窗学友(诤友诤言)(3)
1957年秋,我再一次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新安堡小学转学到郭家沤麻坑小学读书。这里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很远,好像在西天边上,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到有些闭塞与原始。虽然我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和我的“家乡”大不一样的,处处感到既陌生又很新鲜。
学校没有新安堡规模大,学生老师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是五年级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所以我是1958年第一届毕业生。
来到生疏的环境,我没有生疏感,新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很快就有两个好朋友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思去结交的朋友,是按大人们的朋友概念相处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叫郭志彪,另一个是孙方举。
郭志彪,和我家在那家窝棚的房东都姓郭,但读音却不一样,郭志彪的“郭”读“国”,是第二声。
那家窝棚的房东是老哥俩在一起过日子,守着一棵独苗郭洪奇;郭家沤麻坑的郭家,也是老哥俩守着郭志彪一个男孩,真是巧合了。郭洪奇和郭志彪一样的“悲伤”,小时候母亲就没了,而他们俩的个性却有天壤之别。郭洪奇,从小就娇生惯养,对同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在新安堡念书时,郭洪奇住西屋,我家住东屋,许多事我都由着他,我们之间没有友情可言,倒有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感受。当我们都为人之父了,才都各有所悟,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像是久别的同胞亲近不够。可那时不是,同屋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努力用功。在新安堡小学时,我受郭洪奇的影响,很贪玩,学习稀里糊涂。和郭志彪交朋友,我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上进了。
1957年冬,我约他去辽河西岸的山上玩,他答应了。小时候我就爱爬山,姥姥家的背后就有七星山,我常去那玩。现在离姥姥家太远了,远得看不见那山了,有些思乡,思念姥姥……
郭志彪嘴上答应我了,但他迟迟不肯动身,直到做完了作业,我们才起身成行。过了几天,他主动要和我去“老背河”,我早就心驰神往那个地方了。“老背河”是辽河的故道,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冬天的冰面很很透亮,可以看见很深的河底都有什么,夏天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完成作业!
和他玩了两回,让我回味无穷,受益匪浅。如果说,直到现在我依然注重学习的话,那么,这功劳就归属我的学友郭志彪了。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位诤友了,没有他的诤言与熏染,我绝对考不上初中!
郭志彪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直接被新民六中录取为保送生。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奇#書*網收集整理,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员,是他考虑伯父伯母父亲年事已高,快点就业,少拖累三位老人。
直到1969年,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