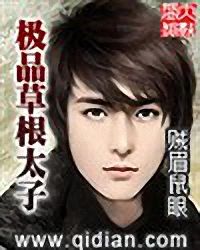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说也好,“那你就和我一起去吧。”
他笑了,知道我的秉性,从来不主动也不愿意和领导单独对话。
我们只有三四分钟的谈话,寒暄的话还没有说完,刘书记有“客人”了,我顺便告辞。
那几年来,乡里的财政很是紧张,常常不能在正常的时间内开资,或做其他的事情。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招待费过高,二是地税收缴甚少。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各村欠乡里的“统筹款”迟迟不能上缴,积累过多,积重难返,形成了奇怪的恶性循环。最初是三两个村欠账,后来变成了七八个村,互相观望,“先进吃亏论”嘛。这笔帐是贾书记王书记当政时欠下的,人混熟了,脸上都是“磨不开”的肉,你能把我咋的,咱不是哥们嘛。
难道贾书记王书记就真的不想要账吗?非也!这笔钱用处大了,干部开资不说,敬老院那么多的老人就是靠它生活,许多公益事业都靠它维持发展,一刻也不能推延。村里不给钱,只好由乡里“垫付”。乡里哪有钱啊?借!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了,怎么办?要!可是,讨要归讨要,不给归不给。但是啊,讨要不能白讨要,不给不能白不给,都是公家的钱,好好答对答对“帐主”就是了,这一年就算过去了。下一年再要,再不给,再答对……讨要者、欠账者都相安无事地过太平年,丰衣足食高枕无忧的太平年。
到了刘书记年月,乡里的欠账就成了“债台高筑”,要账的困难用一个“难”字来形容太不够分量了。刘书记为了打开“钱”的被动局面,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孤注一掷”地跟欠账叫板了。“孤注一掷”,是拿自己的乌纱帽做赌注,要不来钱,就走人,反正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出路被高筑的债台堵死了。
刘书记的招法是:根据村干部工资偏低的实际情况,先制定一个调资的文件下发到各村,从来没有过。村里的书记、主任、妇联、治安等一干人马,像看天书似的琢磨着文件中字里行间的分量与含金量。其实,“分量”和“含金量”好比权利与义务,好比投入与产出。含金量俨然是座金山,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把它背回家里来。不管怎么说,困难是有的,钱途是光明的,不由得你不动心去试试……再说了,别的村能做到,咱们差啥啊?干!
随之而来的,刘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内容只有一个,落实文件精神,限期半个月交齐所有陈欠——统筹款。他说,账是我的前任欠下的,但我这一任一定要收回!希望大家打消侥幸心理,你不要说什么困难和原因,我也不听。难道老百姓没有向你们交纳提取吗?没交的你们为什么不去要?钱都哪去了?你们收你们应该收的钱,我收我应该收回的钱。这好比香港是满清政府欠下的“债务”,江泽民难道就因为不是他的责任,就放弃收回主权吗?
到会的都笑了,笑得心服口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多年的遗留问题迎刃而解。
4 如毛的上司 (作茧自缚)(15)
4如毛的上司(作茧自缚)(15)
“言必信,行必果”,作为领导,做到这一点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现在都讲“忽悠”二字,没有人相信领导说话会算数,也不在乎了,你干嘛去认真。但细想起来又不难,有什么难的呢?说话之前好好搞搞调查,做到心中有数,说自己有把握的话,打有准备之仗,难吗?比如说,按农村生产规律和上级心理轨迹,秋收结束之后,农田基本建设这仗就得开枪了。年年如此,年年市里都要为各个乡镇下达作战指标,劳民伤财,收效甚微,又年复一年。
1998年秋末,刘书记和市里摊牌了:罗家房乡受自来水水源地的影响,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不是防涝而是抗旱,所以,市里给我们下达的治涝工程的土方任务我们不打算完成!别看上级瞎指挥,那你也得听,刘书记的话他们能愿意听吗?刘书记也清楚,但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吧,领导怎么会“不听”,无可奈何也得听!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难能可贵!“言必信,行必果”,那年的农田水利工程我们一锹没动。
作为领导“近君子,远小人”更是难得,有谁不愿意给自己戴高帽啊,虽然是小人之举,但舒服。自古以来,怕是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别人为他抬轿子戴高帽的,何况那些小人对抬轿子戴高帽之能事练达得很。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少不了这样的人,对此可以随时随地淋漓尽致地大显身手,且不遗余力。前面说的那个打了饭碗子的,同乡政府大院拜拜的那位,其小人之能为可谓登峰造极了。自他到乡政府以来的几年间,所有的领导,只要是他认定有用者,无一逃出他的手腕,而被抬得晕晕忽忽,捧得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任他颐指气使。在外人看来,他就是领导的上司,就是领导的爹。他对领导说话可以不讲什么分寸,也可以大大咧咧地“顶撞”或戏谑,也可以拍拍他们的肩膀。而对于没有实权,没有用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你跟他打招呼,他用嗤之以鼻来回应就算很够意思了。他的为人哲学可以用四个字来浓缩:现用现交。
他基本上是和我一个时间来到乡政府的,比我年少。开始时,干了几年临时工,是个通讯员。后来,“抬、戴”之术屡见奇效,平步青云,捞了个民政助理的肥差,有了“抬、戴”良性循环的资本。
罗家房算得上地灵之所,到这里任职的主们,个个都会被灵气陶冶成“人杰”。可惜的是,好多历届领导等明君,个个被这个“八千岁”玩得俯首帖耳,俯首称臣地替他效劳尽力,但也有例外者。
新的党委书记驾到,机关中人人皆拭目以待,看看他在这个“重头戏”面前又是如何粉墨登场,又是如何地收场的。
第一幕叫“亮相”。领导去哪了,靠灵敏的嗅觉他都能找到,争取第一个得到接见。很多人还是头一次见到刘书记的时候,人家刘书记就叫他“王哥”了。那种亲近之情、密切之容,构成了一道别人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没有你插足的机会。亮相,就亮出个“狐假虎威”的效果,亲密无间的形象。
第二幕叫“入戏”。对此,时尚有说法,称之为进入角色。刘书记手头有一条烟,挺“冲”,他说他不敢吸,那“冲度”相当于60度老白干烈性酒。八千岁听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随即接过话茬儿:“给我吧!”
刘书记自己不用,还有人喜欢它,他不会吝啬的,也不能当面不给他面子,这条烟就成了八千岁的了。这也是他入戏演出“一箭双雕”和“一石二鸟”的剧目。其一,众目睽睽,都看到了吧,我们的关系如何?非同小可。我虎口拔牙如同探囊取物,不可小觑。其二,礼尚往来之渠道被烟疏通也,这就叫“欲取之,先与之”日后我好投桃报李,顺理成章。
其三叫“谢幕”,惊诧的谢幕。刘书记“送礼不收,溜须不受”,令机关上下惊诧不已,也叫八千岁十分惊诧啊。刘书记牺牲了一条烟,坏了八千岁的千秋大业。他觉得,恍惚之间天地都变了,屡试不爽的万应灵药失效了。他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好大的一把“米”。这“米”就是他的饭碗子,身怀的绝技,露馅了,演砸了。从此,人们的心病不治自愈,眼前一亮,再也不怕得罪了八千岁而激怒领导给你小鞋穿了。所以,他们敢在机构改革中毫不违心地给八千岁打分,“穿小鞋”,致使他一败涂地。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被时代的潮流卷到浅滩上成了沉舟,一个机关的股长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地上而爬不起来。这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
那么,他是怎么入党的呢?答案是,几经周折,几多坎坷,才终成正果。
机关支部大会和支委会多次讨论他入党的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愁煞人也。欲进不能,欲罢又不忍,愁坏了两个人,一是八千岁自己,一是那时当权的党委书记。领导思来想去,觉得既然对他有了承诺,就该负责到底。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领导动用了他的权威,暗示机关支部负责人专门找和八千岁过不去的两个人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两个人抵挡不过这种干预和压力,违心地扮演了“月下老人”的角色。八千岁入党大业就是在领导亲自指导和策划下进行的,完成的。八千岁对此很是懊恼,入个党咋就这么费劲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还不如不……他认为,党不党的没关系,只要我和说了算的拥抱在一起,任何死神都不能把我从“得意”中抢走。
在他为人处世哲学地指导下,我行我素,义无反顾,怎么可能去反思自己的“失误”啊,怎么会理解什么叫自我检点啊!这回机构改革他傻眼了,头头脑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寡不敌众,无力回天。唉,作茧自缚,咎由自取了。
5 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
1958年初春,大跃进的号角刚刚在农村吹响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叫王胜岩,是我们这里“乡镇”一级的大人物。那时公社还没成立,更不能叫“乡镇”。当时“公社”一级的地方政权称之为“区”,后来又叫“作业区”了,他是作业区的首脑人物,我听大人们说的,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看外表,他人很老了,其实那时他也就30多岁,但在小孩子的眼里他就是老头。“王书记”衣着简朴,腰间经常系个麻绳做腰带,和我的邻居老头差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老革命、老八路、老资格,没有一点架子,基层的干部都围着他转,神圣、威严。
等我到公社当临时工上班的时候,他在我们公社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待不住,就做机关的常客。有时候晚上没事可做,我们常在一起打扑克,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一些了解。
王书记头脑很机敏,扑克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