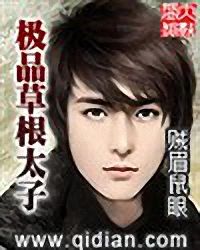草根家事-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书记呵斥。
“碍事叭啦的,总往这溜达啥?”
“曹书记,碍什么事了?有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党员,咱们村有几个?”
我看不过去,连说带笑地诘问他说话太不尊重人。
村上的报纸多得是,真正看的真就没有几个人,挑点花边新闻看看,闲聊有话题也就是看报纸的宗旨了。
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书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狱回来就喝。什么酒他都敢喝,贫下中农的喝,满月酒也喝,甚至“地富”的酒也敢喝。他不怕“混线”,我是书记我怕谁?
刚从监狱回来喝,尽人理解,结束牢狱之灾值得庆贺。后来接着喝,人们更是理解,老婆回来了,大喜。
他在监狱时,老婆不能养活一帮孩子,“嫁人”了,和本队一个姓朱的老光棍同居多年。那时的人讲良心,老婆“不愿意”离开姓朱的,说那是忘恩负义。姓朱的满脸的皱纹,形体猥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怎么和潇洒倜傥的张书记相提并论啊!后来经热心人说和,彼此都解放了“传统守旧”的思想,破镜重圆啦。
再后来的喝酒,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几起几落,致使他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走出如何做人和做官的怪圈,烦闷又苦恼,唯有“借酒浇愁”。他真的很后悔,后悔走错了许多步好棋,心甘情愿地整过好多好人。在喝酒的言谈中,他想过向人家赔礼道歉,但清醒后就推翻了。他说,道歉是无济于事的,“疮好了,疤瘌还在。”下野后,他消沉了许多许多,自以为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枯竭,更是想以酒来激活仅有的一丝希望,他希望历史重新再来!
历史不会再来,生活却在无情地延续着,就像他一天到晚的程序——
无论是生产队时的“大帮哄”,还是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以后,张大叔都是早上默默地去地里干活,晚上悄悄地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生怕有人来讨债似的。那是他很少喝酒了,体力难以驾驭酒力,囊中羞涩难以沽酒,几乎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天地。
没过几年,他和老伴都得了慢性疾病,个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自己的责任田也无力经营,够得上“几块疮痍,几多疮疤”了。村党支部,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很关切,时常给予一定的补贴。怎奈他的困难太多太大,这些有限的输血难解他越烧越旺的“心火”,有限的补救仅仅杯水车薪而已。有道是:输血不如造血,世界上一切繁荣与昌盛,没有一样是输血创造出来的。张大叔已经没有造血的机能了。
期间,我去过他家两次,其捉襟见肘的拮据令人生怜。那时候我正处在“草房+学生=贫困”的尴尬中,对他无力支撑,只能“同病相怜”,好言相慰让他鼓起勇气了。后来我不想去了,也没有再去过他家,他见到我那种内疚之情让我坐立不安。
人为什么要自责呢?又为什么要记恨呢?我没有丝毫这样不人性的闪念,因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电影”既已上演完毕,背景还那么重要吗?“小鱼泛不起大浪”,我们都是“小鱼”,就不要苛求那惊涛骇浪把你冲向何方,受到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劫难,只留下那么一个疮疤就够了,忘却疼痛的好,更不可耿耿于怀。面向未来吧,那才是你的力作,才是你新的一页。
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老伴到乡里请求救济,每次都是我帮她把事办完,再安排她坐车回家才做我的事。这时的张大叔已经过时了,他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大连的外国语学院,那就是张大叔能延续生命的一根稻草。
他的小儿子很出色,毕业后的工作也很好,时常把钱寄回来,补贴家用。张大叔的那一丝希望终于变成一缕曙光。遗憾的是,“曙光”的前程是多彩的光亮的,对于张大叔来说,却是反照的回光。
1998年,我到曹家村搞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时,在一片荒岗上见到了张书记的坟冢,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卒年月,镌刻着一个难以诠释的人生。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老伴也入土为安了,我才想起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心中不禁惨然。
2 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 温文的上司
和厉害的上司相PK,教育圈内我的某些上司,可以用温文尔雅来评介,尤其是我初次接触到的教导主任,王驱虎老师,他是界内界外人士公认的好人。但是后来一提起他,无不为之扼腕唏嘘,遗憾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在旧社会和刚解放时的农村,还是习惯把老师称为先生的,特别是上些年纪的人。“先生”,是不是“先知先觉”“先生一步”的本意我不知道,反正在百姓的心中,是知书达理满腹经纶的圣明贤达之士,王驱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0年9月1日,我当上了民办老师。那时的二道房学校,有好多的民办老师我都认识,公办老师没有几个,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的老师。丁钦忠、邹和昌、谢长柏、李志民、李玉民、王玉杰……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是新民六中的校友,相居很近,时常见面,彼此还会陌生吗?所以我迈进老师办公室的门,他们自然热情十分,把我介绍给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握手。
王主任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脸膛白皙,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和颜悦色地向我交代工作。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工作”,接着则是打听我的一些近况,又说明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等。
总之,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欢迎”我,才懂得人格是那么的贵重,受到尊重是多么的荣幸。我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是客套话,但绝不是言不由衷地迎合。
时间长了,我对王主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竟然有一个比我还辛酸的历程。
王主任原本姓高,名叫高明铎。父母过世后,他成了一个孤儿,年幼的王主任被好心的高家收养了。高家老两口无儿无女,视他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念书,终于成为一名师范毕业的人民教师。
感叹老天不公平,好人不长寿,高老头夫妻俩命薄福浅,刚见到东方喷薄日出,就双双驾鹤西游一梦千秋了。幸好王主任毕业了,不然这个独根苗的吃喝穿戴将如何打点啊!
王主任出身贫寒,吃得苦耐得劳,且又根红苗正,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入党提干了,是“文革”前的党员。那时的老师中有几个党员啊?全公社200多名“臭老九”中,党员人数不过四五名吧,那是相当的奇缺,珍贵。在很多人的眼睛里,王主任的政治资本得天独厚,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艳羡。他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显身手扶摇直上,他却选择默默地耕耘属于自己那一块田亩,心无旁骛。因之,不少人都为他惋惜啊,说他白白地放弃了大好的机遇……
王主任本分也本质,是他放弃机遇的主导。这样的“机遇”在清醒人的眼睛里是这样解释的:
他深知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愿意充当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
此说也有道理,也算明智之举,明哲保身也是人生上策,明智人不会做无谓的牺牲啊。
是的,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无作为就是大作为。在“文革”中王主任没有沾上一滴血迹,依然一身洁白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有口皆碑。
王主任对他的属下一贯的“温良恭俭让”,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他那张脸犹如一幅画,一幅“笑画”,一年四季没有丝毫的怒目相视,什么人见了都是那样的笑容可掬。
1971年,王主任被提升为公社教育助理。我们相处一年多相互感觉甚好,在那种轻松的氛围中,更多的愉悦色彩,应该是王主任的热心所浸染。
1976年,我去了公社做气象员的时候,王老师转任“知青办”主任了。就是因为管了知青,有些事儿他自己就说不清了。
知青办主任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新来的知青到条件好的大队插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老知青或回城或升学;还可以把国家下拨的建青年点的资材,根据特殊情况由他酌情分配……所有的“情况”,都要由主任去定性,来定夺……
就在王老师主持知青工作的期间,他家盖起了3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祸起萧墙”似乎顺理成章。
新的砖瓦房,在那时的农村可谓金碧辉煌的景观了,谁看了都会说“这家真有钱”啊!下一句就是“钱从哪来的?”的疑问。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千元户”都是大海捞针,盖这样的房子,岂是千元户的“消费”?别说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就是大队公社的干部对此也要划个问号。
问号划在脑子里,拿不上桌面,这倒更糟糕,没有办法把这个问号从每个疑惑人的心中抹掉。抹不掉的问号就是个肿瘤,会致人于死地。正是这个问号,把王老师拖进了下坡路。
领导永远是关怀同志们的。听到那么多的非议,公社的领导决定对王老师先行转移,省得肿瘤转移要他的名,就把他转移到了曹家中学当了老师,不做领导了。
他走了,“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乱用职权”的“控告”也转移到“无声无息”那去了。
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