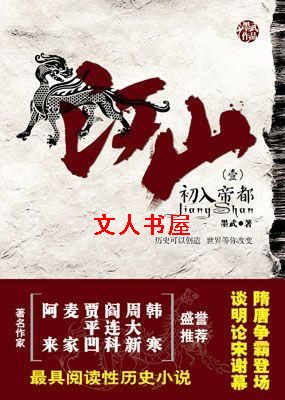目迷美色-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才光明正大的来。”
聂娆沉吟了一会:“我们家也是两个孩子,我爸妈白天上班,我哥就带着我,也不怎么管我,他和男同学看鬼片非把我拴在身边逼我一起看。他们一帮男生看完吓得出门倒水都不敢,抽了半天签把我推出去了。可在学校里真有被哥罩着的感觉,到后来,他也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何齐锐关了水,两手在抹布上抹了抹:“我小时候可没欺负过她,齐柔这姑娘从小就爱撒娇,惹人疼,就是玩心大,喜欢凭着聪明做事,自制力差了些。”
聂娆看着他那表情,想说什么,最后又没说。
收拾完厨房三个人去外面转悠,院子周围的地界荒,平时就人迹罕至,到了除夕,更是家家户户都守在电视机前看没什么新意的晚会节目。
那里面出场表演的,都是熟人,更没看头了,一说买烟火,何齐柔比谁都跑得快,一马当先冲出屋,何齐锐在门口给聂娆胡乱围了一圈围巾。
不知道哪里好笑,两个人傻兮兮的对着乐了一会才出门。
买了烟火和廉价的香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而行人看不清他俊朗的面孔。
马路不是很宽,三个人权当散步,何齐锐咬着烟牵着聂娆,令一只手替小姑娘拿着一把仙女棒,小拇指上还勾着一袋杂七杂八的爆竹。
何齐柔在前面蹦跶着开路,想玩了,踮起脚拿他叼在嘴间的香烟,用火柴棍点燃,自娱自乐,一路上都很开心。
何齐锐的手很暖和,聂娆被他很自然地牵着,看着前面跑得很快的小女孩问他:“过了年六月份她是不是就要高考了?”
他语气平平地陈述:“去年她考过一次,自己觉得成绩不满意又来了一年。”
聂娆问:“差多少?”
何齐锐说:“二十分。”
她叹了口气,觉得有些可惜:“平均下来没门也就三分多,耽误一年。”
白色的雾气从他鼻孔和嘴巴里冒出来,他看了眼不远处欢乐画着无穷符号的何齐柔:“也就一年,没什么耽误不耽误,她是接受不了,安慰的话是说给已经放弃的人说的,心有不甘的人不适合听。”
一步之遥,擦肩而过,不是三言两语的安慰就真的能获得解脱。
话音刚落,何齐柔风风火火跑过来,从他手里又拿了一支,引燃以后就跟着他们慢悠悠走,静静的,再没有离开。
她好些年没玩过这些东西了,自以为沾了聂娆的光,高兴的劲头很足,拉着聂娆往她手里塞了一支。
聂娆难却盛情,驻足路边,停下来把手里的仙女棒燃完。
何齐锐满目柔情地看着笨拙地挥舞火花的聂娆,和在一旁大咧咧做指导、笑得两眼弯弯的妹妹,六年来,头一次觉得这么美好。
回去后,俩人真要睡一屋,何齐锐让聂娆先去洗澡,他去收拾东西打地铺,何齐柔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凉拖鞋捐了出来,意味深长地偷笑。
冬天冷,头发也没什么油,聂娆冲了一会就出来换他去洗,进屋以后看了看他打的地铺,底下是一床垫絮,草草铺了一层,连床单都没有,上面摆着枕头棉被。
发着橘黄火光的电火炉摆在旁边,一不小心就会踢到,这么简陋的条件,她怎么好意思让他睡地上。
过了一会何齐锐进来,只见她坐在床边,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看不出脸上写着什么。
他一笑:“怎么了?”
聂娆挣扎了一会,心一横,硬着头皮道:“你别睡地下了,我不介意和你挤一挤,上来吧。”
第二十九章
何齐锐先是一愣,随后当真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还坏心眼地凑近,玩味地勾起嘴角:“这么主动?”
明明是她体谅他,这人反而倒打一耙,聂娆一下就没了恻隐之心,踢踢他的腿:“我改主意了,你睡你的地铺吧,我怕你晚上睡觉不老实。”
何齐锐不服气:“你这是不信我能把持住,我又没有前科,你怎么不信?”
聂娆拟着他的得意之色意味深长地还击:“你想到什么了,我是怕你晚上踢被子牵连到我。你说我第一次来你们家做客,一晚上就感冒了,那多不给你面子。”
要比成熟稳重,何齐锐未必逊色,脸上掩饰得天衣无缝,笑了笑,渐渐离开:“睡吧,晚上要起来别磕着绊着。”
他想拥有她,但不是今天,也不是这种场合。
聂娆看着他,顺着他的话保证:“不会踩到你的。”
何齐锐朝地上看了一眼,瞧着电火炉说:“我是说它。”
片刻沉寂。
何齐锐轻车熟路地关掉灯,火炉的光微弱,却足以把整个房间照亮。
聂娆缩进被子里,他也掀开地铺躺了进去,寂静的冬夜里,屋舍的火炉旁,他们没有耳鬓厮磨一番云雨,而是沉默地陪伴和呵护。
睁着眼,听着自己的呼吸,聂娆有些难以入睡,翻了个身,看着面庞被火光照得精致光鲜的男人。匀称的身材,紧致的腰腹,结实的四肢,还有五官勾人的脸,她看得入神。
不因美色为他吸引,却因外表为他着迷,心跳都快了半拍。
过去也有人追求过她,或是一味付出以致自我感动,或是利用道德约束捆绑,或是奉承逢迎太顺她心意,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与她相似,充满共性,都精于人际交往间的分寸进退,都有不可言说的坚韧隐忍,有着相似的苦衷和操不完的心。
尽管今天一来二去他还是睡在了不怎么舒服的地上,可是她记着了,他曾为她付出。
这时,床下的人忽然睁开眼睛,轻笑,无奈道:“你再不睡我就该睡不着了。”
聂娆赶紧故作镇定地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窗外此起彼伏的是除岁的爆竹声,万象更新,载满了人们美好的祝愿,她默了默,低声说:“新年快乐。”
……
新的一年,聂娆给何齐锐准备了一份惊喜,早在他还没搬出那间老房子的时候她就听过不少传言,说他除了会唱霸王别姬这么经典的曲目,还精通音乐创作。
虽然不知道有几分真假,但那天他确实拿了一把吉他出来,于是她调了几个人出来给他建了一间工作室,新戏杀青后让他专门录制专辑,圆他年轻时的梦。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杜泽临再不拖着她加班了,给她的任务也就是朝九晚五按时完成分内工作,聂娆察觉到不寻常,敏感地担心其中有古怪,专程跑到静园里问了一趟。
杜泽临什么都没说,要她陪着下了盘棋,又把她遣了回去。
之后,董权跃下台,换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头面人物,据说是香港哪个大佬的儿子,跟杜家半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大概是他拜过把子的朋友。
再后来,听说杜绮婷被赶出了杜家,和她那群保镖一起,连卷土重来的资本都被刮了个干净。
聂娆想着她当初放狠话的姿态,摇头骂了声活该,也渐渐明白,大概她对杜泽临没用了,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这天她下班,准备约他一起吃饭,没想到何齐锐却把他拉到了录音棚。
老童人好,估计也知道何齐锐的计划,在他进去后,笑着把聂娆请到玻璃外她对面的位置坐下,给了她一只大耳麦。
聂娆坐在操作台前,面前零零散散的都是仪器。
虽是白天,狭小封闭的空间里还是开着灯,华丽温馨的光线只照亮了半个房间,暖色调给人安谧与柔和。
里面的东西和外面差不多,布置得妥妥当当的吸音墙面上安了两盏壁灯,玻璃窗旁边是棕褐色地板一样的木头,除了电脑设备和可以推拨的大操作盘,还有上下两排电子琴键,这些他都用不着。
两台连在一起的液晶屏幕挡住了他半张脸,只透过他幽深的眼眸看得出他很认真,似乎在往吉他上插着线,半晌挪到带防喷罩的麦克风那儿抱着吉他坐好,这下他的上半身都能被看见了。
之后他对着老童打了个手势,聂娆看着老童站着拨了几个键,耳麦里就传来他亲手弹奏的伴奏的声音。
悠扬的前奏配上他那双深情的眼睛,比烈酒还醉人,这二十秒漫长得足够她从上至下完整地打量,他好看的指节拨着琴弦,娴熟得可以不看琴键,专心致志凝望着她。
凉凉的没有杂质,像平缓地穿越云层:“如果悲欢都一览无余,有何称之为惊喜,那次相逢没来得及问你名字。”
民谣的唱腔,像娓娓讲着故事,令人心境平和。
“于是一席之地成了辗转的姿势,好坏平摊的故事,化作旷日持久的救治,一见如故却无法安置,就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某年某天下了场大雨,我醉在街头,你是宣之于口的心思。”随着情绪逐渐推进,那股深情像入了骨髓,他平静地望着她,歌喉里却透着淡淡的惆怅。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你感叹错过良辰不由己,像被蒙上了眼睛,可我说,银河要比流星美丽,亘古不变的美丽,毁掉神座和岛屿,神还是神,鲸还是鲸,你还是你。”
他的手指还在琴弦上流连,聂娆却蓦然红了眼睛,只听他镇定沉稳的声音从容从耳机里传来:“聂娆,这是去年你给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写的歌,知道你要来,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觉,用两天两夜写了这首歌。”
“那天早上发现你在看,想干脆告诉你,又怕给你带来困扰,终于你肯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他在这句话后顿了一顿,鼓起勇气问,“你愿意嫁给我吗?”
聂娆望着玻璃对面的他,点头,嘴唇蠕动,轻声道,愿意。
何齐锐看着她的口型,笑了。
中午老童出去给他们订盒饭,何齐锐出了录音室往她这边走。
连续录制了两个小时他整个嗓子都是喑哑的,喉头不舒服地耸动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聂娆感觉身侧凹陷了一块,他就把脑袋搁在她肩上了。
他温热的掌心放在她肚子上轻柔地抚摸,随后隔着薄薄的布料滑过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