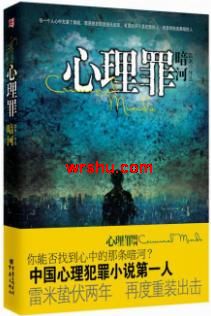月望尼罗河-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晓蓠往闭目倚在床头的图特投去了探视目光,两人谈话,他安静得像不存在,可她清楚他一个字都没有遗漏。
几乎是她眼睛落在他身上的一刹,图特淡道:“我是军队的统帅。”张开眼,对上她的目光。
是统帅,就断无可能弃阵而去……晓蓠抿着唇,视线中他的眉间眼里尽是冷硬决意。
普塔月转眼即逝,泰比月捎着初冬的萧瑟,结束了炎热与泛滥统治的时代。
季节更迭,战局也出现了斗转星移的变换。
孟斯贝尔恪守己责,时刻奔走于前线和埃勒古城之间,向图特汇报帕拉米苏带领部队作战的最新消息。若斯事体大,依米奥也会亲身跑一趟,在那次对战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基于这连串变故,以赫塔被重新起用,以参谋身份在帕拉米苏的营中走动。
尼罗河发水,古实人忙着捕鱼充饥,他们也不曾停歇,在洪水鞭长莫及的角落布置起给新邻居的见面礼。
纵长浅出的土坑紧密铺陈着草堆、折枝,与河岸线平行的导火线跟随退潮的脚步一条接一条形成,最终,本将在水退后供维图牧群食用的麦草地,一夕之间熊熊化了灰烬。
帕拉米苏谈及此举神情语气不无赞赏。
哪怕本意不在于彻底切断古实人的粮食供应,只是明白看着自己的东西在眼底下被逐步染指,已足够叫他们心慌发难,出动大军全力痛击,否则以古实东岸盟军自恃食物充足死守城中的态势,想要一年半载就让他们折服投降,简直做梦。
“你的夫君精于攻心啊。”他笑吟吟地看着她。
她不予回应,仅眉宇微敛。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帕拉米苏但笑不语。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绝对有能力扭转乾坤。
晓蓠以出来透气为由,留下孟斯贝尔和依米奥两人在房里跟图特汇报。
帕拉米苏是典型的行动派,而事实也印证了她的预感。
经加博戛巴荒原一战,古实重新把战力死死包围在纳帕塔和卡洼周边,临近第三瀑布的科尔马相对前者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不屑被埃及军占去,帕拉米苏也乐得收下充当前哨,显然他很清楚古实盟军的想法,自然也不会按对方设想恃着人多上门硬磕,他把视线调向了东南方,那里有着维图的根源。
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帕拉米苏不单找到并潜入了维图人在南瓦迪山上的栖息地,还快速攻陷了核心的谟地那村。
就在前天夜里,维图的大长老和族长的亲族被相继护送进科尔马城。
埃勒古的上空灰蒙着天。
低低压向地面的云层酷似一张致密的巨网,隔着光,挟带着阴暗四处飘荡。
迄今经历的一切已令她受够了这场战争,即使随之种种无论她多厌倦还是要面对,现在,她只想能好好喘一口气。
晓蓠一眨一眨眺望着怪物似的大片乌云,觉得空气没比房间里的流通。
怪物的半边身子忽然被一道黑影取替。
“在看什么?”
朦胧光影中,她的笑靥浮动:“帕苏伊。”
被勾起的画面打乱了周遭的平和,一瞬间兵荒马乱。
滔天大火、囚禁、生死一线。
胜利天平即将倾向古实的一刻,数千埃及援军带着破竹之势,像一柄泛着冷艳暮色的末日之刃横亘进死亡荒原,飞溅起滚滚沙砾,古实军队措手不及,仓促逃散撤退。
然后她看到了风尘仆仆的红发男子驭马直奔到她面前,头一回露出所有的张皇失措,失礼地,狠狠地抱住了她。
这位赫梯的月神祭司,没有辜负她所望,找到了帕拉米苏和他的部队,他对她的情谊,早已超越了国家、阶层和立场。
而她感受着他烫手的体温与急促心跳,却无力抬起手回抱他,说不出一句话。
“怎么站到了外面?”
“他的属下和他汇报事情,我正好想一个人吹吹风。”
明澈的绿眸透出了笑意。
“你有事找我?”晓蓠回归正题,问道。
“我想看看你。”
“我很好,谢谢关心。”
男子的表情写着不信。
她失笑:“对呀,你也是祭司,所以看得出他的伤势。”
帕苏伊神色黯然了一下。
晓蓠长长吁了一口气。
“也就是,你也无能为力,对不对。”不然他不会只是来看她。
被移送到埃勒古城的除了她和图特,帕苏伊因为是祭司,也随同军中部份受了重伤的将士转移至此。
北瓦迪山下小小的边城大多居住着埃及人,亦有不少古实人,城内气氛平和,似乎没受到两边交战的太大影响。
帕苏伊没有一瞬的迟疑,他径直望进她浓黑的眼睛。
“如果只是骨头的局部碎裂,我可以列出敷用的药草你们派人去找,最好的结果是骨伤由内自己愈合,走动起来可能没有受伤前灵活。”
她垂下了眼帘:“但图特的是股骨断裂。”
十多天过去,从主祭司口中得悉的这个诊断结果一直萦绕她心头,然而由她真正说出来,却是想象不到的尖锐撕裂,连呼吸也扯出汩汩鲜血。
头两三天还难以察觉,到第四天,右膝往上开始出现不明显的肿胀,第七、第八天,肿胀扩散至整截大腿……她知道,假如没有抗生素抵挡细菌入侵感染,又得不到其它有效的医治,前方等待的将是皮肤溃烂、高烧、意识昏迷。
帕拉米苏已经派人快马送信到底比斯,可是现实总爱往以为看得到希望的人脸上扇一巴掌。
帕苏伊和依米奥他们相继离开,晓蓠回到了房间。
床上的他安静地坐着,安静地看着前面的虚空,像完全没注意到她。她不由想起初识的一个早上,她爬上屋顶,他面对着苍茫雾色,周身散发着教她心惊几欲转身逃跑的孤独气息,可她没有,相反,她唱了首歌,不想被他出言打击才匆匆溜掉。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是寂寞的,还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
她轻轻把手放在了他肩上,深邃的眸随即映出她的脸。
“要休息一下了。”
当她扶住他的上身准备帮他躺下去,图特用眼神止住了她。晓蓠顿了顿,在床沿坐下。
“有话要对我说?”她浅笑着问。
干燥温暖的大手握着她,“你可以离开埃勒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你想,我都尽力替你实现。”
笑意冻住。
“为什么?你觉得我怕了,想退缩?”
他只是凝着她,一言不发。
晓蓠毫不闪避,她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令他这样做,彼此已明志至此,他怎么可能还——
眼睛扫过微微皱褶的被单,呼吸不受控制地促了促:“你不想让我看到这样的你,是吗?”
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晓蓠不敢相信,几乎失声控诉起来:“为了这个,你现在叫我离开?”
眼见她就要失控,图特不觉加大了手劲,“你身上的伤还没痊愈,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
“除非你命人绑我走,否则我决不离开!”她大叫道。
“蓠!”他拔高了声音。
晓蓠被他这么一唤,霎时冷静了下来。
“听好……”
她反手拽过那只大手,打断了他:“既然你还懂这样叫我,你就该记得,我是为了什么来到古实的。”
图特没料到她会这么说,一时间愣住。
明白他终于在好好听她讲话,晓蓠稍稍松了口气。
他蹙着眉,伸手抚过她的眉尾颧骨,最后停在柔嫩紧致的脸颊上。
“我喜欢看到这里充满喜悦。”
“如你所愿。”
“你该离开的。”他几不可察地叹了口气。
晓蓠不再与他争辩,仅仅覆住他的手,弯起满目的温柔:“可我是你的妻。”
时日仍在缓缓淌过,战争尚未结束。
帕拉米苏出现在二人面前时,她刚服侍完图特洁身更衣。
“你们有事谈,我在外面待一下。”说着就要端起水盆朝房门走去。
明亮的异色瞳对准了她:“这次是来找你的。”
晓蓠眉头微沉。
听毕他的来意,她解开了颈后的绳结。
“你怎么知道这是甘格拉部落的信物?”她看着细致打量手上绿松石的男人,将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我当过海亚婚嫁的护卫队长。”
“所以你在第一眼见到时就已认出我身上的这枚松石。”
帕拉米苏抬起头,对她一笑:“只要能把甘格拉的老人家请到科尔马城,接下来我就可以省下很多功夫。”
是不是有些无所其极?明了他的“请”是如何一回事,她心中好笑。但兵者诡道,或许并不名誉,可特殊时期,奏效就好。
接过他递回来的项饰,晓蓠继续说:“这块宝石跟着海亚公主到埃及有好几年了,你对那些老人的记忆力这么有信心?”
“在巴卡耳山,每条甘格拉村庄的入口都有一座和这枚松石外表一样的石雕,这足以代表它的权威,亦是当时海亚府中丢了这块石头却没有消息大肆外传的主要原因。”
晓蓠还有一个疑问。“你怎么确定甘格拉族长会亲自出面,万一对方怀疑是陷阱,宁可弃卒保帅呢?”
“你的问题可以堆成一座山了。”帕拉米苏挑起一边唇角,然后耸了耸肩,“不过这个问题……我只听说他是个重亲情的家伙。”
晓蓠满腹疑虑,假如这件信物真像他说的可以左右战局,一旦有什么闪失,她可成了罪魁祸首。但转念想到无辜受害的三兄弟、不断增加的流血和憎恨,她又祈盼帕拉米苏是那个能够终结这一切的人。
没错,眼下还有什么比结束这场战事的可能,更值得他们放手一搏?
她的视线和图特不期而遇。
“那拜托你了。”
晓蓠直起身,摊开跟随站起的男人手掌,把绿松石稳稳放进其中,双手裹着他的手指紧紧合上。
帕拉米苏眸光潋滟,若有所思地定在眼前两人身上,半晌,什么都没说,迈开长腿阵风似的离开,一如他来的时候。
雨季已过,天空却淅沥淅沥下起细密的雨。
过去,雨天总能让她得到平静。
图特在睡。
看上去那么安稳,熟睡的脸庞舒展、恬静,令人怀疑他在做甜蜜的梦。她握着他的手,但愿他睡得再踏实些。
她记得,父亲来接自己的那一天,天空也是阴阴沉沉,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将下雨看作是美好的事,即使她渐渐知道了,雨天除了意味着生机和惬意,也为人们带来出行不便、洪涝及苦涩的心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