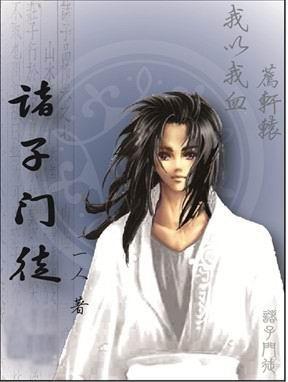女囚门-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站在米兰屋外的一个犯人推开米兰的门,把头伸进屋子说:“米兰,叫你接见。”
米兰爬起来,没精打采地收拾好信和书,她没有对“接见”这个意外的词汇表示诧异。她脑子里一塌糊涂地黑,除听见别人叫自己的名字,她什么也没听见。她出了大铁门,内值班让她上接见室,她一摇一晃地走了进去,她感觉自己要飞了起来,轻得一不小心就会双脚离地。直到她看见坐在接见室里的冷白冰,思想才恍恍惚惚地清楚起来。
冷白冰说:“米兰,你没想到我会来吧。”
米兰点头。
冷白冰将带给米兰的食物放在台子上。这时的冷白冰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一个女人。她的目光停留在米兰脸上,没有了先前的冰冷。
冷白冰说:“米兰,你的脸色太难看了。”
米兰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冷白冰说:“上午开减刑会有你吗?”
米兰点点头。
冷白冰说:“那你还有什么好难过的?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米兰埋着头不说话。
冷白冰有些按捺不住了,她眉毛一竖,又露出了在监狱时的冷酷模样。
冷白冰说:“有什么你说,我会全力帮助你。”
米兰吞吐了半天说:“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我没想到自己也能获得改判。”
冷白冰就不再说什么。米兰跑回监室借了别人接见用的大茶缸,倒了满满一缸茶水,放在冷白冰面前。这时候轮到冷白冰忧郁了,几十年的牢狱生活,似乎浓缩成了一缸茶水摆在她面前,引发了她关于往事的无数回忆。
半个小时后冷白冰开始一股脑儿地喝水,很快缸子里就只剩下茶叶。米兰又要往缸子里倒水,冷白冰用一只手挡住了。
冷白冰问:“米兰你到底想要什么?”
59、破碎的黑暗(2)
冷白冰把话说得跟一颗颗铁钉似的,叮叮当当地掉到米兰面前的台子上。米兰转开脸正好看见上午获减刑释放的人群提着东西朝铁门外走。西瓜皮夹在人群里,她穿得非常干净,脸上有像阳光一样的东西浮动着。3号站在铁门内朝西瓜皮挥挥手便进监室去了。
米兰说:“西瓜皮减刑了。”
冷白冰说:“狗日的运气比我好。”
从城里开往监区的班车已经停在了监房外的道路上,很快接见室里的人陆续起身朝外走。如果错过了这趟班车,就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的班车了。冷白冰也随人群站起来,她走到门口后,转过脸来见米兰仍站着没动,就又折回身来。
冷白冰说:“如果你觉得待不下去,明天中午你想法出来,然后你顺着背面,也就是我们上山的另一条道往前走,我找车在那等你,中午吃饭混乱没人会发现你。”
米兰愕然地站在那里,她的身体朝前倾了一下,没等她说话,班车已经发出刺耳的喇叭声。冷白冰急跑出接见室,在缓缓移动的班车后追了一段路,车才停下来。冷白冰在上车时仍仓促地回过头看米兰,尽管她什么也没能看见。
大雪好像停了一会儿,到了深夜雪又簌簌地下了起来。也许因为下雪,也许因为减刑释放走了些人,监房比平日更加安静,好像空了一半似的。
这一夜,米兰没法睡。冷白冰临别时说的那串话,黑沉沉地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感到自己憋闷得要炸开似的,她说不清自己是兴奋、期待还是恐惧。
玻璃上反射出明亮的雪光。
3号又在黑暗中唱起了歌。歌声飞扬在雪地里变得破碎不堪。
60、尾 声
几个月后米兰从所有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经过努力她当上了大队记录,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开始。对那场亦梦亦幻的爱情她不再纠缠,她认为那场被自己视之为爱情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切也许只是自我沉溺的幻觉。不久米兰的奶奶便死了,狱方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米兰,并派专人送米兰回去参加了奶奶的丧事。当冷白冰再次来探望米兰时,她已判若两人。
秦枫后来去了芜市《法制生活报》当了编辑。
关红被派外出追捕表现突出,获追捕能手荣誉称号。
张道一在一次监狱暴动中光荣献出了生命,年仅32岁。
后 记
当我终于坐在一堆完整的稿子面前时,我无法说清内心的感受。
写作这篇小说的时间,几乎与我从事监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这个过程漫长得无法把握,我曾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死灭般的绝望。
也许故事中始终贯穿全篇的主人公“米兰”的绝望,就是我的绝望,或许是小说中那群女人的绝望。
1996年,我从省女子监狱调到贵阳市艺术馆工作,从此脱离了狱警生涯。我租住在城乡交界的一间农房里开始了《女囚门》(原名《无水之泳》)的写作。
那时我的女儿一岁半,我每天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而我的女儿在我身后的一张破沙发上,也开始了她生命之初的写作。她人模人样地将稿纸的方格一丝不苟地填满。我为她悄无声息的认真和投入震动。这样的震动成为一种负疚压逼着我,使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女囚门》的上半部“看守所”的全部写作。那些日子,我父母为了不让女儿影响我,每天早早地接走了她。他们恨不得让我一个溺子扎进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因为生活的原因,使我的写作一度中断。这让我常常陷入焦躁和不安之中。
1998年我搬进尚未装修完的新居,十月的一天我走出家门被从天而降的铁锤击中头部,我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当然就更不可能提笔写作了。在这场死难中,我感谢与我素昧平生的向欣医生,他在一些非人性的纠缠里坚持了一个医生应有的难能可贵的品质,使我于灭亡样的对人的感叹里有了一些美好的感受。当然我心中善良人性的神话从此破灭了。
1999年春天,市文化局局长为了扩大我的接触面,好心地将我抽调到省“50年活动筹备办公室”工作。到了国庆工作结束,已经是1999年的初冬,我突然迫切地想完成整个写作。我逃难似的去到一个叫阳关的村子,住在一户农民家里,重新开始了《女囚门》的写作。女主人对我非常好,见我穿着布鞋,连夜和另一个妇女用毛线为我织了一双拖鞋。当她的儿子在第二天早上将拖鞋放在我的写字桌上时,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些日子我穿走在田间小道上,心情被一种遥远的阻隔撕得七零八乱。有阳光的时候,我就跑到紧靠树林的石头草蒿里坐着。我真的特别需要这样的方式来模糊一种绝望的真实。不过我的写作状态却很好,有那么两天达到上万字。当然其中有一天,我的手被冻僵了,由于握笔时用力太大,到了晚上,居然痛得再也握不住笔了。
空隙的时候我就会给女儿打电话,每天保持两次,清早和晚饭后。我对女儿一直有负罪感。
当然结束那段生活,并没有完成《女囚门》的写作。回来后自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使写作再次停顿下来。到了2000年的春天,我挣扎着重新开始了《女囚门》的写作。从春天到夏天,我依靠着写作不断地向外挣脱,它对我真是一种拯救。那些日子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我会是什么样子。
还是那句话,写作使我重新坚强地活着。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绝望到不能入睡的地步。写作使我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的阴影里挣脱出来。写作使我重新改变着一切。那段日子在以后的岁月里真的不会被我所了解。
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