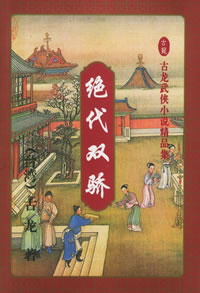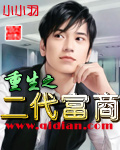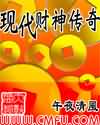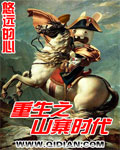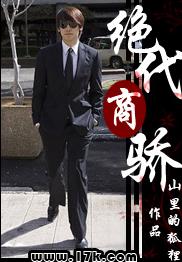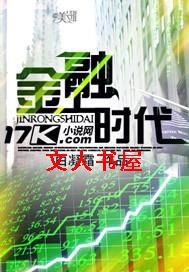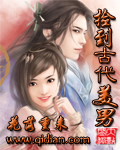新列强时代-第5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他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
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
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
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
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
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他立即以两江总督名义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
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他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
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他的真心。
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后来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他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
还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
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屠杀,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失踪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
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
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搞得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十分尴尬。
不管怎么说,在曾国藩的强硬手段下,湘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我裁撤,一时震惊了整个大清官场,各地督抚都怀着莫名心情看着两江发生的变故,一时间湘军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第646章尾声
“湘军这么快就怂拉?”
待京城的确切消息传到两广,整个乡勇队都沸腾了。吴可顺应民意再次召开乡勇队高级将领扩大会议,商讨湘军突然裁撤将引起的巨大波澜,会议刚刚开始便有将领迫不及待跳了出来叫嚷道。
不怂行吗,就算湘军想要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吴可把这次会议当作国内局势研讨会,打算从朝廷以及湘军两个方面,探讨出湘军到了眼下自我裁撤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因素,然后吸取教训看看乡勇队有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
以吴可此时的身份地位,自然能从朝廷搞到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消息。
别看湘军如今风光无限吸引整个天下的目光,可实际上它只是朝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湘军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一边作为进攻金陵的预备队,一边又防备湘军突然‘失控’做出什么让朝廷措手不及的过激行为。
在金陵的西部,有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有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有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头脑清醒的曾国藩再们敢轻易冒险?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即将离开的老人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和请求,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下来。
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瓶似的惆怅无比。
曾国藩知道手下人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
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
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
有淮军在,曾国藩的处境安全很多。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
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刘长佑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
吴可把两江发生的情况,已经自己的想法全盘道出,让手下一干小弟明白两江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告戒他们不可大意不然湘军就是前车之鉴。
有将领表示不以为然,湘军连内部都统一不了臆见,出现眼下情况那是活该,乡勇队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吴可闻言一乐,知道小弟指的是曾氏兄弟争吵一事。
话说曾国藩没有征求曾国荃的意见,便主动帮他那位九弟搞了个‘兵退’,那个曾老九气得够戗,不管不顾在公众场合让曾国藩没脸。
这事儿在两江官场一时传为笑谈,不过曾国藩的处理手段也确实让人佩服,轻松便解决了这个尴尬。
曾国荃的生日那天,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不过几天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根据这事,吴可笑言老曾还是很有能耐的,大家可不要以为湘军倒霉了就小瞧了别人,曾国藩能混成眼下这等程度可不是吃素的。
那厮可不是个简单角色,在解散数万湘军以表心迹的同时,他还上奏停解湘军军饷,巧妙处理当时复杂的金银粮饷问题。
要知道朝廷在金陵城破不久,即逼令曾国藩交出金陵缴获的金银。曾国藩一面上奏朝廷,称金陵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另一面上奏停解湘军军饷,以作交换条件。
在奏请裁军后的没几天,他即奏请停解湘军军饷。第一笔是停解湖广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同治元年(1862年)以来,至少每年有120万两供金陵围城军队使用。
停解湖广厘金表明曾国藩的诚意。朝廷二话不说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可留其三成作饷,他谢恩拒绝以表诚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的军饷朝廷也予以批准,江西厘金改供鲍超等军。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归湖南主持征收。
这厮为了取信朝廷,可是付出了极大代价。同时因为忌惮来自两广清军方面的压力,不知是否有意缓和与无之间的紧张关系,待收复金陵没多久,布置在江西与广东交界以及湖南与关东交界的厘关税卡全部撤走。
两广方面自然不会轻易跟湘军和好如肠骨,不过有好处可得吴可和手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