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亲终于安静地睡熟了。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有人在欢乐和幸福中深深沉醉的时候,有人却在不幸和痛苦中苦苦挣扎。今夜,欢乐和幸福的人们呵,你们尽情地欢乐和幸福吧,人都是为了欢乐和幸福而生的,我为你们深深祝福;而在不幸和痛苦中挣扎的人们,请你们记起往昔的每一份欢乐,也请期待未来的每一份幸福,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到来。今夜之后,寒冷的冬天将蹒跚而去,温暖的春天将如期而来。
我伫立黑夜的窗前,凝视着万家灯火,每一盏灯火下面,都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都有一张张喜气洋溢的脸,没有人会想到,我所伫立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温暖的角落。
耐不住寒气的侵袭,我坐到了床上。收音机响着,疲惫的我却再也抵挡不了睡神的“进攻”,在新年钟声将要敲响前的半个小时,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梦中,世界飘了好大好大的雪,我和父亲一起手忙脚乱地堆着一个滑稽可爱的又胖又大的雪人,在我们的欢笑声中,钟声响了……
在我为病中的父亲担心,担心七十多岁的他老人家能否熬过这生死的一关时,我和华的爱情,也一直在痛苦的煎熬中进行着。
虽然我们不曾见面,虽然我们只是“纸上的爱情”,但是,我们的爱却是真挚的,热烈的。
华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华。
一封封厚厚的往来书信,是我们爱的证明。
然而,这样一种“未见面的爱情”,爱的愈深,我们所受的煎熬也就愈加深重——我们都渴望早点见到对方,但却恐惧见面之时即是分手的开始。
你想跟我去当乞丐吗?
与华第一次通话时,华为我流下了太多的泪水。
是在一个暮色渐浓的入夜时分接到华的第一个电话的。
华的声音让我喜悦。
华说,她想来看我,骗父母说到福建看一个同学;但因她从未出过远门,父母不放心,不让她来;而华,又不能接受我去看她,说“那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名声”……
华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华的哭声从电话那端穿越千山万水而来,使我心碎——我多想能伸手去为她拭去脸上的泪水。可我,又能做到什么?
握着话筒的手在颤抖,我只能用苍白的语言安慰电话那端的她,我说,华,不能来就别来吧,以后再找机会,好么?……别哭了,再哭,我也要哭了……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母亲,华是为我流下最多泪水的女子。
在这次电话中,华说,真想跑到我身边来,和我过一辈子篱笆茅舍的日子。
我说可别这样,你想跟我去当乞丐吗?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一直盼望着华能在我生日时前来看我,在心里我已经准备好,她见了我这武大郎的样子后,就和我说拜拜。
但她,终于没有来。
生日前三天,我收到华寄来的信和贺卡,信纸的每一页都画着生日蛋糕和红烛。
华说:“舟,我不能来,别怪我……”
我失望至极!
华:
前天、昨天、今天,一直想着要放弃你,逃避你。我好绝望。我真难以承受这太深的痛。你不仅不能给我一个未来,甚至也不能给我一个现在呵!
终于咬牙下了最后的“决心”:放弃!坚决放弃!为你不敢前来看我的软弱,也为你怕“名声不好”的虚荣,你必须为你的软弱为虚荣付出代价;而我也将为放弃你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然而,下午与你通电话时,面对你的纯真与柔情,我……一下子又推翻了所有要与你分手的理由,并且,终于有勇气告诉你,我的残疾真正残在何处。
要说出那让我一生悲哀的“驼背”二字时,我的心是怎样的在滴着血呵!因为,说出之后,也许就将是你弃我而去的开始……
把我的残疾实情告诉华,是因为我想让她爱得更真实一些,同时,也是为见面时打好预防针。
至于她了解了我的残疾之后,会不会因此像菁一样提出分手的问题,我实在顾不了这么多。正是因为爱她,所以我更不愿对她有任何隐瞒和欺骗。
2月14日,我一个人度过了一个孤寂伤感的情人节。
而华,她会来么?来,又在什么时候?
一个所谓的“诗人”,沦为了一个偷车贼
正月初五这天,我在邮局和华通了我有生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长途电话。
华在电话中叫我“放弃”她,说她不值得我爱,就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
我艰难地在电话中和华谈判着,时不时陷入沉默。
总算说服了华,不再轻言放弃。
结账时,才知道打了67分钟,节日半价,也花了五十多元钱。
正好让一位在这所邮局工作的表兄碰上,他责备我:怎么这样乱花钱?
我又能说什么?
倒霉事接踵而来——就在第二天,我借来的一部自行车被盗了……
华:
你真是舟前世的冤家呵!
昨天,因为你的叫我“放弃”,竟然和你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浪费了几十元血汗钱舟并不心痛,让舟心痛的只是,舟的心华“好像”从来不懂……
第九章 当一回孝子(3)
昨夜,舟是怎样度过的,华,你知道吗?
昨夜,舟是决定了:不放弃!绝不放弃!死也不放弃!
然而,早上想骑车去拿饭给父亲,停在楼下的单车却不翼而飞了,只有一把撬掉的锁扔在角落。醒悟之后,舟默默地,走出了医院。舟的心,像冰一样冷。
那一刻,舟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并且愈来愈坚定:放弃!放弃!放弃!……
那一刻,舟心硬如铁,舟以为,这一次舟是真正要放弃华了,仅仅因为一部破单车。仅仅因为一部破单车吗?华,人生是怎样的荒唐呵!
……
自行车,是大姐嫁在城里的女儿,也即我的外甥女,借来给我用的。如果是我自己的,或者是外甥女的倒也罢了,偏偏是外甥女向她丈夫的哥哥借的。因为春节那几天,医院食堂放假,不开伙,我只有到外甥女家拿我和父亲的一日三餐。从医院到外甥女家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路,骑车能省时间,因为重病的父亲身边不能长时间没有人。
其实我也想过,车停在住院部楼道过夜是否安全的问题,但停了几夜均没事,又想医院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一块人间的净土,不可能发生偷自行车这种卑鄙无耻的事。
然而,还是发生了。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是冰冷的。
车被偷了,必须赔,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怎么赔呢?
赔钱吗?不可能,父亲住院钱都不够哪。
谁又能想得到,前天还在给友人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要“灵魂走向崇高”的我,所萌生的,竟是这样一个该死的念头:
偷——我被人偷了,我也去偷一辆!
终于,几天之后,我在医院门口看见了一辆停着的自行车,竟然没上锁,我心里一阵狂喜,在原地呆了好几分钟,心头“扑扑”直跳,看清附近无人之后,我几步跨过去,推出车子骑上就跑……
一个所谓的“诗人”,很轻易地,沦为了一个偷车贼!
那时,我心里有没有犯罪感,我已无从记起了。
但我是可耻的,卑劣的。
几个月后,我人亡家破,我甚至这样想过:我人亡家破的厄运,是不是因为我在医院偷了那样一辆不该偷的车,上天才降给我如此深重的惩罚与报应?
车偷出来后,我把它骑到了外甥女家。外甥女不在,她的婆婆出来问我什么事。
我吱吱唔唔地说,车被偷了,我赔一辆给你们……
因为做贼心虚,也因为不善扯谎,我在言语间终于露出了“车是偷来的”这一“马脚”。
外甥女的婆婆一听,脸色陡变,双手乱摇:这车我们可不能要,你还是快骑回去吧……
我不敢把车“骑回去”,而是骑到了城里一位亲戚家中,放在了那儿,直到父亲出院后,我才把它取了出来。
那车,我骑回村后立即把它送给了一位急需用车却囊中羞涩的朋友,我很少再骑它,偶尔有事骑上它时,也是提心吊胆,生怕遭到报应——被车撞了。
病重的父亲,也会这样死去吗?
医院里的日子,是压抑的,沉闷的,一如当年在收容所里的日子。
整天面对惨白的墙壁,听着无休止的呻吟,那简直是另一种“坐牢”!
由于医院迟迟不安排手术,父亲的病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靠从生殖器口插入一根导尿管直达膀胱,外接导尿袋,才能让尿畅通,这,对一个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是十分痛苦和难以承受的。
父亲不管白天黑夜,常因忍不住疼痛而呻吟出声。父亲的呻吟是单调而独特的,总是用他生身地——闽东方言,一声声几小时连续不断地低唤着“娘呀,娘呀”。
这个时候,年老的父亲,委实可怜得像个可怜的孩子。
呻吟是一种排解痛苦的较好方式,但对于我来说,父亲的每一声呻吟都如刀子一般割裂着我脆弱的心。同时,疚愧之情也在折磨着我:我这个将要而立之年的儿子,长了这么大了,从未让父亲放心过,我实在是一个不孝的儿子。
最初入院时,医院病床挺松,我和父亲各睡一张病床。春节过后,病人渐多,病床不够用,我这个陪护人员只好把床铺让出来,在父亲的病床旁搭个地铺。
父亲身上插着导尿袋,不方便上厕所,只能在床上大便,每次都是在床上铺两张厚纸,父亲大便完后,我再替父亲手楷净,把大便清理到厕所里。
医院里经常有病人死去,死者的家属哭天号地的,不分白昼或黑夜,我听了,心中总有莫名的悲伤和惶恐。
病重的父亲,也会这样死去吗?
父亲住院后,哥哥的很多朋友,包括镇政府的一些领导,都来看望父亲;他们往往都是50元、100元地拿给父亲“买点补品”,这里面,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也有一些虚伪的“真诚”。
我不能据此评判哥哥这个“官”当得好或坏。
这时候,哥哥的身份是村长兼党支部书记。
我的一些朋友也来看望了我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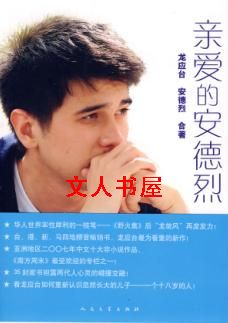




![[尼罗河女儿]亲爱的侍卫长大人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