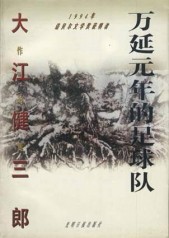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给予我的启示,而今已经展开成形。这面白弓背的大汉,无疑便是曾祖父的弟弟。他在仓房的地下足足关了十年,反思万延元年的暴动。然后,他突然又出现在地上,把十余年自我批判的岁月里获得的一切心得都用来推进这第二次暴动。既然前次暴动鲜血淋漓的成果已经大打折扣,他便致力于不让暴动的参加者和旁观者出现一例死伤,有效地迫使攻击目标大参事自杀,同时又不使暴动的参加者遭到处罚。寺院东堂的墙面上,依然是我与鹰四、妻子一起看过的地狱图。我便在这里,向年轻的住持讲述了这一切。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依然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
〃万延元年暴动时深受其害、疑心重重的那些转变时期的农民为什么把暴动的领导权交给一个不知来历的奇怪大汉?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正因为传说中万延元年暴动的领袖,以一个暴动专家的身分在农民们面前复活,他们才情愿聚集到他的领导之下。明治四年的暴动,从其结束的实际情形推测,骚动的中心目的乃是一个政治性的计划:迫使大参事下台。或许这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样的口号激发不起农民的冲劲来,所以,这个关在地下室里研读新近刊物的自我幽闭者,尽管他自己与这样的迷妄无缘,但他利用种痘、血税之类词语语意的含糊,煽动民众,组织暴动,最终搞掉热衷于新型强权的大参事。在这以后,他重又回到地下生活中去,不放任何人再见到他,把自我幽闭的生活再过上足有二十年。我相信是这样。从前我和弟弟都在探求万延元年的暴动以后曾祖父的弟弟到底变成了怎样的人,却都不得要领,没摸到实处。我们只顾探求那个穿过森林跑掉的子虚乌有的人了嘛。〃
住持善良的小脸泛起红晕,一直微笑着倾听我的这番宏论,然而却不置可否。在〃暴动〃的日子里,他曾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因此,直到现在,他还对我显得忧心忡忡,刻意用一种过分的平静,来冲淡我心中的兴奋。然而过了一会儿,他还是给我提了个旁证。
〃明治四年骚动中那个驼背领袖的传说,在山脚很是出名哩。但纵然如此,他却未在诵经舞的〃亡灵〃里面出现过啊。阿蜜,这怕是因为它会和您曾祖父弟弟的〃亡灵〃发生重复,所以人们才没去造出另外一个〃亡灵〃罢。当然,这个证据实在太消极了。〃
〃诵经舞吗?演员们进仓房里落了座之后,便在那里大吃大喝,莫非这也是因为,有一个代表性的'亡灵'曾经在那里的地下室度过长期的幽闭生活?这样的话,这证据可算积极了。我想,祖父在注释这本书时,其实明知道这驼背怪人就是他的叔父,他暗中表达一种敬爱之情呢。〃
对我的这种空想连篇的大肆假设,住持仿佛觉得无法苟同。他不直接回答我的话,倒是转向了那幅地狱图,说道:
〃要是您的推测正确的话,这幅画八成也是您的曾祖父,给还活在地下室里的弟弟画的呢。〃
我展眼望着那幅画。我发现,还是与鹰四、妻子共同欣赏时那种深切安谧的情感。而今,它却不单单是作为被我的情绪唤起的一种被动的印象,而是作为一种独立于我的实在的绘画实体而存在于此。它能动地存在于画面上,一言以蔽之,乃是一种浓重的〃温存〃。定做这幅画的人,也许要求画师一定要描绘出〃温存〃的实质。当然,还必须是画地狱。因为他的弟弟虽生犹死,正在自我幽闭当中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地狱,他要这幅画给弟弟安魂。然而那火焰之河,一定要涂得一片鲜红,犹如阳光映照下山茱萸树那红彤彤的叶背;那火焰的线条,一定要画得平稳柔和,犹如女性裙裾的皱褶。那
〃温存〃也要体现在火焰河中。既然这幅画意在给既为亡者又为鬼怪的狂烈的兄弟安魂,便必得将亡灵的蹉跌和鬼怪的残酷暴露无余。然而这鬼怪和亡灵,纵然各自表现着残虐和苦闷,但必须有一条宁谧的〃温存〃纽带,把他们的心联结起来。在地狱图中所画的亡灵中……诸如那些披头散发的人,他们摊开四肢,瘫倒在灼热的石块上面,或如那些火焰之河里的人,他们的臀部瘦成了三角形,正伸向火雨淋漓的虚空之中……或许这些亡灵中的某一个,便是用曾祖父的弟弟做了原型。这样想来,我不禁要把所有亡灵的形象,都在我意识的最深处细细回忆一番,仿佛能寻到一个可称为血亲的固有面容。
〃阿鹰见了这画,挺不高兴来着吧。〃住持提起了往事。
〃小时候他就一直害怕地狱图罢。〃
〃莫非阿鹰并不是怕这画,倒是不喜欢画上画的地狱的那种'温存'?现在来看一下,我真要这样想了。〃我说,〃阿鹰有一种惩罚自己的欲望,觉得他应该活在更为惨酷的地狱当中。或许正是这种欲望的驱使,才让他拒绝了如此宁谧平和、安详'温存'的假地狱吧。我想,为保证自己地狱的惨酷不遭到削弱,阿鹰一定做过不少的努力呢。〃
年轻的住持渐渐收起了毫无意义的微笑,在他的小脸上面分明现出了一种怀疑的神情。于是我发现,他那对怀疑之事佯装不知的表情里反倒现出一种目中无人的闭锁。面对着这个对于山脚人的生活全无兴趣的住持,我实在无意把自己心中的问题再讲出来。对我来说,那地狱图毋宁是另一个积极的证据。如果需要重新考察对曾祖父的弟弟和鹰四做出的判断,这些新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住持送我到山门的途中,向我讲了〃暴动〃以后山脚青年们的情况。
〃听说,与阿鹰一起做事的那个衣着单薄的青年,合并以后第一次选举,他就选上了城里的议员哩。看上去阿鹰的'暴动'完全失败了,可是至少,它倒把从前山脚里已固定下来的人员构成撼动了一下。说到底,既然阿鹰集团里有一个小伙子选上了城里的议员,可见对那些顽固的大人们的头头儿,也是有了点影响力的。'暴动'对整个山脚的未来都会是卓有实效的,阿蜜!其实,这'暴动'将山脚人纵向的社会渠道扫除掉,又将年轻人横向的渠道牢牢地巩固了起来。阿蜜, 我想,在山脚做长远展望的基础已经建起来了!S弟和阿鹰,他们悲惨地死了,可他们尽了职责!〃
我回到家时,超级市场的天皇已经离开了仓房。那群孩子们,本来一直在欣赏那断壁残垣以及地下室上面地板的裂缝,一俟黄昏降临,他们也立刻作鸟兽散,急急地沿着石子路跑走了。我在孩子的时候,山脚的孩子们便是如此,除去祭祀之类特殊的日子,只要黄昏一到,便立刻气喘吁吁地各回各家,全然不像〃乡下〃的孩子,到了夜里,还要贪玩不止。今天的孩子们是否是因为害怕树林里来的长曾我部还不得而知,但他们仍旧不曾改掉这一习惯。
妻子用从超级市场买来后攒起的面包和熏肉给我作了些三明治当晚饭,放在炉边的盘里,自己却横躺到里间,俨然一副专心保护腹内胎儿的模样。我用油纸包起三明治,塞到外套的口袋里面,绕到世田和,摸出一瓶满满的威士忌和一个空酒瓶。我洗了洗空瓶,盛满热水,然而那水却很快就冷却下来,像渗入牙龈的冰水一般。我早该想到,半夜里的寒风是相当地厉害,于是我打算除了自己正用的那条毛毯外,再从壁柜里把预备的拿几条出来。我正蹑手蹑脚地从妻子的旁边走过的时候,发现她原来并没有睡着。
〃我想一个人考虑一会儿,阿蜜,〃她厉声说,好像我要找机会偷进她的毛毯里面一样。〃重新回想一下我们夫妻生活的许多细节,我看我受你的影响很多,也经常在你替我分担责任的前提下做决断。如果你要抛弃谁,我总站在你这边,附和你支持你。可现在,我觉得很不安呢,阿蜜。保育院的那个孩子,还有我就要生下的这个孩子,我都想自己承担起责任,不再靠你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
〃是嘛,我的判断靠不住指不上嘛!〃我畏缩地说了这一句,再也不说话了。我也想关到仓房的地下室里考虑一下。既然发现了新的证据,那么我必须打破自己的成见,对曾祖父的弟弟和鹰四进行复审,这样,我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纵然这对于死人已无任何意义,但这却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我钻到地下室里,像一百年前的那位自我幽闭者一样,背靠正面的石墙蹲将下来,把三条毛毯牢牢裹在外套上面,吃三明治,一口一口轮流喝威士忌和早已变凉的白开水(幸好从南方吹进山脚的狂风,还没有让它冻成冰),陷入了沉思。这地下室长年人迹不至,到处都是让虫子咬坏的书页。凌乱的碎纸,朽坏的书桌,腐烂散破而又干巴巴的草席子,叫强风一吹,它们全堆到屋角,散发着霉味。墙上的石头略有些潮湿,仿佛冷汗津津的皮肤一般,长久的磨损使得它摸起来柔和可人,却也散发着同样的霉味。湿重纤细的灰尘,粘得鼻孔唇边眼角到处都是,我不禁想起了二十五年前得上了小儿气喘病那时的痛苦感觉:这灰尘可不会把毛孔全都堵住,让皮肤无法呼吸罢?闻一闻指尖,发出的也是同样的气味,分明已经叫灰尘给传上了。我把指尖用力往膝头上擦,可是赶不走那种气味。在我把自己关在这黑暗当中的这段时间里,也许会有螃蟹般大小的蜘蛛,从尘垢堆的深处爬将出来,在我的耳朵后面咬个不停。想到这里,便有一种厌恶感仿佛直吞噬到我生理的中心,眼前的黑暗当中,便充满了朝着我虎视耽耽的各种怪物:大如乌贼的蠹鱼,比得上草鞋的潮虫,以及像狗一般大小的不合节令的蟋蟀。
复审。然而,在这地下室里,如果曾祖父的弟弟关在这里,把他暴动领袖的identity终生坚持下去,那末,我过去深信不疑的判决就要被推翻。鹰四的一生,一直刻意仿效着曾祖父的弟弟,他最后的自杀,也便是用我所发现的曾祖父兄弟的identity之光,给他的〃真相〃染上了新的色彩。换言之,便是向苟生的我炫示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