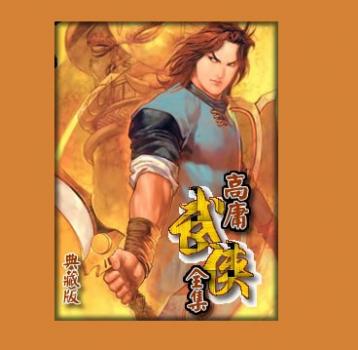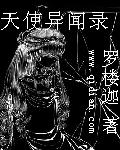忏悔录-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没有产生过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一些原则,因为她的性格和基督教的道德太吻合了。凡是教会明确规定的,她都去做;其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喜欢服从的。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规定她开斋,她会守斋一直守下去,这完全是为了伺奉上帝,丝毫不是出于谨慎小心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从属于达维尔先生的原则的,说得更准确些,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坦然地每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不是出自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的顾忌并不比她多,但是她和她们之间的不同是;她们是由于情欲的诱惑,而妈妈则是被她那诡辩哲学所欺骗。在最令人感动的谈话中,我甚至敢说,在最富有教诲意义的谈话中,她可以平静地谈到这个问题,面部的表情和声调毫无改变,而且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她的谈话,随后她会以同样冷静的态度接着谈,因为她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定的,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解释、奉行或回避,而不会冒亵渎上帝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虽然和她显然不同,我承认我不敢反驳她,因为要反驳,我就得扮演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但是,我不仅知道她的气质可以防止她滥用她的主张,我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自己要求例外,就等于让她把她所喜欢的一切人都算作例外。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的地方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在她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而在当时甚至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叙述一下她的主张,我要遵守我的诺言。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她的这些处世之道正是我为了使自己心灵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于是我便十分坦然地尽量从这个信赖的源泉中汲取一切。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了,我真想把我的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给了她。由于我对她的加倍的依恋,由于我确信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长,又由于我对将来的命运处之泰然,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是十分幸福的情况。这种局面缓和了使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中的一切激情,从而使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久的时光。给这些日子增添了乐趣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用一切办法来培养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由于我一心要使她爱上她的园子、养禽场、鸽子、母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我虽然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但并没有搅乱我的平静,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可怜的身体,更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收获葡萄和水果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加之又处在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使我们对田园生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们怀着极端的惋惜心情看着冬天的来临,回城的时候就好象要被流放似的,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活到下一个春天,我觉得向沙尔麦特告别就是永别。在离开的时候,我吻了吻那里的土地和树木,尽管已经走得很远,我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回城以后,由于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经很久了,又由于我已失去了城市里的娱乐和社交的兴趣,我就不再出门了,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萨洛蒙最近成了我和妈妈的医生,他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他对宇宙法则有相当明智的见解;对我说来,听他那些非常有趣且富有教益的议论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为有益。一切愚蠢和庸俗的谈话是我所一向不能忍受的;但听取有益的与有丰富内容的谈话,则始终是我最大的愉快,我对这样的谈话从不拒绝。同萨洛蒙先生的谈话使我感到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涉及到我那摆脱了束缚的心灵行将获得的高深知识。我由于对他的好感进而发展到喜欢他所谈的课题,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的书籍。那些能把科学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特别是由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对我更为相宜。我开始阅读这些书,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贪婪地读它们。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读了它上百遍,并且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手册。最后,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逐渐引向研究学问的道路上,而且,我虽然每天都认为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但却更加奋勉地学习起来,就好象要永久活下去似的。别人都说这样用功学习对我有害,我却认为这对我有益,不仅有益于我的心灵,而且有益于我的身体,因为这样专心读书的本身对我就是一件乐事,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很多。诚然,这对于我的疾病,实际上不能有所减轻,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剧烈的痛苦,我对身体的衰弱,对失眠,对用思考代替活动,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我把机能的一步步慢慢衰退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到死方休的过程了。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琐事的挂虑,也使我避开了一直到那时被迫服用的讨厌药品。萨洛蒙承认他的药对我没有什么用,也就不勉强我继续尝那些苦味了,他只是开一些可服可不服的药方来安慰可怜的妈妈,以便减轻她的忧郁,这一方面不使病人对病情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医生的信誉。我放弃了严格的节食疗法,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在我体力允许的范围内重新过起健康人的生活。我样样都有节制,但没有任何禁忌。我甚至又开始出门了,我去拜访我的朋友们,特别是我非常喜欢交往的那位孔济埃先生。最后,也许是由于我认为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由于在我内心深处蕴藏着还能生存下去的希望,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我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以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好象我相信我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有的东西。我对布沙尔的书店发生了好感,一些文人学者经常到他那儿去;不久,由于春天——我曾以为不能再看到的春天——已经临近了,我便在那个书店里选购了几本书,以便有幸能回沙尔麦特时,随身带去。
我得到了这种幸福,我就尽量享受这种幸福。当我看到草木萌蘖发芽的时候,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重新看到春天,对我说来,等于天堂里的复活。积雪刚刚开始融化,我们就离开了那所监牢般的住宅,为了听那夜莺的初啭,我们去沙尔麦特是相当早的。从那时起,我已不再相信我快要死了,实际上也很怪,我在乡间时从未真的病倒过。我在那里感到过不舒服,但始终不曾缠绵病榻。当我觉得身体比平时还坏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看见我要死的时候,就请把我抬到橡树的树荫下,我保证会复原的。”
虽然衰弱,我又恢复了田间的活动,当然我是量力而为的。我为自己不能独力从事田园工作而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