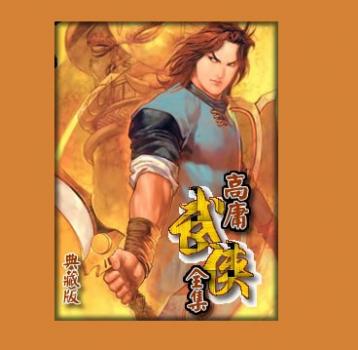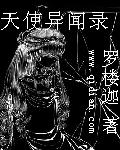忏悔录-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呢?我的上帝呀!真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神圣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总是想法子把他的心倾吐出来的,要把满腔的东西拿给人看的。这样的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到脸上,他决不会想什么修饰打扮。
我那时又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这是埃皮奈夫人以前告诉我的,也是他实践了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箴言,当我听到的时候,曾引起我无穷的感慨,虽然当时我还只把它当作一种打趣的话看待。但是不久我就看出,这个原则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那么多叫我吃亏的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狄德罗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种秘密教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作过解释。
我又想起了好几年前人家就再三给我下过的那些警告,说这个人虚伪,说他会装假,特别是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弗兰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而且他们都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密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兰耶先生当时跟波立尼亚克子爵过往甚密,当格里姆开始在王宫区落脚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弗里森伯爵死后那种悲观失望的情形。这是因为他要维持他在遭到菲尔小姐的严厉对待后所博得的那点名声,这种名声,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么盲目的话,一定会把其中的骗局看得比任何人更清楚的。他被人硬拉到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做作得煞有介事,真是悲痛欲绝。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用浸透泪水的手帕蒙着眼睛,看到公馆的房子就哭个不停,但是一转过一条小径,就只见他登时把手帕放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了。这种情景多次发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马上也就给忘了。我自己也同样把它忘了,可是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偏偏使我又把它想了起来。我在格勒内尔路住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当时在乡下,有一天早晨来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从乡下赶到,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头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当天还有人在戏院里看到他呢。
这一类事情,我想起了很多,但是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这样晚才注意到。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毫无例外地介绍给格里姆,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跟他形影不离,简直不愿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上了一些别的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凭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朋友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劝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的那些朋友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过丝毫好感。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这样,而他是住在伯爵家里的,因此我若能跟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至于弗里森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也没有对我表示过好感,而格里姆跟旭姆堡伯爵相处得还更随便些。
不仅如此,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的。然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不要在他们的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实际上好些。这些朋友一共有三个: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最配听我倾诉秘密的人,却又是唯一我没有告知这秘密的人。然而他却知道了我这个秘密;是谁告诉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很少可能出之于埃皮奈夫人之口,因为她知道,如果我是那种人,也学她背信弃义,我就有办法残酷地报复她,剩下来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特别是对付我,因此极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同谋。我可以打赌,只有杜克洛,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因此他可以有泄漏秘密的自由,而他却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策划把两个女总督从我身边拉过去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也拖下水,但他始终以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只是在事后才从他口里知道他们之间在这问题上的经过;但是,当时我已经从戴莱丝口里听到了一些,足以使我看出在那一切活动当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是想摆布我,即使不是拂逆我的意愿,至少也要瞒着我;再不然,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做工具去实现什么阴谋。那一切必然都是不正派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那是出于友谊,就让他相信去吧。
这种所谓友谊叫我在家里和在家外一样地倒霉。几年来他们和勤·瓦瑟太太那种频繁的晤谈使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显然变了,而这种改变,当然不会于我有利。他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密谈中究竟讨论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讳莫如深呢?这个老太婆的谈话难道就那么有趣,使得他们这样喜欢吗?或者是那么重要,值得这样严守秘密吗?三四年来,这种密谈一直继续着,我早先觉得是可笑的,这时我再想想,就开始感到诧异。如果那时我知道那女人在为我准备些什么的话,这种诧异是会发展到焦虑不安的程度的。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吹嘘说他对我如何热心,这种所谓热心眼他对我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相容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于我有利的东西;他诡称对我抱有的那种慈悲感,很少有助于我,倒是有损于我。他甚至尽其所能,把我所选定的那个职业的财源给我断送了,因为他毁坏我的名誉,说我是个坏的抄缮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轮不到他来说呀。他自己另用了一个抄缮人,凡是他能拉走的主顾,一个也不留地从我这边拉走了,他就这样证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影响才能生活,并且要把我的生活来源断得一干二净,不把我逼上他那条路,就不甘心。
把这一切总结一番之后,我的理智最后使我原来还替他说话的那点先入之见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认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断定是虚假的。于是,根据好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决心不再见他了,并且把这个决心通知了埃皮奈夫人;不过那些事实我现在都忘记了。
她极力反对我这个决心,而对我提出的理由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当时她还没有同他商量。但是第二天,她并不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由他们俩一起起草的很巧妙的信,她利用这封信替他辩护,说一切都由于他那种收敛的性格,关于详细的事实却一字不提,并且认为我怀疑他对朋友背信弃义是一种罪过,敦劝我跟他言归于好。这封信(见甲札第四八号)使我动摇了。后来我们又作了一次谈话,我觉得她比第一次谈话时有准备些,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完全让她战胜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判断错了,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对一个朋友做了最不公正的事,应该赔礼。简言之,我也和对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软弱,作出了我原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那一切要求和解的表示;我仿佛是另一个乔治·唐丹,到格里姆那里去,为他给我的侮辱而请他原谅;心里老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认为只要你和婉客气,天下无不解之冤,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信念使我一辈子在我那些假装的朋友面前不知做出了多少卑躬屈节的事。其实,正相反,恶人的仇恨心,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就越发强烈,越觉得他自己不对就越发对对方怀恨。我不需要离开我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在格里姆和特龙香两个人身上找到这个论断的十分有力的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好,根本找不到我对他们俩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可作借口。他们的怒气日甚一日,就跟猛虎一样,越容易出气,怒气就越大。
我满以为格里姆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先来请和,会感到惭愧的,因而会张开两臂,带着最恳挚的友情来接待我。谁知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