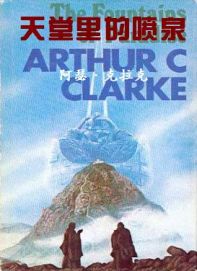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说的什么?”我说。我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今儿晚上要个小姑娘玩玩吗?”
“我?”这么回答当然很傻,可是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你这么个问题,一时的确很难回答。
“你多大啦,先生?”开电梯的说。
“怎么?”我说。“二十二。”
“嗯——哼。呃,怎么样?你有兴趣吗?五块钱一次。十五块一个通宵。”他看了看手表。“到中午。五块钱一次,十五块钱到中午。”
“好吧,”我说。这违背我的原则,可我心里烦闷得要命,甚至都没加思索。糟就糟在这里。你要是心里太烦闷,甚至都没法思索。
“要什么?要一次,还是到中午?我得知道。”
“就一次吧。”
“好吧,你住几号房间?”
我看了看我钥匙上面那个写着号码的红玩艺儿。“1220,”我说。我已经有点儿后悔不该这么着,不过已经太晚了。
“好吧。我在一刻钟内送个姑娘上来。”他打开电梯的门,我走了出去。
“嗨,她长得漂亮吗?”我问他。“我可不要什么老太婆。”
“没有老太婆。别担心这个,先生。”
“我怎么给钱?”
“给她,”他说。“就这样吧,先生。”他简直冲着我劈脸把门关上了。
我回到房里往头发上敷了些水,可是在水手式的平头上实在梳不出什么名堂来。接着我想起在欧尼夜总会里抽了那么些烟,又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就试了试自己的嘴里有没有臭味。你只要把手放到嘴下面,对准鼻孔呼气,就闻得出自己嘴里有没有臭味。我嘴里的味儿倒不大,可我还是刷了刷牙。接着我又换了件干净衬衫。我知道自己用不着为了个妓女把身上打扮得象个布娃娃似的,不过这样我总算有事可做了。我有点儿紧张。我的欲念开始上来了,可我也有点儿紧张。我老实跟你说,我原来还是个童男哩。我真的是个童男。我倒有几次机会可以失去我的童贞,可我始终没失去。总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比方说,你要是在女朋友的家里,她的父母总会突然回家——或者你害怕他们会突然回家。或者你要是在别人汽车里的后座上,那么前座上总有什么人——或是说有什么姑娘——老想知道整个混帐汽车里在干些什么。我是说前座上总有个始娘老回过头来看看后面在他妈的干些什么。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什么事发生。有一两次,我只差一点儿就上手了。特别是有一次,我记得。可后来出了什么事——我都记不得到底出什么事了。问题是,每当你要跟一个姑娘行事的时候——我是说不是个做妓女什么的姑娘——十有九次她总不住地叫你住手。我的问题是,每次我都住手了。大多数男人都不这样。我却由不得自己。你总拿不准她们是真正要你住手呢,还是她们害怕得要命,还是她们故意要你住手,万一你真的干了那事,那么过错就都在你身上,她们可以脱掉干系。不管怎样,每次我都住手了。问题是,我心里真有点儿替她们难受。我是说大多数姑娘都那么傻。你只要跟她们搂搂抱抱一会儿,就可以真正看出她们全都失去了头脑。一个姑娘只要真正热情上来,就不再有头脑。
我不知道。她们要我住手,我就住手了。我送她们回家以后,总后悔自己不该住手,可到时候又总是老毛病发作。
嗯,我在穿另一件干净衬衫的时候,心里暗忖,这倒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我揣摩她既是个妓女,我可以从她那儿取得一些经验,在我结婚后也许用得着。有时候我可真担心这玩艺儿。在胡敦中学的时候,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里面讲一个非常世故、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好色的家伙。他的名字叫勃朗夏德先生,我还记得。这是一本坏书,可勃朗夏德这个人物倒是写得不错。他在欧洲里维耶拉河上有一座大城堡,空闲时他总是拿根棍子把一些女人打跑。他是个真正的浪子,可很使女人着迷。
他在书的某一章里说女人的身体很象个小提琴,需要一个大音乐家才能演奏出好音乐。这是本粗俗不堪的书——我知道这一点——可我怎么也忘不掉那个小提琴的比喻。我之所以想取得些经验,以备结婚后应用,说来也是如此。考尔菲德和他的魔提琴,嘿。这有点粗俗,我知道,可也不算太粗俗。
我不在乎自己在这玩艺儿上成为老手。如果你真要我说老实话,我可以告诉你说当我跟一个女人一起胡搞的时候,有多半时间我都他妈的找不到我所寻找的东西,要是你懂得我意思的话。就拿刚才我说的那个差点儿跟我发生关系的姑娘来说吧。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她的奶罩脱掉。到了我真正把它脱掉的时候,她都准备往我的脸上吐唾沫了。
嗯,我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那妓女来。我真希望她长得漂亮。不过我对这个也不十分在乎。我很愿意这事能快点儿过去。最后,有人敲门了,我去开门的时候,在手提箱上绊了一交,差点儿摔坏了我的膝盖。我总是选择这种紧要时刻绊倒在手提箱之类的东西上。
我开了门,看见那妓女正站在门外。她穿了件驼毛绒大衣,没戴帽子。她有一头金发,不过你看得出是染过的。可她倒不是个老太婆。“您好,”我说。温柔得要命,嘿。
“你就是毛里斯说的那位?”她问我,看样子并不太他妈的客气。
“毛里斯是不是那个开电梯的?”
“是的,”她说。
“晤,是我。请进来,好不好?”我说。说着说着我变得越来越凉了。一点不假。
她进房后马上脱下大衣,往床上一扔。她里面穿着件绿衣服。她斜坐在那把跟房间里的书桌配成一套的椅子上,开始颠动她的一只脚。她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开始颠动搁在上面的那只脚。对一个妓女来说,她的举止似乎过于紧张。她确实紧张。我想那是因为她年轻得要命的缘故。她跟我差不多年纪。我在她旁边的一把大椅子上坐下,递给她一支香烟。“我不抽烟,”她说。她说起话来哼哼卿卿的,声音很小。你甚至都听不见她说的什么。你请她抽烟什么的,她也从来不说声谢谢。她完全是出于无知。
“让我来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叫吉姆.斯梯尔,”我说。’“你有手表吗?”她说。她并不在乎我他妈的叫什么名字,自然啦。“嗨,你到底多大啦?”
“我?二十二。”
“别逗人啦。”
这话的确可笑。听去真象个孩子。你总以为一个妓女会说“别见鬼啦”或者“别胡扯啦”,不会说“别逗人啦”这类话。
“你多大啦?”我问她。
“反正比你更懂事,”她说。她倒是真鬼。
“你有手表吗?”她又问了我一遍,随即站起来,从头顶上脱下衣服。
她脱衣服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我是说她脱得那么突然。我想,你要是看见过女人站起来从头顶上脱衣服,总难免要动情,可我当时并没有。情欲我倒是真的没有。我并没动情,只觉得十分沮丧。
“你有手表吗,嗨?”
“不。不,我没有,”我说,嘿,我倒真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她现在只穿着一件粉红色套裙,看了真让人窘得很。一点不假。
“孙妮,”她说。“咱们来吧,嗨。”
“你想不想再谈一会儿?”我问她。这话说得很孩子气,可我当时的心境真是他妈的奇特。“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常要紧的事?”
她望着我,好象我是个疯子似的。“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谈的?”她说。
“我不知道。没什么特别的话,我只是想,你或许愿意聊一会儿天。”
她又在书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可她心里并不高兴,你看得出来。她又开始颠动她的一只脚——嘿,她真是个容易紧张的姑娘。
“你想抽支烟吗?”我说。我忘了她不抽烟。
“我不抽烟。听着,你要是想聊天,就聊吧。
我还有事呢。”
可我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聊。我本想问问她怎么会当妓女的,可我又怕问她。看样子她也不会告诉我。
“你不是打纽约来的吧,是不是?”我最后说。我只想出了这么句话。
“好莱坞,”她说着,起身走到床上她放衣服的地方。“你有衣架吗?我不想把我这件衣服弄皱。还是崭新的呢。”
“当然有,”我马上说。我能站起来做点儿什么事,真是太高兴了。我把她的衣服拿到壁橱里挂好。说来好笑,我接的时候,心里竟有点难过。我想起她怎样到铺子里去买衣服,铺子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是妓女。售货员卖给她衣服的时候,大概还以为她是个普通的姑娘哩。这使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道理。
我又坐下来,想继续跟她聊天。她真他妈的不会聊天。“你每天晚上都工作吗?”我问她——这话说出口后,听上去似乎很不象话。
“是的。”她在房里到处转悠。她从书桌上拿起菜单来看,“你白天干什么?”
她端了端肩膀。她的个子很瘦。“睡觉。看电影。”她放下菜单朝我看着。“咱们来吧,嗨。我可没那么多——”“瞧,”我说。“我今天晚上精神不好。我这一夜过的很糟糕。一点不假。我照样付你钱,可我们要是不干那事儿,你不会在意吧?你不会很在意吧?”糟糕的是,我真的不想干那事儿。我没有冲动,只觉得沮丧,我老实告诉你说。她本人很叫人泄气。还有那挂在壁橱里的绿衣服什么的。再说,我觉得自己真不能跟一个整天坐在混帐电影院里的姑娘干那事儿。我觉得真的不能。
她走到我身边,脸上带着那种可笑的神情,好象并不相信我的话。“怎么回事?”她说。
“没什么。”嘿,我怎么会那么紧张呢!“问题是,我最近刚动过一次手术。”
“是吗?哪儿?”
“在我那——怎么说呢——我的锁骨上。”
“是吗?那玩艺儿是在他妈的什么地方?”
“锁骨!”我说。“呃,真正说来,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