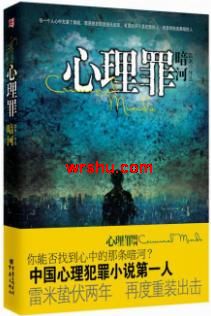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哪来的消息?”头发斑白的上尉梅尔库洛夫怀疑地笑着问。
“你不相信吗,彼佳大叔?”
“坦白地说,我不相信。”
“炮兵连连长打电话告诉我们的。他从哪儿知道的,这很容易解释,他昨天才从师部回来呀。”
“能在澡盆里泡泡就好啦。”
丘博夫带点儿傻气地笑着,装作用桦树枝条抽打自己的臀部的样子。梅尔库洛夫哈哈笑起来。
“我们这间土屋里只要有个澡盆就行,——水要多少有多少。”
“你们这儿太潮湿啦,大潮湿啦,”卡尔梅科夫打量着圆木筑起的墙和咕卿咕卿响的土地,愤愤地说。
“旁边就是沼泽,还能不潮湿。”
“你们要感谢至高无上的神,叫你们呆在沼泽地边,就像在基督怀抱里一样舒服,”本丘克插嘴说。“其他地区都在进攻,可是我们这儿一个星期却只打一梭子弹。”
“去冲锋陷阵也比在这儿活活烂掉好得多。”
“彼佳大叔,养活哥萨克,可不是为了要他们去冲锋陷阵送死啊。你是假装胡涂。”
“那么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照惯例,政府只是在关键时刻才打哥萨克这张王牌。”
“净说鬼话,”卡尔梅科夫摆了摆手。
“这怎么是鬼话!”
“就是。”
“算了吧,卡尔梅科夫!真理是驳不倒的。”
“这算什么真理……”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你装什么傻呀?”
“注意,诸位军官!”丘博夫叫道,像演戏似的向四面鞠着躬,指着本丘克说道:“本丘克少尉马上就要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圆梦书说梦啦。”
“您又在出洋相啦?”本丘克的眼睛紧逼着丘博夫的视线,冷笑道。“不过,您继续出您的洋相吧——人各有志嘛。我是想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再也看不到战争啦。阵地战刚一开始,哥萨克团队就统统被分散到僻静的地方待命。”
“然后呢?”利斯特尼茨基收拾着棋子问道。
“然后,一旦前线上开始骚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士兵已经开始厌恶战争,逃兵越来越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到那时候,要镇压叛变,哥萨克就派上用场了。政府养活的哥萨克,就像系在木棍上的石头。紧要关头,政府就要用这块石头去打破革命的头盖骨。”
“我的亲爱的,你简直是着迷啦!你的假设太不能令人信服啦。首先,无法预先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再说,你怎么知道将来要发生骚动以及其他等等事件呢?
假定出现另一种情况:协约国打垮了德国人,战争以辉煌的胜利结束,——到那时你给哥萨克安排什么用场呢?“利斯特尼茨基反驳道。
本任克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目前还看不出什么结束的征兆,更不用说辉煌胜利的结局啦。”
“战争拖下来了……”
“还要继续拖下去,”本丘克预言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休假的?”卡尔梅科夫问道。
“前天。”
本丘克把嘴鼓得圆圆的,用舌头弹出一个小烟团,扔掉烟头。
“你到哪儿去啦?”
“彼得格勒。”
“噢,那儿怎么样啊?京城里热闹吗?唉,他妈的,要是能到那儿,哪怕就住一个星期呢,出什么代价,我都不在乎。”
“令人高兴的事情也不多,”本丘克斟酌着字眼,说道,“面包奇缺。工人区里到处是饥饿、不满和无声的抗议。”
“咱们要想熬过这场战争也不那么容易。你们以为怎样,诸位?”梅尔库洛夫疑问地环顾了一下所有在场的人。
“日俄战争引起了一九零五年的革命,——这次战争势必以新的革命收场。而且不仅是革命,还要发生国内战争、”
利斯特尼茨基听着本丘克的话,作了个含糊不清的手势,仿佛想打断少尉的话,接着,站起身,皱着眉头,在土屋里踱起步来。他抑制着满腔的愤怒,说话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在我们军官中竟会有这样的人物,”他朝有点儿驼背的本丘克那面指了指。“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他对祖国,对战争的态度……他在一次谈话中虽然说得很含糊,但足以证明了他的立场,他希望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我这样理解对吗,本丘克?”
“我是希望战败的。”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不管你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希望自己的祖国战败——这毕竞是……对国家的背叛。这对任何一个正派人来说,都是——耻辱!”
“你们还记得吗?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就曾鼓吹反对政府,从而加速战争的失败。”梅尔库洛夫插嘴说。
“本丘克,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利斯特尼茨基问道。
“我既然希望战败,那我自然是同意的;作为一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竟会不同意自己议会党团的观点月n 岂不是笑话。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使我更为惊奇的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政治上竟如此无知……”
“我首先是个忠于沙皇的士兵。我一见到‘社会党同志们’的那副尊容就恶心。”
“你首先是个混蛋,然后才是个自鸣得意的粗野军人,”本丘克心里这样想,敛去笑容。
“除了阿拉,再也没有神啦……”
“在我们军界,情况是特殊的,”梅尔库洛夫好像很抱歉似地插嘴说,“我们大家似乎都远离政治,我们都住在村头上。”
卡尔梅科夫大尉坐在那里,持着下垂的胡子,两只炽热的、蒙古人的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丘博夫躺在床上,一面听着人们的谈话,一面在着梅尔库洛夫那张贴在墙上的、被烟草熏黄的画片: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脸像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惹人心烦地、轻佻地含笑看着自己袒露的胸膛。左手的两个手指头揪着棕色的奶头,小拇指小心翼翼地高高翘起,低垂的眼皮下面有一片阴影,瞳人闪着温暖的光亮。她微耸起肩膀,托着要滑下来的衬衣,锁骨窝里有一片柔和的光影。女人的姿态是那么自然、优雅,整个画面色调暗淡,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使得丘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人神地欣赏起这幅绝妙的绘画来,传到耳边的谈话,早已成了耳旁风。
“这太好啦!”他的眼睛离开画片,大声称赞道,但是太不凑巧,本丘克恰好说完下面这句话:“……沙皇制度一定要被消灭,你们可以深信不疑!”
利斯特尼茨基手里转弄着纸烟,恶意地笑着,一会儿看看本丘克,一会儿看看丘博夫。
“本丘克!”卡尔梅科夫叫道,“您等等,利斯特尼茨基!……本丘克,您听见了吗?……噢,好,就算这次战争将要变成内战……以后又怎么样呢?好,你们推翻帝制……那么以阁下之见,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呢?政权又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类似国会,是吗?”
“国会算得了什么!”本丘克笑着说。
“那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实行工人阶级专政。”
“嘿,真有你的!……那么知识分子和农民扮演什么角色呢!”
‘农民会跟着我们走的,一部分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也会跟我们走,而其余的那些……对其余的那部分人我们就这么处理……“本丘克迅速地把原来捏在手里的一张纸拧成紧紧的纸捻儿,然后摇晃着这根纸捻儿,从牙齿缝里挤出这样的一句话:”就这么处理这帮家伙!“
“您飞得也太高啦……”利斯特尼茨基嘲讽地说。
“我们就是要居高临下,”本丘克结束说。
“地上可要先铺上些于草……”
“那您为什么还要志愿参军上前线,而且还晋升为军官?这又怎么跟您的见解相吻合呢?真——是——太——妙——啦!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嗨嗨……反对消灭自己这些……阶级兄弟——却突然……晋升为少尉!”
卡尔梅科夫用手巴掌在靴筒上拍了一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您指挥您的机枪队消灭了多少德国工人?”利斯特尼茨基质问道。
本丘克从军大衣的侧袋里掏出一大卷纸,背朝着利斯特尼茨基,在纸卷里翻了半天,然后走到桌边,用宽大的手巴掌把一张日久变黄了的报纸铺平。
“我杀死过多少德国工人——这是……个问题。我志愿到前线来,是因为早晚也会把我抓来。我想,在前线,在战壕里学到的东西,将来会有用的……将来。看,这儿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他念起列宁的文章来:就拿现代的军队来说吧。军队是组织的一个好范例。这种组织所以好,就因为它灵活,同时又能使千百万人服从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动员令一下,他们就会在指定地点集合。今天他们还蹲在战壕里,有时得蹲几个月,明天他们就会以别的队形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避开枪林弹雨创造出奇迹,明天他们又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上地雷,明天他们会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俄里。受同一意志所感召的千百万人,为了同一目标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以适应改变着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
“‘形势’是什么玩意儿?”丘博夫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本丘克的身子晃了一下,如大梦初醒,他想弄明白问话的意思,用大拇指的关节擦了擦疙疙瘩瘩的前额。
“我问你,‘形势’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是懂的,可是我却不能清楚地讲出来……”本丘克脸上露出开朗、单纯、稚气的笑容;在他那忧郁的大脸上出现这样的笑容显得那么不协调,就像一只浅灰色的小兔崽子欢蹦乱跳地掠过秋雨后忧郁、凄凉的田野一样。
“形势——就是情况。局面等等的意思吧,我说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