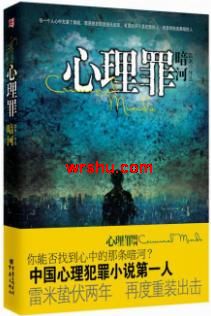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2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流东西!”
哥萨克从草垫子下面拿出步枪,扯着老婆的一只手,没好意思当众亲嘴,只把妻子的硬邦邦的手在自己的手里握了一会儿,悄悄说了几句话,就跟着战斗队的一个战士往村里的小学校走去。
聚集在荫凉的、树木参天的夹道里的车辆像打雷似地轰隆轰隆地驶过桥去。
这个岗哨在一个钟头内,就扣留了五十来个逃兵。其中有几个在扣留他们的时候还进行过反抗,特别是一个留着大胡子、样子很凶、已经不很年轻的叶兰斯克镇下克里夫斯克村的哥萨克。他根本不理睬哨长叫他下车的命令,却把马抽了一鞭子。
两个哨兵抓住了他的马笼头,一直到了桥的那边才把车拦住。这时哥萨克没有多加思索,从衣襟下拿出一支美国温彻斯特来复枪,往肩膀上一背“让开道!……混蛋,我打死你!”
“下来,下来!我们有命令,凡是不服从命令的格杀勿论。我们马上请你吃黑枣儿!”
“庄稼佬!……昨天你们还是红党呢,今天就教训起哥萨克来啦?……臭不要脸的!……让开,我要开枪啦!……”
一个裹着副崭新的冬季裹腿的战士,站在大车前轮上,经过短促的交手后,把来复枪从哥萨克手里夺了下来。哥萨克像猫一样躬起腰,顺手从雨衣下面的刀鞘里拔出马刀,跪在那里,隔着拴在车上的油漆摇篮刺过去,刀尖差一点儿没刺到及时躲开的战士的头上。
“季莫沙,拉倒吧!季莫纽什卡!啊呀,季莫沙!……不要这样啊!……别斗气啦!……他们会杀死你的!……”哥萨克那发疯似的、枯瘦如柴的丑老婆,痛心地哭号起来。
但是他全身直立站在车上,挥舞着蓝光闪闪的马刀,折腾了半天,不让战士们靠近马车,不住目地、沙哑地骂着,眼睛发疯似地四下打量着。“滚开!我要砍啦!”
他那黝黑的脸在抽搐,浅黄色的长胡子下面冒着唾沫泡,浅蓝色的白眼珠儿变得越来越红。
好容易才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摔倒在地,捆了起来。这个厉害的哥萨克之所以这么逞能好斗,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在马车上一搜,就搜出了一个已经打开盖的、装着烈性的头锅烧酒的大瓶子……
树阴夹道上出现了空前的拥塞。大车紧紧地挤在一起,不得不把牛马卸了,用人力把车推拉到桥边去。车杆和车辕僻啪断裂了,牛马被牛虹叮咬,愤怒地尖声嘶叫,不听主人的吆喝,烦得发狂,往篱笆上乱撞。咒骂、呼喊、鞭子声和妇女的哭号声在桥边响了好久。后面的许多车辆在可以转弯的地方都掉转车头又回到大道上去,想下到顿河岸,赶往巴兹基村。
被扣留的那些逃兵都被押送到巴兹基去,但是由于他们全都带着武器,所以押送兵根本管不了他们。逃兵和押送的战士们立刻就在桥边打了起来。过了不久,战斗队的战士就都回来了,逃兵们却有组织地自己向维申斯克开去。
在大雷村,普罗霍尔。济科夫也被拦住了,他把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发给他的休假证明拿出来,一点儿也没有留难就放行了。
他到达巴兹基的时候,已经近晚了。从奇尔河沿岸各村涌来的几千辆大车,塞满了所有的大街小巷。顿河边上,一片混乱。难民们把大车排在岸边,足有两俄里长。五万多人分散在树林里,等候渡河。
炮兵连、司令部和军需品正在维申斯克对面的河边乘渡船过河。许多小船在摆渡步兵。几十只小船在顿河上穿梭,每船摆渡三四个人。码头附近水边拥挤、混乱异常,像开了锅似的。担任后卫队的骑兵部队一直还不见来。大炮的轰鸣声,仍旧不断地从奇尔河方面传来,而刺鼻的辛辣焦臭气味变得越来越浓。
渡河工作一直继续到大亮。夜里十二点钟左右,第一批骑兵连队开到了。他们要在黎明时开始渡河。
普罗霍尔。济科夫听说第一师的骑兵还没有到,就决定在巴兹基等候自己的连队。他费了很大的劲,才牵着马,穿过密密层层地拥挤在巴兹基医院围墙旁边的车辆,没有卸鞍子,把马拴在一辆不知道是谁的大车辕上,松了马肚带,就在大车队里找起熟人来。
在堤岸附近,他远远地看见了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她把一个小包袱抱在怀里,肩上披着一件暖和的上衣,正在朝顿河边走。她那艳丽刺眼的美貌,引起了聚集在岸边的步兵们的注意。他们对她讲些猥亵的话,他们落满尘土的汗淋淋的脸上露出笑容,闪着白晃晃的牙齿,传来阵阵下流的笑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头发哥萨克,穿着没系带的衬衣,皮帽子歪在后脑勺上,从后面抱住她,把嘴唇贴在她那清秀、黝黑的脖颈上。普罗霍尔看到,阿克西妮亚猛地把哥萨克推开,凶狠地张开嘴,不知道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四周响起一片哄笑声,那个哥萨克摘下皮帽,嘶哑地低声说:“唉,大嫂子啊!你就叫我亲一下嘛!”
阿克西妮亚加快了脚步,从普罗霍尔面前走过去。她那丰满的嘴唇上颤动着轻蔑的微笑。普罗霍尔没有招呼她,他正在人群里寻找同村的人,在车辕呆呆地朝天坚起的大车群中慢悠悠地穿行,听到一些醉话和笑声。一辆大车底下铺着块粗麻布,上面坐着三个老头子。一个老头子的两腿中间放着一个酒桶。这几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正在用炮弹壳做的钢杯子轮流舀着喝酒,嚼着干鱼片。浓烈的酒气味和腌鱼的咸味馋得饿得发慌的普罗霍尔停下脚步。
“老总!但求万事大吉,跟我们一块儿喝一杯吧!”一个老头子招呼他说。
普罗霍尔也没有客气,就坐了下来,画过十字,笑着从好客的老头子手里接过盛满散发着香甜诱人的香气的烧酒杯。
“趁现在还有日气,喝吧!哪,就一块成鱼。小伙子,你别厌恶老头子们。老头子都是聪明人!你们年轻人还得向我们学学怎样过活……哦,和怎么喝酒呢,”
另一个鼻子塌下去、上嘴唇豁得露出了牙龈的老头子瓮声瓮气地说。
普罗霍尔担心地斜眼看着那个没有鼻于的老头子,喝于了杯里的酒。在喝完第二杯、准备喝第三杯的时候,他按捺不住,问:“老大爷,你的鼻子是浪荡掉的吧?”
“不——不,亲爱的人哪!是冻掉的,还是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冻得生病,就这样把鼻子冻坏啦。”
“我错怪你啦,我以为:是不是害花柳病把鼻子烂掉了?我可不要传染L 这种脏病呀!”普罗霍尔坦白地承认说。
老头子的这番话使他放心了,他贪婪地把嘴唇凑到杯子上去,放心地一饮而尽。
“活到头啦!怎么能不大喝呀!”烧酒的主人是个壮实、魁梧的老头子,哇啦哇啦喊着。“你们瞧,我拉着二百普特麦子,还有一千普特扔在家里。赶着五对牛,可是现在非得把这些东西都扔在这儿不可啦,要知道不能牵着它们渡过顿河呀!我积攒的全部家当全都要完蛋啦!我想要唱歌!玩乐吧,乡亲们!”老头子满脸都涨紫了,热泪盈眶。
“不要哭喊啦,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莫斯科——是不相信你的眼泪的。咱们只要能活下去——还会积攒起来的!”瓮鼻子的老头子劝导朋友说。
“我怎么能不哭呀?!”老头子的睑哭得都变了样子,提高了嗓门说。“粮食都完啦!牛都要死啦!红党要把房子烧掉!儿子秋天战死了!我怎么能不哭呀?我为谁挣了这份家业呀?从前,我总是累得汗流浃背,一个夏天要穿烂十件衬衣,可如今却成了光屁股光脚的……喝吧!”
普罗霍尔听着谈话,吃了一块像炉盖那么大的咸鱼,连喝了七杯烧酒,肚子撑得饱饱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站起来。
“老总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要不要给你的马拿一点粮食,要多少都行?”
“来一口袋!”普罗霍尔嘟哝说,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无动于衷。
老头子给他倒了一草袋上等燕麦,帮着他扛到肩膀上。
“别忘了把口袋送还我!看在基督的面上!”他抱住普罗霍尔,流着醉醺醺的眼泪,请求说。
“不,我不给你送回来。我说啦——我不送回来,就是不送回来……”普罗霍尔也不知道为什么固执地说。
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大板车。草袋子压弯了他的腰,直往两边晃。普罗霍尔觉得,自己仿佛是走在结了一层很滑的薄冰的地上,腿向四面乱滑,直哆嗦,就像匹没钉马掌、小心翼翼地走在冰上的马。他又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他怎样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戴帽子来,还是没有?一匹拴在马车上的白头顶枣红马闻到了燕麦味,把头伸过来,咬破了口袋角。麦粒从破口里沙沙响着漏了出来。
普罗霍尔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又往前走去。
也许本来可以把剩下的燕麦扛到自己的马那里。但是当他走过一头大牛跟前时,那牛忽然发起牛脾气,从旁边踢了他一脚。牛被牛虹和蚊子咬得痛苦不堪,又热又烦,简直要发疯,根本不让人靠近。在这一天,普罗霍尔已经不是第一个沦为牛发脾气的牺牲品,他被一脚踢出去老远,脑袋撞到轮上,立刻也就睡过去了。
半夜,他醒了过来。铅灰色的黑云在他头顶上灰色的夜空中盘旋着,迅速地向西方飘去。弯弯的新月偶尔从云隙中钻出来,但是很快乌云又遮蔽了天空,凉爽的夜风在黑暗中仿佛吹得更强劲了。
骑兵部队正从普罗霍尔躺在下面的那辆大车附近开过去。大地在无数钉着铁掌的马蹄子下呻吟、叹息。马匹闻到了大雨将至的气息,直打喷嚏,马刀碰在马镫上叮当乱响,闪晃着烟头的红光。开过去的骑兵连队带来一阵阵浓重的马汗味和皮缰辔的酸味。
普罗霍尔——跟所有的服役的哥萨克一样——在战争年代里,已经闻惯了这种骑兵独具的混合气味。哥萨克把这种气味从普鲁土和布科维纳一直带到顿河草原,这种骑兵部队固有的、永久的气味,就像是自己家宅里的气味一样,使人感到那么亲切、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