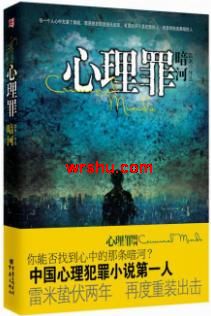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20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直立起来……把我扔下来……他们就会把我打死!……“已经朝他打了两枪,仿佛是从远处传来一阵喊声:”我们活捉他!“眼前是一张英勇的、前额光光的、张牙露齿的脸,无檐帽的飘带迎风乱舞,帽箍上的金字已经褪色,暗淡无光……葛利高里紧踏马镫,挥刀砍去——觉得刀锋黏糊糊地砍进了水兵柔软的、有弹性的身躯。第二个水兵脖子很粗、身体健壮,开枪打穿了葛利高里左肩上的肌肉,当即就被普罗霍尔。济科夫的马刀削去半边脑袋,倒在地上。葛利高里拨马朝近处的枪栓响处冲去。一个黑乎乎的步枪口正从装着机枪的马车后面伸出,直对着他的脸。他使劲把身子往左一歪,连马鞍子都活动了,呼哧直喘的发疯的马也跟着晃了一下,躲开了在他头顶尖声号叫的死神,在马跃过机枪马车的车辕时,砍死了那个开枪的水兵,水兵的一只手还没来得及用枪栓把第二颗子弹顶进枪膛。
在短短的一瞬间(后来这一瞬间在葛利高里的脑子里却变成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他砍死了四名水兵,也不听普罗霍尔。济科夫的呼叫,又去追赶藏在胡同拐弯处的第五个水兵。但是这时赶到葛利高里面前去的连长抓住了他的马笼头。
“你往哪儿去呀?!他们会把你打死的!……板棚后面他们还有一挺机枪呢!”
又赶来两个哥萨克和普罗霍尔,他们立刻下了马,跑到葛利高里跟前,强行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他在他们的手里挣扎着,喊:“放开我,坏蛋!……我要把这伙水兵!……统统……砍死!……”
“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麦列霍夫同志!请您清醒清醒吧!”普罗霍尔苦苦地劝他说。
“你们放开我吧,弟兄们!”葛利高里已经换了另一种颓丧的声调请求说。
哥萨克们放开了他。连长悄悄地对普罗霍夫说:“扶他上马,护送他到古森卡去,看样子,他是病啦。”
连长朝马走去,命令连队:“上——马!……”
但是这时葛利高里把皮帽子往雪上一扔,摇摇晃晃地站了一会儿,忽然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大声哼哼起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扯起身上穿的军大衣扣子。连长还没来得及朝葛利高里迈出一步,他就一头栽到地上,裸露的胸膛贴在雪上。他号哭起来,哭得浑身直哆嗦,像狗一样,用嘴舔着篱笆边的残雪。后来,在神智清醒的那一刹那,他想站起来,但是怎么也起不来,于是他扭过泪流纵横、被疼痛弄得不成样子的脸,朝聚集在他四周的哥萨克们,声嘶力竭、粗野地呼喊:“我砍死的是什么人呀?……”他生平第一次在痛苦地抽搐中挣扎,满嘴喷着白沫喊叫:“弟兄们,我是得不到饶恕的!……看在上帝面上,砍死我吧……为了圣母……把我处死吧!……”
连长赶忙跑到葛利高里跟前,同一个排长一起,弯腰俯在他身上,把系马刀的皮带和军用背包扯下来,捂上他的嘴,压住腿。但是他的身子虽然被他们压着,好半天还弯得像弓一样,用两条痉挛着的、挺直的腿乱刨着细雪,一面哼哼着,一面用头往马蹄翻起的、闪着亮光的、肥沃的黑土地上乱撞,他生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曾充分享受了生活为他准备的一切——甘少苦多。
只有野草是这样在土地上生长,它吮吸着能创造生命的土地的奶汁,漠不关心地接受阳光的抚爱和恶劣天气的摧残。在暴风雨致命的袭击中驯顺地倒下去。然后,把种子迎风撒去,同样是那么漠不关心地死去,枯萎的草茎沙沙作响,向照耀着死亡的秋阳致敬……
第六卷 第四十五章
第二天,葛利高里把全师的指挥任务交代给自己属下的一位团长,由普罗霍尔。济科夫陪着,去维申斯克了。
卡尔金斯克镇外有一大片很深的洼地,洼地上有一个叫草席塘的池塘,水塘里落满了停下来休息的野雁,在水上游嬉。普罗霍尔用鞭于朝水塘方向指了指,笑着说:“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要能打一只野雁就好啦。咱们就可以用它来下酒!”
“好,咱们走近一点儿,我用步枪试试看。我的枪法曾经相当不错。”
他们向洼地深处驰去。普罗霍尔牵着马停在一道隆起的土坡后面,葛利高里脱下军大衣,把步枪的保险机扣上,顺着一条还残留着去年的灰色艾蒿的浅沟向前爬去。他爬了半天,几乎连头也没有抬,就像是去侦察敌人的潜伏哨似的往前爬,就像当年在德国前线,在斯托霍德河附近摸德国哨兵时那样。褪色的保护色军便服和褐绿色的田野混成一体,小沟隐蔽着葛利高里,使那只翘着一条腿站在水边春汛冲出的棕色小丘上守望的野雁的尖利眼睛看不到他。葛利高里爬到能进行短距离射击的地方,略微欠起一点儿身于;那只守望的野雁扭动着像石头一样灰色的、蛇似的脑袋,警惕地四面张望着。它的身后有一群雁散浮在水面上,很像盖了一块浅黑色的苫布,它们一会儿呱呱叫几声,一会儿又把脑袋扎进水里。轻微的咕咕派派的鸣声和水的溅拍声从水塘边传来。“可以固定瞄准,”葛利高里想道,心怦怦直跳。
把枪托子靠在肩膀上,瞄准那只守望的野雁。
开枪以后,葛利高里跳了起来,被雁群的鸣叫和翅膀的煽动声震得耳朵都要聋了。他要打的那只野雁慌忙振翅高飞,其余的野雁也都飞起,像一块浓云似的在水塘上空飞舞。葛利高里很伤心,又朝飞起的雁群打了两枪,一面注视着有没有野雁落下来,一面向普罗霍尔走去。
“瞧啊!瞧啊!……”普罗霍尔跳到马鞍子上,直立在上面,用鞭子指着在蔚蓝的晴空中远去的雁群喊道。
葛利高里扭回身去,兴奋和猎人样的激动。使他浑身直哆嗦:一只野雁离开已经排好行列的雁群,缓慢地时断时续地煽动着翅膀,急速地落了下来。葛利高里踮起脚尖,用手巴掌搭在眼上,盯着这只雁。孤雁离开了惊鸣的雁群,向一边飞去,越飞越没有力气,缓缓下落,忽然像一块石头似的从高空坠下,只有翅膀下面雪白的羽毛被太阳照得闪光耀眼。
“上马!”
普罗霍尔张开大嘴笑着,跑过来,把缰绳扔给葛利高里。他们向山坡疾驰而去,一气跑了足有八十沙绳远。
“就是它!”
野雁伸着长脖子,展开翅膀,躺在那里,仿佛是在最后一次拥抱这片冷酷的土地。葛利高里没有下马,俯身捡起打落的野雁。
“子弹打中它什么地方啦?”普罗霍尔好奇地问。
子弹打穿了雁嘴的下部,把眼睛旁边的骨头打歪了。死神在它飞翔的时候追上了它,把它从排成人字形的雁行里揪出来,扔到地面上。
普罗霍尔把雁系在马鞍上。两人又上路了。
他们把马留在巴兹基村,坐渡船过了顿河。 葛利高里到了维申斯克,就住在一个熟识的老头子家里,吩咐赶快把野雁拿去烤,自己并未到司令部去,却派普罗霍尔去买烧酒,一直喝到黄昏。谈话中主人大发牢骚说:“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们维申斯克的长官有点儿太专横啦。”
“什么长官?”
“那些自封的长官呀……库季诺夫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他们怎么啦!”
“他们总是欺压那些外来户。谁要是跟红军走了,就把他们的婆娘、女儿和老头子关进监牢。我的亲家母为了儿子的缘故,也被关起来啦。这简直太没道理!哼,比如说吧,你跟着士官生跑到顿涅茨河那岸去了,红军就把令尊——潘苔莱。普罗珂菲奇——关进监狱去,这恐怕是不对头吧?”
“当然不对啦!”
‘可是这儿的政权却就要关。红军从这里过,谁也没有欺压,可是这些人却变得像疯狗一样,乱咬一气,哼,他们无法无天!“
葛利高里站起来,微微地摇晃了一下,伸手去拿搭在床头上的军大衣。他只是稍有醉意。
“普罗霍尔!拿马刀来!拿手枪来!”
“您上哪儿去,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
“用不着你管!叫你拿什么,你就拿什么。”
葛利高里挂上马刀和手枪,扣上军大衣扣子,扎上腰带,径直朝广场上的监狱走去。站在门口的一个非战斗部队的哥萨克卫兵想阻拦他。
“有通行证吗?”
“让我进去!告诉你,躲开!”
“没有通行证什么人我也不能放进去。还没有这样的命令。”
葛利高里把马刀还没有抽出一半来,哨兵已经躲到门里去了。葛利高里跟在他后头,手不离刀柄,闯到走廊里。
“把典狱长给我叫来!”他喊道。
他脸色灰白,鹰钩鼻子恶狠狠地弯着,紧皱着眉……
一个担任看守的瘸腿哥萨克跑了过来,满脸孩子气的文书从办公室朝外张望了一下。睡眼惺松、怒火冲天的典狱长很快就来了。
“没有通行证乱闯——你知道吗,这是要判罪的?!”他哇啦哇啦地吼叫起来,但是一认出是葛利高里,仔细瞅了瞅他的脸,丧魂失魄地结巴说:“原来是您哪,老老……麦列霍夫同志,是吧?怎么回事?”
“拿牢房的钥匙来!”
“牢房的钥匙!”
“怎么,还要我给你重复四十遍吗?好啦,快把钥匙拿来,狗崽子!”
葛利高里朝典狱长迈了一步,典狱长往后退了退,但是还是相当坚决地说:“钥匙我不能给。您没有权利这样做!”
“权——权‘……”
葛利高里的牙齿咬得咯吱直响,抽出了马刀。马刀在他手里嗖嗖响着,在走廊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画了一个耀眼的圈子。文书和几个看守都像受惊的麻雀,四散逃命,典狱长紧靠在墙上,脸色变得比墙还自,嘟哝说:“您就胡来吧!哪,给您钥匙……可是我要去控告。”
“我就是要胡来给你看看!你们在后方待惯啦!……你们在这儿充他妈的英雄好汉,把娘儿们和老头子关进监狱!……我要把你们这帮家伙全都轰走!全给我上前线去,混账东西,不然我立刻就把你砍死!”
葛利高里把马刀插回刀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