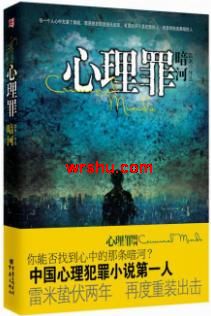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1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概也正是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正当莫斯科国事会议的成员会间休息时,大剧院的走廊里有两位将军——一位身体瘦小。生着一张蒙古人的脸,另外一位是个身强力壮、肩膀上结实地长着一颗留着平头的四方脑袋,略微有些斑白的鬓角梳得平平正正,耳轮紧贴在鬓发上,——他们离开众人,一面在细木块铺的地板上来回踱着,一面在低声交谈。
“宣言的这一条将要规定取消军队里的各种委员会吗?”
“是的。”
“统一战线,紧密团结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实施我提出的那些措施是无法挽回局势的。陆军已经根本不能打仗啦。这样的军队不仅不能赢得这场战争,甚至连稍微像样点的迸攻都顶不住_而巨有些部队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瓦解了。那么这里,后方的情况呢?您看,工人对任何企图使他们就范的措施的反应是什么呢?
——罢工和示威。我们会议的成员只能步行来开会……这简直是耻辱!!后方必须实行军事化,必须规定严厉的惩戒措施,无情地消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害人精——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最迫切的任务。将来我也可以继续得到您的支待吗,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是无条件支持您的。”
“对此我深信不疑。谢谢您。您看到了吧,已经到了必须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而政府却只限于敷衍塞责和说漂亮话——什么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那些企图像七月那样推翻人民政权的人’啦一不,我们向来是先做后说。而他们却恰恰相反。好吧……有他们吞食自己敷衍政策恶果的时候。但是我不想参与这种不诚实的游戏Z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主张公开的斗,我不喜欢说空话。”
身材矮小的将军停下来,站在跟他谈话的人的对面,旋转着他的深保护色军服上的铜钮扣,由于激动,讲话有些结巴:“他们自己给这些恶棍摘下笼头,现在自己却被革命民主政治吓得发抖啦,要求把可靠的军队从前线调到首都来,而同时又为讨好这种民主政治,不敢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进一步,退一步……只有把我们的力量完全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用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政府让步,如果他们不让步,——那么咱们就走着瞧吧!我将毫不犹豫开放前线,叫德国人来教训教训他们!”
“我们已经和杜托夫谈过。哥萨克会全力支持您的,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
咱们需要商量的是如何协调将来的共同行动。“
“开完会以后,我在驻地恭候您和其他诸位光临。你们顿河那儿的情绪怎么样!”
那位身强力壮的将军把刮得发光的四方下巴紧靠在胸前,忧郁地皱起眉头,直瞅着自己的前方。大胡子下面的嘴角哆嗦着,回答说:“我对于哥萨克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信心了……而且现在根本就很难判断他们的情绪。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哥萨克应该做些什么,使外来户拥护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效果如何,却不敢担保。我担心,当哥萨克和外来户在双方利益冲突时,会各走极端…
…土地问题……双方的思想都在围着这个轴心打转转儿。“
“您手里要掌握一些可靠的哥萨克部队,一旦内部发生意外事件时保证自身的安全。等我回大本营后,跟鲁科姆斯基研究一下,大概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从前线抽调几个团到顿河地区去。”
“那我就太感谢您啦。”
“那么,今天咱们就谈谈快调我们将来共同行动的问题。我坚信拟定的计划会胜利实现,但是幸运也常常是不可靠的,将军……万一时运不济,它背弃了我,——我可以期望在你们顿河地区找到栖身之地吗!”
“不仅可以找到栖身之地,还可以受到保护。要知道哥萨克自古以来就是以好客闻名的呀。”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卡列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那忧郁的目光中的倦意减掉了几分。
一小时后,顿河军区司令官卡列金在会场向安静下来的听众宣读了《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宣言》。
从那无起,在顿河地区,在库班地区,在捷列克地区,在乌拉尔地区,在乌苏里江地区,在所有的哥萨克的土地上,从这边到那边,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撒下了一张像黑色的蜘蛛网一样的大阴谋网。
第四卷 第十五章
距离被六月战役的炮火抹掉的市镇废墟一俄里的地方,弯弯曲曲的战壕像蛇一样横在树林边。紧靠林边的一带地区由哥萨克特别连防守。
战壕后面,在一道茂密、难以通行的赤杨和小白桦绿树丛那面,是一片战前开采过的、闪着铁锈色亮光的泥炭沼泽;野蔷薇开出了像红莓果似的。喜人的花朵。
右面一点。在一块突出的树林边,横着一杀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使人觉得像是一条荒僻的、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树林的边沿,长满枯萎的、被枪弹扫射过的艾蒿,烧焦的树桩像驼背似的弓了起来,一带黄褐色的胸墙,弯弯曲曲的战壕沿着光秃秃的田野伸向远方一战场后面,就是开采过的。高低不平的泥炭沼泽和被炸得满目疮痍的道路——也还都使人感觉到生活的痕迹,人类劳动的痕迹,可是树林边上的土地却呈现出一幅凄凉、悲伤的画面,令人神伤。
从前在莫霍夫蒸气磨坊里当机器匠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天到附近一个驻扎着一类辎重队的小镇上去。直到傍晚才回来。他往自己土屋走的时候,遇上了扎哈尔。科罗廖夫。扎哈尔几乎是在跑,马刀乱碰着装满沙土的麻袋,胡乱挥舞着双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躲到一边给他让路,但是扎哈尔抓住他的军服扣子,转动着发黄的病态的白眼珠,低声说道:“你听说了吗?我们右面的步兵正在开拔!
他们要放弃阵地吧?“
扎哈尔那像凝固了的生铁水似的黑连鬓胡子乱成一团,眼睛流露出饥饿、愁闷的绝望神情。
“他们是怎么放弃阵地呢!”
“他们开走啦,至于怎么个放弃法——我不知道。”
“也许,是换防吧?咱们到排长那儿去打听打听。”
扎哈尔回过身,往排长的土屋里走去,两只脚在粘滑、潮湿的泥地上直打滑。
过了一个钟头,这个连由步兵替换下来,向市镇开去、第二天早晨,大家从看守马匹的战士手里牵过战马,用强行军的速度向后方开去。
细雨连绵,低垂的白桦树都像弯了腰似的。道路在林间穿行,马匹闻到潮湿的气味和去年的落叶浓烈的干枯、沉闷的气味,打着响鼻、快活地走起来。水汪汪的毒莓像粉红色的串珠一样挂在草丛上,雨水洗过的三叶草上的花朵像泡沫似的闪着刺眼的白光。风把沉重的雨点从树上吹洒到骑士们的身上、军大衣和军帽上尽是斑斑的黑点,像是被枪砂子打过一样。一缕缕正在消失的马合烟的烟雾在队伍的上空飘荡。
“把咱们抓过来——扔过去,鬼知道他妈的又往哪儿赶我们。”
“战壕里的日子难道你还没有过厌吗?”
“真的,这又要把咱们赶到哪儿去呀!”
“一定是进行什么改编吧_”
“不太像改编。”
“唉,乡亲们、抽口烟——一切苦恼就都忘啦!” “我把自个儿的苦恼全装在马料袋里……”
“大尉老爷,您准许唱个歌儿吗!”
“可以吗?……起头儿吧,阿尔希普!”
前排有个人咳嗽了一声,唱道:有几个哥萨克退伍了,骑上骏马回家乡。
肩上挂着肩章,胸前佩着十字章。
几个像受了潮似的声音无精打采地唱了两句就沉默了。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在一排的扎哈尔。科罗廖夫在马镫上站起来,大声嘲笑道:“喂,你们这些瞎老头子!难道咱们就这副可怜相唱歌吗?你们这是在教堂门口擎着破碗,唱‘乞讨歌’哪。歌手们……”
“好啊,那你就领唱吧!”
“他的脖子太短,没有长嗓子的地方。”
“你吹过牛皮,把尾巴往旁边一翘,就算完事啦!”
科罗廖夫把长了虱子的大黑连鬓胡子握在手里,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拼命挥了一下马缰绳,唱出了第一句:哦哦,勇敢的顿河哥萨克们,欢声歌唱吧……
连队好像被他的歌声惊醒了,唱道: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光荣!……
歌声在雨水淋淋的树林上空,在狭窄的林间小路上空荡漾:哦哦,我们要为所有的朋友们做一个榜样,我们开枪射杀敌人!
我们射杀敌人,仍然保持齐整的战斗队形。
我们唯命是从。
长官大人怎么命令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冲——砍杀敌人!
行军的路上大家一直唱着歌,庆幸可钻出了“狼坟”。黄昏前就上了火车。兵车向普斯可夫开去。刚开过三站,大家已经都知道连队是和骑兵第三军团的其他部队一同开往彼得格勒,去镇压已经开始的骚乱;这个消息传开以后,谈话声就静了下来。红色的车厢里长时间笼罩着一片朦胧欲睡的寂静:“刚出火坑。又进地狱!”
又瘦又高的博尔谢夫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二月以后就没有更换过的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在第一次停车的时候就到连长那里去了“哥萨克都很激动,大尉阁下。”
大尉盯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巴上的一个深洼看了半天,笑着说:“亲爱的,我也很激动呢。”
“要把我们运到哪儿去?”
“去彼得格勒。”
“去镇压吗?”
“难道你以为——是去帮助骚动吗?”
“我们既不愿意去镇压,也不愿意去帮助骚动。”
“他们可完全不征求咱们的意见。”
“哥萨克们……”
“‘哥萨克们’怎么样!”连长已经是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自己知道,哥萨克们在想什么、难道我高兴干这种差使吗?赶快拿去在连里念念一下一站我跟哥萨克们谈谈、”
连长交给他一封叠起来的电报,然后皱起眉头,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嚼起一块布满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