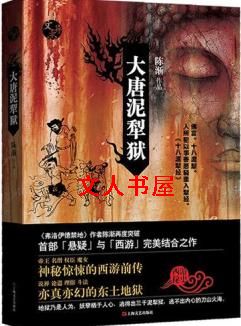大唐后妃传之珍珠传奇-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室外已站了一片子人,想没料到李俶突然出来,一时间跪的跪,站的站,一个个大气不敢出。李俶疑惑的望过去,宫女、内侍,或捧盅,或端药,或垂手,既有自己身旁服侍的,也有几名面熟,蓦的省起是御前侍候之人,听得“吭喀”的清嗓声,一名从七品服饰的太医由侧房出来。
李俶冷汗涔出,一个箭步上去,伸手抚开侧房的门,那外袍被门夹拉,悄然委地,却是浑不在意,只往内走。沈珍珠细弱的咳嗽之声隐隐传来,近身的宫女迎上李俶,见他的神情,不敢说话,手忙脚乱的为他掀帘,由他入内室。
沈珍珠半倚着床,方从一阵剧烈的咳嗽中渐渐平息,阖目养神。一名宫女持着手巾,为她拭额头细密汗珠,见李俶进来,正要施礼,李俶却劈手拿过手巾,扬眉示意她退下。
凝视沈珍珠片刻,愈发瘦弱苍白了,额头虚汗不止,顷刻绵绵密密层层叠叠,遂拿手巾点点沾拭。却听沈珍珠“嗯咦”一声,侧过面去,蹙眉咳嗽,开初一两声压抑低沉,谁知竟一发而不可止,挖心掏肺般又咳又喘,单薄的肩抖动得厉害,李俶挽住她半边身子,不住为她抚背顺气。
半晌,她抚胸稍定,似是无奈的望李俶一眼,半喘着气微声道:“看,我真是不中用——”
李俶伸指按于她唇上,摇头道:“不许再说话。你总是性子执拗,……竟然还瞒着我。我身子好了,不用担心。”她淡淡宽慰,笑着点头,由他扶着躺下,微微闭住眼;眼睑泛出缕缕淡青色。沈珍珠咳嗽不止一天一夜,原本因李俶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不多时侧头睡着。在睡梦中,仍不时咳嗽。
李俶待沈珍珠睡熟,更衣传太医问话。
沈珍珠缠绵病榻月余,方渐渐好转。
李俶形同往常,整日里于元帅府署理军务,或到亥时后归来,甚或彻夜不返。就算晚间不能回来,也必会遣人问候沈珍珠病情。
在若干静谧宁和的夜晚,待李俶在疲倦中沉沉睡熟,沈珍珠总会于半夜蓦然醒来,籍着温润月色,端疑他那张俊逸清泠的面庞。仿佛与从前是并无二致的,但总该有什么不同罢,他背负着那么多,何时开始,就是在她面前,也不说不透、不露端倪?一路随他而来的人,崔光远身任御史大夫,远在西北与数倍于已的叛军交战;陈周负伤隐匿,暂不能复用;刑部形同虚设,风生衣在刑部等同闲职;李倓身死……或许,他从未象现在这般孤独过。然而,他是李俶,这平静的背后,总有许多,是她无法想象的……
卧病其间的某日,叶护请得肃宗谕旨,进宫探望沈珍珠。沈珍珠半卧于床,令宫女掀起帐帷,与叶护相见。
叶护着回纥常服,领袖皆是宽阔而花样繁复的织金锦花边,显得尊贵华丽无比,眉眼中隐去几分犀利,行动中多出几分稳重,更显出与年龄不称的练达成熟。
沈珍珠实觉与叶护极为疏离,昔年一点名份,教她进退两难,絮絮叨叨问过他几年来经历,沈珍珠终于开口道:“还否记得陛下前月所语?在大唐可有称心的女子?”
叶护并不红脸,嘴角挟着一缕凌然众物的冷笑,稍纵即逝,温声答道:“大唐女子虽然千娇百嫣,可惜,都不是我所喜欢的。”
沈珍珠有些惊诧,谑笑道:“我却听闻你与安咸郡主甚是相投,陛下有意赐婚了。”安咸郡主是肃宗第七女,系肃宗为太子时侍妾周氏所生,年纪尚不足十四岁。
叶护微怔,一笑置之,道:“我对义母讲实话——安雪性如小孩儿,我回纥男子看重的女人,都是能助男子撑起半片天地的,我总不能讨个小孩儿回帐养着吧。我现在只是碍于父汗之命,屈意陪着那小郡主玩乐而已。”
“父汗之命?”沈珍珠默念此言,不明默延啜此举是何用意。
“父汗一直关切义母病情,”叶护见宫女出内室端药,面上有丝狡黠,低声道,“在广平王殿下彻夜不归时,曾数次潜入宫中探视义母,义母可知?”见沈珍珠惊得几近失神,又肃正容颜:“不过父汗因离回纥时日太久,昨日已启程回转哈刺巴刺合孙,军务暂交由我处置。”
就这样走了?沈珍珠蹙眉,虽说理由充分,但默延啜此行来中原,这般无功而返?叶护端坐面前,神情笃定自若,一丝儿也没有少年将军独处他国的怯弱,甚且带着几分悠闲,仿佛有所倚靠。以默延啜所言,叶护也是第一回领兵出征,默延啜当真放心放手,叶护真能这样无所恃?心中一凛,莫非——默延啜并没有离开?籍以离开之名,既让他处于暗处,避免一国之主身处他国的危机,也让唐室放松警惕?
默延啜到底在做何盘算?回纥固然势强,但以其之力,目前确实难以吞下整个中原。沈珍珠头有焦痛——这天底下男人,整日里盘算来盘算去,营营利利,总没有停止的一日。有些争斗迟早要发生,虽不是迫在眉睫。心底分明有了倦意,却仍要陪他们周旋下去。
叶护眸中闪闪发亮,说道:“义母在想什么?是否担心我回纥铁骑不能担当助大唐收复两京之任?还是有话要嘱咐我?义母之命,我决计听从。”
沈珍珠望向面前少年,倒生了耻辱的愧疚,脸上发烫,终于启口道:“你认我为母,也算得半个大唐之人。可否答应我,永不与大唐为敌?”
叶护碧深眸子里的亮光渐渐熄灭;微挑的嘴角扬起嘲笑,“今日义母嘘寒问暖,原来就为这最后一句话。”沈珍珠并不后悔,但也无言以对,自己行径固然卑鄙,然为国为家,她所能做到的,也不过仅此而已。
叶护嘴角一扯,还待讥笑,那眸中的晶莹之物却不听使唤的噙起,他扭头反手一把揩去眼泪,回首怆然而笑:“我还以为自己真有了母亲,原来,我终究是无人疼爱的孤儿。”
沈珍珠看着面前的叶护,恍惚中时光错离。十余年了,安庆绪失去母亲当夜,也是这般悲怆无助,愤世疾俗,他将一方白手巾蒙于逝去母亲面上,跪了半宿,只滚下一粒泪,“天地间再没有我的亲人。”她曾是那样怜悯他,以为世上只有她真正懂得他,然而终究一错再错,她再有万钧之力,也拉不回错堕深渊的他。
“叶护,”沈珍珠够不得未穿靴袜,跳下床揽住这少年的肩臂,她其实只比叶护大数岁而已,此时叶护身量反比她高大,倒让她只能仰望,“你我都让这身份羁绊住了。——若当初你肯跟我回大唐,也许今日情形全然不同。我这个义母确实名不符实,然而,可汗对你,却甚似亲子,有这样疼爱你的父亲,有没有我这样的义母,也不重要了。”说毕,将当日平远茶楼默延啜对自己所讲,一一转述给叶护。
叶护默不作声听完,眼中又噙起泪光,忽的抬头对沈珍珠道:“义母,我总记得极小的时候,母亲抱我在怀。你,可以象母亲一样,抱抱我吗?”
沈珍珠一怔,开初只觉要搂这偌个男儿入怀,甚是滑稽,但见叶护眼神殷切,再不是那日自负高傲的少年将军,只是一个幼失母爱的小孩儿,忆及自己也是幼年丧母,此时不仅忽起同病相怜之心,母性亦油然而生,长叹一口气,慢慢将叶护搂在怀中,肩头一颤,仿佛有泪润湿衣裳。
“大唐镇国夫人,”叶护按住沈珍珠肩头,慢慢后退两步,决绝于这短暂的亲情拥抱,面庞沉静而坚决,“我欠你一条命,自然会答应你的要求,只是——我没有母亲了——”他举袖,拭去眼角残余的泪痕,深深一揖,离开。
李俶晚间听说叶护来访,极是不豫,“父皇定要让你置身其中,处处为难。”
沈珍珠劝道:“父皇也是不得已为之,只是,他恐怕小看了回纥人。”遂将对默延啜的疑惑说与他听。
李俶眉间眼里溢出笑意,扶她躺下,轻拍她面颊,“睡吧,默延啜确实未走,但他暂时不会危害我们,且观后情罢。”
八月初四,肃宗制家宴于行辕内廷,高席以待叶护。
酒过三巡,肃宗笑谓叶护道:“朕拟不日兴兵讨贼,欲以王子之军为先锋,可否?”
叶护起身答道:“父汗已告诫臣儿,务以陛下所令为是,叶护听从陛下调遣。”
肃宗大喜,环顾在场诸子妃嫔,目光落于沈珍珠,甚有藵奖之意,对叶护道:“此行辛苦,朕必将大大酬劳回纥军士。”
叶护懒洋洋的将几案上一盅酒喝下,似有薄醉的睨目道:“陛下太过客气。我回纥与大唐本是姻亲,亲威有难,哪有不来帮忙的——只是,臣率兵千里而来,确不可空手而归。只请陛下应允,若我回纥兵马真的管用,克复长安洛阳后,容我军尽取两京女子、衣帛!”
沈珍珠大惊,手中酒盏微微漾动,李俶一只手伸过来,托住她的手臂。她斜觑,李俶神色如常,只托住自己的那只手力道加重,他是益发喜怒不形于外了。
哲米依隔着重重席宴,脱口道:“叶护,你在说什么!”
叶护端了一盏酒置于嘴边,挑眉冷笑道:“听说大唐有句俗语,‘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哲米依姑姑做了大唐王妃才几天,这样回护你婆家?大唐物庶丰厚,咱们回纥要这点东西算什么,陛下,您说呢?”
肃宗袍襟一揽,哈哈大笑,“这有何难?朕应允你就是!”此言一出,沈珍珠宛然看见,立于肃宗身侧的张淑妃释然吁气,再观身畔众人,却多有此种形态者,心下微凉。
八月初五。今秋酷热,沈珍珠正吩咐请产婆,以备近日素瓷生产,宫女匆匆来禀:“素瓷姐姐那边服侍的人刚刚来说:姐姐她今早起来,腹痛不已,怕是快生产了。”
沈珍珠心急火燎的带着两名产婆赶至,素瓷已在榻上痛得死去活来,产婆道:“要生了,要生了!王妃快请回避!”
沈珍珠在房外踱步半个时辰,听见里室“哇——”的婴儿哭声,响亮透彻。
产婆跑来报喜:“奴婢还没见过头胎生产这样顺利的呢!禀王妃,母子平安,是个大胖小子。”沈珍珠不曾想素瓷生产如此顺利,想起自己生李适时所受苦楚,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