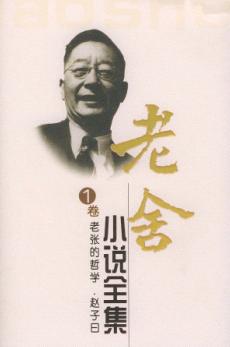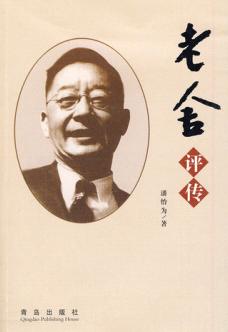怀念老舍-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
“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憾之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一九六七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一九五O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我不相信,迟至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一九五O年九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老舍死得悲壮,他是现代的屈原。
此文为纪念老舍逝世三十四周年而写二OOO年八月二十四日初稿
十一月八日补充修改
注: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舒乙首披:1968年诺贝尔奖本属老舍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事实内幕。
舒乙说,中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诺贝尔奖评选程序,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经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胜。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老舍与现当代文学中的幽默
孙洁
今年2月3日是老舍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老舍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大家,他幽默的创作风格是他在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个性中鲜明的特点,同时,这种幽默,也成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甜酸苦辣中较为独特的一味。
可以说,老舍的幽默形成于他独有的忧郁型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同步于中国现代作家共有的对时代对人生的焦灼与绝望感。当然,有些作家,如鲁迅,面对绝望,选择了战斗加以反抗,不过,老舍却是以幽默来化解与遮蔽它,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幽默对于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中国文学实在是不合时宜,老舍山东时期苦心经营的幽默宫殿先经受了时代的冲击,又终于在民族危机尖锐上升的“七七”之后轰然塌陷。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当说,直到最后20年才为幽默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与文化气候,这之前幽默文学的不发达是中国文学走进新文学阶段后背负的沉重历史宿命的一方面表现而已。老舍在山东的7年,即老舍以幽默特色横空出世之后渐入佳境的时期,中国文坛上也出现了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幽默热”。但是,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幽默杂志的涌现也好,“幽默年”、“小品年”的短暂繁荣也好,都只不过是两三文人一厢情愿织造的假象而已,注定了好景不长。这一来是因为这些幽默文学的逃遁倾向的确不利于它们向纵深处的发展,二则因为尚处于发轫期的中国幽默文学还不具备向主流文坛挑战的实力。中国幽默文学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致使它的发展在30年代、抗战时期以至整个40年代都远远落在讽刺文学之后。老舍进入抗战时期后搁置了幽默创作却磨砺了讽刺之笔也属大势所趋。
在“幽默”一词方经林语堂译出,还未得推广,大多数知识者并不习惯于用它的时候,周作人说:“我只觉得我们不很能说‘为滑稽的滑稽’,所说的大抵是‘为严正的滑稽’,这是我所略觉不满足的。
(《滑稽似不多——通信二》)“周作人以自由主义观幽默,似乎更能看清幽默之在中国的难以成器的病因所在。现代讽刺文学与幽默文学的不同发展情状正是现代社会更多地提供了”为严正的滑稽“的气候的结果。
尽管在重重约束之下,老舍的幽默创作仍然顽强地发展与完善着自己,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幽默文学的代表。检点现代幽默文学史,真正具备底蕴——深刻的哲学心境,浓烈的同情倾向,以及合宜的与入木三分的表现——的幽默作品为数不多,老舍山东时期的《离婚》、《骆驼祥子》因之就格外突出。现代文学史上最可一论的幽默作家还有以文学创作为余事的钱钟书。他的《围城》对人生之荒谬圈套的把捉更是以深不可测的绝望为内核的;他的幽默论(《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对“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致使“幽默品格降低”的指责,是对“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的不以为意也是对真幽默之稀见难觅的一声黯然轻叹。
新时期北京作家群自觉追步老舍,语言的刻意模仿与文化态度的趋同明显多过幽默的习染,这主要是因为幽默更多地依赖于创作主体的个性秉赋。尽管如此,老舍的幽默仍然因为这些作家在新时代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再现。这也是30年代老舍在幽默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的又一表征。所谓“京味作家群”前后,还有王蒙逞才的幽默与王朔带“痞气”的幽默堪称独树一帜。而无论是王朔、陈建功还是王蒙,这些作家的幽默都有过于辞气浮露的缺陷。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多作出一副冷漠于价值关怀、拒绝读者的姿态,在远离固有创作观念的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远离了幽默。倒是作为新文学传统赓续的“严正的幽默”在少数作家的笔下还在焕发出亮色,但一般都是作为副笔。应当说,新时期以来真正以幽默为追求并有作品作支撑的成熟作家尚未出现。特殊的国情与现代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印证了周氏兄弟的先见,幽默文学的始终得不到自如舒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老舍的幽默秉赋在时代的厚障壁前一再受挫也早成过眼烟云,但愿下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能卸去那沉重得不堪舁举的历史宿命和人为约束,催生出真正的健康明朗的幽默文学来。
《文汇报》
老舍住过的地方
顶小顶小的小羊圈
进入80年代以后,小羊圈胡同突然变得赫赫有名了。恐怕总有数以亿计的人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是小羊圈的老居民们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就凭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今,小羊圈改叫小杨家胡同了。它的西口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上。单看外表,小杨家胡同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它是那么狭小、简陋,以至从它前面路过时,稍不注意,就会忽略它。小杨家胡同真是小,入口处只有一米多宽,除了自行车,别的车辆大概永远不用打算进去。胡同小还不算,它还不直,进了胡同走二十几步就碰墙,连着拐几个九十度的硬弯之后,才能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马蜂腰,细而直地往北伸去。到了最北头有一个更大的葫芦肚儿,它的东面便是有名的护国寺的西廊之下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那时,隔不久,小空场的两棵大槐树下,就有一次集市,集市一过相当安静。夏天,槐树上垂丝而下的绿槐虫在微风中打着秋千,偶尔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