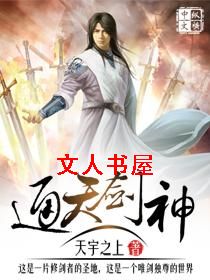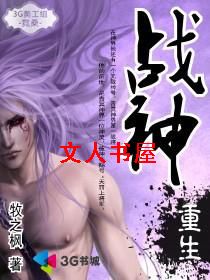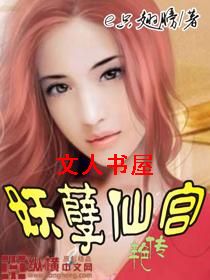藏獒的精神-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的作家有五种分类,即名作家、作家、大作家、大师、精神导师。五种分类产生了五种境界、五种精神现象,其表述如下:
精神导师——救世姿态、信仰写作、舍己之心、无人之境
大师——创世姿态、理想写作、利他之心、自如之境
大作家——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
作家——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
名作家——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
这个表述应该从下往上读,它是一个金字塔,名作家(名为作家者)在最底层,不计其数;精神导师在最高端,凤毛麟角。
“救世姿态”、“创世姿态”、“醒世姿态”、“愤世姿态”、“入世姿态”,指的是行事原则和写作姿态。
“信仰写作”、“理想写作”、“理性写作”、“感性写作”、“才情写作”,指的是精神现象和思想层次。
“舍己之心”、“利他之心”、“悲悯之心”、“怨望之心”、“名利之心”,指的是心体表现和主体意识。
“无人之境”、“自如之境”、“风格之境”、“性情之境”、“雷同之境”,指的是文本境界和叙述特点。
作家的五种分类和五种境界让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境界是精神的,层次是心灵的,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著作等身,说不定也仅仅是一个“名作家”(名为作家者);有些人一生只写了一本书,说不定就已经是“大师”或“精神导师”。在这个金字塔上,有些作家是从下往上走,有些作家是从上往下走,有些作家是忽上忽下地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品是作家行事原则、写作姿态、精神现象、思想层次、心体表现、主体意识、文本境界、叙述特点的综合体现。作家面对的主要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一种外在的生活,而是自己的心灵。心灵的优劣决定了作品的优劣,心灵的内涵决定了作品的内涵,作品是心灵闪光的显现和物化,而不是生活本身。任何生活都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和提炼,对生活的选择和提炼往往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对作家而言,和自己作战远远超过了和外部世界作战。
而对读者来说,你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作家按此五种境界排序,并把它看成是一生阅读的一条便捷之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的需要做出选择。你若是仅仅需要没有思想坚守的才情滋养,就没有必要阅读“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比如但丁的作品、歌德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它们会让你不忍卒读,因为你的心灵不需要它们的指引。相反,如果你要的是补缺心灵、圆满精神,就完全可以忽略别的,而直取“精神导师”和“大师”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作家有五种境界,读者也有五种境界。一个作家的作品,只会在相同境界的读者里生根、流传。
同样,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不同境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你如果是一个仅具有“入世姿态”或“愤世姿态”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就无法理解具有“救世姿态”的精神导师和具有“创世姿态”的大师,更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价;你如果已经具备了“救世姿态”或“创世姿态”,也不可能只热衷于评价具有“愤世姿态”的作家和具有“入世姿态”的名作家。总之,你具备什么,才会正确评价什么,你不具备什么,就很容易忽略什么。作家有五种境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有五种境界。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只体现一种境界,但有时候也可能例外,它会成为多种境界的综合体,甚至把精神导师的救世姿态、大师的创世姿态,大作家的醒世姿态、作家的愤世姿态、名作家的入世姿态全部吸纳在一部作品中,比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中国当代作家百分之八十五处在“名作家”这个境界,即入世姿态、才情写作、名利之心、雷同之境;百分之十处在“作家”这个境界,即愤世姿态、感性写作、怨望之心、性情之境;百分之五处在“大作家”这个境界,即醒世姿态、理性写作、悲悯之心、风格之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作家争名利,争地位,却不争姿态,不争境界,懵懵懂懂一路写下去,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几层。我们还没有“大师”,更没有“精神导师”,因为并不是你想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就可以做“大师”和“精神导师”,大师和精神导师必须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他们会为了“创世”和“救世”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会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托付给“理想”和“信仰”,而成为人类精神暗夜里的灯塔。
我这样说肯定会有人诘问我:你杨志军也是写小说的,你说你属于哪一种境界?我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个阅读人,我对五种作家五种境界的划分依赖于我作为一个阅读人的立场,我和许多阅读人一样,得到过作家作品的精神引领,我期望这样的引领伴随我的一生乃至人类的世世代代。至于身为作家的我,如果不得不对号入座,那我也就是“名为作家”而已。略有不同的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写作者,我的原则是:“平凡的姿态、平淡的对待、平和的往来、平静的存在。”我更愿意在一种“非作家”的氛围里从事写作,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内心的需要,是不断袭击我的表达欲望的满足,就像面对一个刻骨铭心、日思夜想的爱人不得不袒胸露怀那样。这样一来,似乎又有了第六种作家,第六种“作家”算不算作家?算与不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总结:出世姿态、入世写作、无求之心、空了之境。总结其实也是期许,现在没做到的,以后我会做到。
藏獒从荒原走来
一
当“网谈”无意中把“知识分子”变成“知识藏獒”的时候,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就成了那只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藏獒”。然而时刻纠缠着我的自省告诉我,我不是。有时候“网谈”和“妄谈”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们的心灵就在网谈抑或妄谈中裸露了真实,一步步靠近了真理。所以我不是,不是那只代表真理的藏獒。
人生犹如一次无法预知前途的旅行,那些供人栖息的驿站不知道停靠在哪里。我一直在青藏高原行走,突然有一天漂泊到了黄海之滨,这其中漫长曲折的经历已内化为我心灵的强硬支撑,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轻易触动我了。然而,2004年的秋天,这个黄叶满地的季节却让我在看到驿站的同时有了一次小小的惊讶,而且这个惊讶越滚越大,最后像滚雪球一样延续到了2005年的秋天。
惊讶源自于青岛新闻网大漠的帖子《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这篇发自2004年1月底的帖子从对个人和文本的解读出发,以我的写作状态作为契机,最终走向了对城市文化的质疑。这个结果对作为楼主的大漠来说也许始料未及,对于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当网上的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尚定定地坐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写作,纵使外面雷电交加我亦全然不觉。10月初,大漠通知我要在青岛新闻网与网友进行一次网谈,我用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全部的网帖,内心的震动也可用“雷电交加”来形容。
这是一次颇有意味的集体话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满怀热情,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传达出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和期待,对此,我充满敬意。我的写作生涯已逾历二十余年,此中的风霜雪雨抑或阳光灿烂都不足与外人道,唯有内心的信持历久弥坚,常常引发一些滔滔不绝的文字洪流。由此,大漠的命题便拨雾而出: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一种写作姿态的坚守是否要以作家的困境作为代价,换言之,作家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传统的话题,但在今天被重新提出却有其尖锐的背景与话语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此帖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持久而深刻的文化讨论。
我以为,这是一次超越了作家个人困境层面的众声喧哗,我作为一个被置评的对象,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个舞台的背景,所有发言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舞台中央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此拓展和延伸大漠的命题。我很满意我所在的位置,也很愿意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靶子,为网友提供操练的机会。这是大家给我的荣幸,它使我不是高挂于上下无着的半空,而是成为众声中的一种声音。多种声音的汇聚形成了一种景观,一种罕有的人文景观,我能够感觉到大漠理想的“场”的存在,尽管脆弱了点,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个确乎其然的事实。由对一个作家困境的关注,进而讨论到作家精神的出处以及作家群体的现实处境,再到一个城市文化的建构,相信每个人的声音都充满了真诚的焦灼与关怀。这是每一个思考着的人对一座城市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良知和责任。“最初”意味着最基本的关怀目光,它不包含有任何杂质,是对自己生存的城市直接单纯的情感抚摸;而“最后”则是艰难持守的道德底线,它最终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也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方位,这恐怕才是此次网帖的意义所在。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生命,而是一个众目睽睽的符号,符号所引发的人们对城市文化激烈而深刻的探讨,是大家的收获,也是城市的收获。
在网谈的时候,很多网友的问题都聚焦在了青岛文化,这也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从青藏高原的荒原背景突兀地出现在青岛的蓝天碧海,我应该是这个城市旁逸斜出的一枝虬干。文化视角的转换有个艰难的过程,走近这座城市的文化并能浑然其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对高海拔的荒原寄予太多理想的作家,在这座零海拔的城市里,我更像是一个茫然无措的探路者。也正是这样的探路,让我逐渐明晰了青岛的文化脉络,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