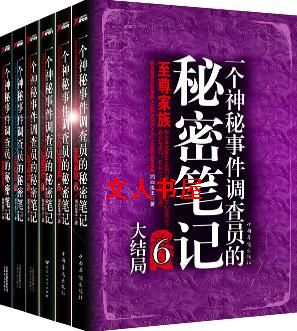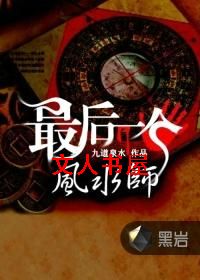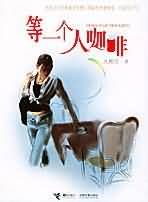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次大战枪炮响起,欧亚死伤数千万人。此时的布洛克放下学术工作,以53岁高龄,等于我现在的年纪,投入前线作战。法国战败前夕,他一方面含泪写下《不可思议之溃败》,一方面相问他的同胞,“历史是不是出卖了我们?”布洛克既是反纳粹的著名史学家又是犹太人,他有一切的理由离开法国;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我28岁第一次阅读布洛克作品与人生时,即惊惧于他的执著与勇敢。我身边的美国朋友迷恋的偶像总是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窝蜂的,像今日陶醉Lady Gaga。我从年轻起始心目中的偶像,至今仍是布洛克。1943年德军南下控制全法,布洛克选择加入地下反抗军;一个53岁的国际史学家,多么不可思议!1944年春天布洛克被捕,狱中他受尽酷刑;6月盟军已登陆诺曼底,但一代史学家等不到纳粹全然溃决,1944年6月16日布洛克在里昂被枪决。临刑前站在布洛克身旁,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颤抖着,低声问他“会痛吗?”布洛克伸出手,揽着他的肩膀,轻声地说:“不会的,一点也不痛。”
我在美国新社会学院研究所(New School)读书时,老师几乎都是欧洲年鉴学派,也多是犹太人。说起布洛克的故事,没有人只在上课,也没有人仅仅是在授课。布洛克与死前彷徨的16岁青年对话,好似站在我们的眼前。错觉之间,我们也亲临了刑场,听闻那一段低声的最后道别。“会痛吗?”“不会的,一点也不痛。”
当天上完课,依例搭地铁回布鲁克林的家。地铁列车一站一站停留,像历史的短暂定格,然后载着乘客前往知名或不知名的下一站。每一次停留,都只是片刻;每一个启动,都是新的抛弃。列车速度把纽约地下铁道满墙的涂鸦变成了动画,它动了,于是最夸张、最残暴的图样以飞快的速度在我的眼前演出,但还来不及辨识,刹那间我又已失去了它们。
地铁,重回黑暗。
历史不是有什么用,而是它总出其不意地来,然后无声无息窒息般地笼罩着你;历史是一个永不断绝的复制品。我在新社会学院求学时阅读布洛克那一代历经的经济大恐慌历史,文人小说下载以为只是进入了60年前的往事;从来没有想到那些数字的点点滴滴,在2008年之后,再度成了我必须熟背的经济史。大萧条对世界深远的影响,其实远比一次大战伤还大,还深。1929年10月29日大崩盘的经济激变,等同资本世界的全面解体。全球每一块土地,工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小国,丝袜供应地,咖啡、棉花、白糖、橡胶、蚕丝种植国,皆一败涂地。大萧条在历史怎么开始的,知道的人多;怎么结束的,知道的人少。它共持续了整整13年,并于1937年看似复苏八年后,二度衰退。这是今日2011年6月全球经济关切的焦点,我们是否又活回1937年魅影下?全球是否二次探底?
大萧条13年期间,除了1937年后引爆二次大战外,一切皆与今日像极了。全球牢牢地被掌握于恶性循环的“完美风暴”中。任何一个环节经济指数出现滑落,其他指数便跟着走向恶化。大萧条最严重时期(1929~1933),英国、比利时失业人口约为22%与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德国高达44%。于是纳粹主义在如此可怕的经济灾难中崛起,使希特勒从一个《我的奋斗》畅销作家,跃升为第二大党党主席,再一步步接掌德国政局。伦敦《泰晤士报》1930年写下社论,“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的恶疾。”《泰晤士报》没有料及的是:失业,本身就会带来战争。
在1930至1931两年间,欧洲12国政权改朝换代,激进右派全面崛起。而当年的拉丁美洲,则演出今日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戏剧性政变。各南美国家财政皆破产,阿根廷进入军政府时期;智利推翻独裁总统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民粹领袖瓦加斯上台。
大萧条的发动者美国当时工业生产量已高占全球42%,英法德三大国总加不过只占区区28%。美国一倒,短短数月,世界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皆掀起政治大波澜;其中最可怕的是法西斯路线变成世界性的运动。人类在经济绝望之际,竟走上拥抱毁灭、种族仇恨的恶行;史学家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只能哑然无语。历史,在那个当下,成了一个无法言语的哑口。
这或许是布洛克53岁还上战场的原因吧!一个史学家衷心信赖的人类文明,全然崩解。笔,已解决不了他的痛;他必需上战场,搏上一天又一天的性命,换回“史家的技艺”。当自由文明已解体,历史,有什么用处呢?
书写悼念布洛克,正值他逝亡67周年(1944年6月16日)。他枪决前的声音仿佛又出现我的耳边,“不痛,别怕。”在诺曼底的一个花园里,他死前四年曾思索一个问题“难道历史已出卖了我们?”历史证明当时的大浩劫及苦难,孕育了后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伯南克、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英国前首相布朗……在79年后类似的大萧条,历史告诉了他们些许答案;也使欧洲极右势力虽仍崛起,但再也没有疯狂的纳粹,再也没有东方日本军国主义。
历史并未全然出卖了我们。
2011年6月13日
一个废墟,两个中国
历史如戏。往往一座宽宽窄窄的舞台,就道尽历代世纪沧桑,留下无尽世间悲剧。可惜我们只会看戏,不会看历史,我们的人生太短,历史却太长,我们或任何当代之人始终学不会以历史的纵深,观当下,或预知未来;也因此始终分不清许多事件在历史中的意义。
唯一的例外,是现代中国的领导精英。
2011年1月20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天。这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GDP数据,初步测算中国GDP总值397983亿元人民币,合6万多亿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1895年甲午战败后,这是史上第一次,中国人超越了日本。115年的历史巨轮,在中日关系上,代表太多屈辱、屠杀、毁灭、战争、家破人亡……各种类型符号至今未歇。按理说,中国官方至少应在南京,或哪个长城关口放点烟火;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反应,却异常冷静谨慎。官方声明大意如下:
一、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这只是量的总和,中国的高GDP是靠高耗能、低工资换取而来;无论国家的生态、民工的血汗都为此付出惊人的代价;因此量上中国超越了日本,值方面比不上,中国经济结构仍有待提升;
三、中国人口高达13亿以上,以GDP总量固是世界第二大,但以人均GDP换算只有4000多美元,全球百名都排不上。
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此数据之日,也正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最后一天。尽管奥巴马以G2最高国宴款待,胡锦涛仍绝口不提中国今日之成就。无论国内或国外不约而同,唱的都是同一出低调之戏。许多人不了解中国领导者的心态,是的,中国正在崛起,但它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大国正面冲突,几代领导人深记邓小平遗训;中国要崛起,就不能与任何大国正面冲突,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必须记住保持一件事:低调。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执旗的士兵挥起国旗,踩的是169个步伐。这一年的中国,是从鸦片战争那一年算起的;这一刻的北京天安门,牢牢记住我们离海淀圆明园废墟,不过几十公里远。
另一个呈现中国历史态度的是关于圆明园遗址的决策。2005年北京翻天覆地拆迁老胡同、旧民房,兴建鸟巢、水立方之时,该不该重建圆明园,又成了巨大的辩论。最终北京市政府决定维持2000年已定的方案,这里将作为中国人永久国耻印记的“遗址公园”,这一片面积458。9公顷的旧物,要让世代中国人永久凭吊,谨记19至20世纪,被列强烧杀抢奸的中国。
中国领导人要人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废墟;它是一部独特的纪录片;一出最苍凉的戏;也是一面最重要的镜子。
在北京我常遇着两种发迹的人,一种是忘了镜子的人,金表名车十足炫耀,首善行善送钱都得红花花纸钞摆在舞台,或直升机上涂个自己的名字,唯恐人不知;另一种,譬如潘石屹,他常常睡觉初醒还没全回神,第一个反应竟是害怕没饭吃,下一分钟清醒些才想起“哦,我现在已是个百亿富翁了。”他用一个可爱的比喻和我聊天,他的灵魂有一半仍住着穷鬼,另一半才是今日发财的他。来台湾第一次,跟着大陆访问团,结果机场挤了百名记者,灯光闪闪,吓得他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没法清楚回答,就打笑地说,“你现在享受的是章子怡的待遇”。他从此明白“章子怡”日子不好过。第二回在台湾见朋友,低调搭着小黄出租车四处见风景。他写的自传书籍《童年的糖是甜的》,对年幼时的苦从不忘怀;至今的他仍常回甘肃天水家乡,据说专事帮忙当地学校修厕所,“管屁股”;因为当地卫生条件太差了,许多女童不到十二三岁,染病被迫割除了子宫。一个不能生育的中国乡下女子,等于不能买卖或生产的牛羊,家人往往就把她们给放弃了;潘石屹想帮助这些女孩,至少有条件当个健康的妈妈。
当代中国面对历史与美国有着重大差异。他们不像犹太人至今仍四处追捕纳粹战犯,也不想提父亲及自己年幼时期的文革迫害。四人帮已死,清朝也覆灭了。算账,不能找回中国的公道;中国的公道得在历史、在废墟中靠自己重建。
西方近日一本极为畅销的书籍《当中国统治世界》,开篇不断地提醒西方读者,中国真正殒落是1830年以后的事;在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全球GDP产值最高的国家,明末之前全球只有中国人能生产精美的硬瓷、无与伦比的丝织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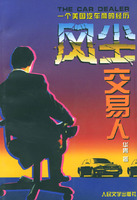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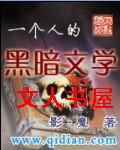
![[网游]暗恋一个傻瓜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1/11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