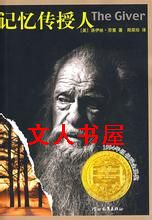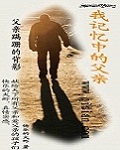记忆碎片-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弄得自己都怀疑自己,那种发自自我本真状态的感动和感悟在哪儿?
不好意思,《红楼梦》就这样也被我弄伤了。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读书的最悲惨境界。
“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我居然很珍惜,等到读过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说:‘去你的’。”(6)
谨以这句话,献给我下面说到的这些书。其实不是它们惹的祸,只恨我把阅读的顺序弄错,在原著之前,看了这些品评原著的著作。——仅有读书的欲望还是不够的,还要抗拒那些不该读或不该先读的书。
《红楼梦学刊》,那是在1986年,市图书馆要卖掉一批存货。我和同学巴巴地赶过去,在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性价比之后,我用四元钱买了十二本《红楼梦学刊》,这是季刊,共计三年的。为了对得起那四元钱,我将这些书基本上全都看了。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呢。
《外国文学名著题解》(上下两册,共两元九角)、《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一元五角),这两套书均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库”系列,将中外名著言简意赅地一网打尽。这两套书我看得都很仔细,使得别人提到任何名著我都宛如看过的样子,学问大得很。但我看得太认真了,认真到渗入我的记忆中,使得我以后有机会读到原著的时候,都像在吃别人嚼过的粮食一样。
《语文报》,这份报纸由位于我曾经军训过的山西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主办,当年可是所有中学生的必备读物。记得里面有一个专栏叫“文学形象画廊”,介绍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语言有趣,配以生动插图,所以很受欢迎,连载了许多期。通过这个专栏,我知道了葛朗台是吝啬鬼,奥勃洛摩夫是大懒汉,别里科夫是套中人。是啊,理解得多透彻。按照这个专栏的说法,哈姆雷特是优柔寡断无病呻吟的典型。但有一年,我沉浸在莎士比亚的原著中不能自拔,再看哈姆雷特,对他的犹疑和挣扎充满了同情和敬意。一个人,承担着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做着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连放弃的权利都没有,真的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快活”(杨过在离别之际对小龙女这么说),有什么可奇怪可指摘的呢?不禁怀疑那个专栏的说法:葛朗台真的是吝啬鬼吗?奥勃洛摩夫为什么选择像一摊泥一样的生活而懒得跟这世界较劲?别里科夫自己就愿意当套中人吗?
终点又回到起点,发现自己已投入到另外一个陌生。
不学有术
大学毕业以后,我有机会与一些饱读诗书的人为友,经常要谈到各自读过的书来佐证自己的品味,或引用读过的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看他们纵横摆阖手到擒来的样子,我经常陷入有劲无处使的境地,脑子里空空如也,想掏出点什么来,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半空里跳一样徒劳。
无奈之余,我就报以高深莫测的微笑:“我最喜欢的读书境界是,把自己看过的书忘得
爪干毛净,白茫茫一片脑海真干净,就像‘太极初传柔克刚’里的张无忌,努力忘掉,能记得半点儿东西都不行——俺们姓张的人就是这么智慧。我正在试图忘掉自己脑中的壁垒,而你们……切!”(7)
“此话倒也有理。”那些满脑门学问的人微微颔首。
我却打心眼里发出一声哀鸣。人家张无忌是肚里先塞进东西再执行忘记程序,而我却是,想忘都无从忘起。
但他们还是被蒙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并没有高傲地将我排斥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而我另一些不懂得随机应变的朋友就没有这么运气和这种待遇了,而是被他们轻蔑地斥为“俗人”。除了吃饱饭需要人结帐、被人欺负需要人助拳、老丈人来视察需要人开车去机场接送外,再也想不起搭理人家。
但我还是认为,不学无术的人,并不比学而无术的人更低级。
大学四年,我基本上过的是不学无术的生活。首先,我考上的就是个不需要太多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天,这在当年可是个时髦字眼)的专业,所以学校安排的专业课和必修课都是能逃则逃。有一年期末的晚上,我正躺在宿舍里怀疑人生,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温和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见到我,迟疑地问:“这是新闻系的宿舍吗?”
我忙点头:“是啊,您找谁?”
“我是你们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老师,来给你们做考前辅导。”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8)。
我突然想起《鹿鼎记》中的一段话:“韦小宝的脸皮之厚,在康熙年间也算得是数一数二,但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居然也不禁为之一红”。
不上课,图书馆总该去吧?但说实话,图书馆对于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男生来说,吸引力实在是不大。我们宿舍老三去图书馆是最勤的,我相信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绝不是自己刻苦攻读的情景,而是一个个女孩从他身边掠过,暗香浮动,裙裾飘飘,他的嘴张得像一张影碟,舌头恰恰伸出一点,就像影碟中央的那个小眼,并幻想着自己在书香世界里的浪漫邂逅。幸亏他大学期间一直没有恋爱成功,才得以保持我们宿舍上图书馆最勤最久的纪录。
图书馆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那种汗牛充栋的绝望感,所以宁愿躲在宿舍里看自己手头仅有的那五六本书。
一次期末考试,突然想起,借的书要再不还到图书馆,就要拖到下学期,就要被扣证了。于是在两门考试的间隙急匆匆来到图书馆,结果被管理员拦住,说不能穿拖鞋进去,这是规定。
不让穿拖鞋?那就不穿呗。我憨直的脑子根本没有多想,马上就把脚丫从拖鞋中脱出,光着脚跑进去。管理员也似乎觉得我这样做得很对,还在馆门口帮那双老鞋子放哨,直到我下来,也没说什么。
人在情急之下产生的逻辑真的是很奇妙。《野鹅敢死队》中也有这样一幕,敢死队员们被困在非洲,瑞弗上尉说要想办法出去。肖恩中尉一声冷笑:“切!难道你要我们走出非洲吗?”
“那你就跑吧。”瑞弗马上回答道。
工作后先住单身宿舍,室友毕业于兰州大学,非常勤学。他说起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的逸事,经常会借到好些年没人动过的书。有一本书借书卡的上一个名字是顾颉刚(9),令他唏嘘良久。
按照推断,顾颉刚建国前在兰州大学执教期间借阅过的书,时隔半个世纪,才被另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中抚摩,盯着借书卡上那个名字发愣。这一情景要让余秋雨老师知道,肯定能写出一篇很人文主义、很“大文化”的佳文。
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尚在学校就读的弟弟妹妹们,看看你们手中的书,有没有先哲的体温和指纹?
图书馆里有许多书,就像野百合一样没有经历过春天,借书卡上永远是一片空白,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枯黄。但也有些书,就像春色无边的艳妇,五陵年少争缠头,秋月春风等闲度(10)。记忆中最抢手的,就是金庸的书了。每一本都被翻得破破烂烂的,连收垃圾的都不愿意要。
那年头的学校是很人道的,配备了许多套金庸来满足大家,但依然是狼多肉少,于是,一些有创业头脑的同学便集资大量购进畅销图书,做起了租书的买卖。为了追求高利润,他们还进行高投资、高风险的租书事业,比如斥巨资购进号称“足本”的港版《金瓶梅》等。这些历练对年轻的老板们很有好处,走向社会后他们中许多人当了书商,凭借对图书市场的准确判断,使其迅速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哦,如今他们又玩起了房地产和期货,再不济也玩起了小姐或二奶。
集腋成裘,老是花钱租书看,经济上也承受不起,好在此时贫富不均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显现。对门宿舍有头猪不知道为什么特有钱,能买许多闲书,金庸之外还有许多,都是图书馆里没有的好货色。我们就忍着他的恶声恶相,卑下地借来看之。
这同学是安徽蒙城人,后来我心目中的文化界一大公害牛群先生(另一公害是张俊以老师)要去蒙城祸害一方,说是扶贫。我深表怀疑,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富得流油,上学时就买得起温瑞安大薮春彦(11)之类。
对了,还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本令我感到严重挫折和奇耻大辱的书。
前面提到的《青春诗历》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必须通过邮购才能买到。我高三和大一各买一年,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疯狂崇拜上了有诗作收录其中的我校女教师杨榴红,得到的附加好处是经常收到该社的邮购目录。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份书目都值得精读并憧憬好几遍的。
我们宿舍老二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研究了一番书目后,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汇去四十元钱,求购十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半月后,图书到货,他给自己留下一本,然后去各宿舍游走,一层楼都没走完,就将其余九本以每本八元的价格售出,净赚三十六元——足够过很阔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二的这一举动令我艳羡不已,把自己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个遍,凑够八十元钱,也给汇出去,求购二十本。按照我的商业计划书,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给卖出去,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比老二节省,或者,黑黑心一本卖十块,就可以赚一百二了……这一蓝图令我开始设计自己的大款生活细节,经常得折腾到黎明才能入睡——自从一次成功的失恋后,我再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已经停止发行——没有言说的原因是被有关部门禁止了,那一拨还有《玫瑰梦》等共四本。天可怜见,他们的信用等级还算较好,把本钱给我退了回来。跟风发财的一枕黄粱破灭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话: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这么说的就是庸才。
《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和穆念慈的爱情与郭靖和黄蓉俨然形成两条平行主线,双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