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股东荣瑞馨也不站在同族这边。他在橡皮风潮中损失惨重,还未缓过来,债主接二连三上门,让他思忖生财之路。由于丢了买办职务,荣瑞馨急需用钱,于是产生了独揽振新大权的念头。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荣瑞馨出面邀请荣氏兄弟掌管振新,如今,他又开始寻找借口罢黜两人。并且,他很快找到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荣瑞馨认为时机成熟,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在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地价固然便宜,荣氏却不愿亲自建造厂房,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产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占地24亩,被分成两块,一部分被租用来做织呢厂,另一部分是轧油厂,可惜两家工厂经营都不好,有意撤出。
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产地。荣氏兄弟详细考察,认为该地块物超所值,厂房、机械等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建筑物也比较牢固,于是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这些人大多是荣氏老部下,对兄弟二人有信心。他们集资30万(实到21万,其余9万陆续补足),荣氏根据每位股东能力,为其安排特定职务,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力求节俭、杜绝浪费、精诚建厂。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此外,为保证股权结构稳定,股东股份只能在内部流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给其他人”。
辩证地看,管理者缺乏约束,容易独断专行,但结合当时实情,却能有效避开繁琐的讨论程序,当机立断,不至于错过市场机遇。而且,以荣氏能力,大可赢得股东信任。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申新纱厂成就“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恒昌源原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1907年建造的九成纱厂,曾名日信纱厂,1916年终止营业,被祝兰舫买下,更名恒昌源。祝兰舫财大气粗,但经营能力一般,纱厂在他手里并未摆脱窘境,于是挂牌沽售。
因自己是茂新股东,祝兰舫自然乐于卖给荣氏兄弟。但考察完这座占地27亩的纺织厂后,荣德生心生退意,他认为“仅地好无益,制造尚不如地偏而机新,立时可造,自成一局,在锡为佳”。而荣宗敬观点相反,认为厂址位置优越,从长远计,日后必有发展便利。最后,荣宗敬说服荣德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不料,振新纱厂老板荣瑞馨横加阻挠。
荣瑞馨与荣氏兄弟虽有不快,但并无深仇大恨,此番阻挠,是害怕申新三厂抢走了自家生意。荣瑞馨对荣氏兄弟的经营能力心知肚明,申新纱厂生意红火,若在振新旁建厂,岂不是公然竞争?于是,荣瑞馨召集一帮农民,在申新厂地建造五洞桥,令建厂无法进行。无奈之下,荣德生疏通关系,让官方出面下令禁止,名正言顺地筹建申新三厂,荣瑞馨只得作罢。
此地块横跨无锡梁清溪河,东岸规划为生产区,建造纱厂、布厂,西岸作为办公区及生活区,建造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部门,两岸以桥相通。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申新各厂新创品牌,如“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等。荣德生要求甚高,尽管每个品牌各有特色,但从用花、拼花、用料上,丝毫不大意。荣德生为申新三厂“好做”牌亲自配料,保证品质,“好做”刚一面世即受到市场追捧,迅速取代“人钟”,成为申新王牌产品。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19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三新财团”一定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词汇。作为荣氏兄弟数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统称,“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分别占据全国面粉、棉纱产能的1/4和2/7。
然而,随着事业壮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在眼前,即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工厂。
事实上,在增建工厂过程中,荣宗敬和荣德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在1919年前后达成共识: 成立一个总领机构,对“三新系统”进行统一管理,集中调拨、互通有无,以图发展。
1921年,上海江西路耸立起一座英国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总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厦”。作为荣氏“大本营”,这幢耗资35万元、占地2。8亩的办公大楼高三层,楼顶插公司旗帜,风光气派,在当时,恐怕只有“状元企业家”张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厦可与之比肩。
三新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采购、供应、销售、资金和人事进行统一管理。各厂经理每日中午到总公司开会,报告生产经营状况,领取指令,然后分头行动,通过电报、电话将指令传至上海、无锡、济南的工厂。从规模和做派上讲,颇具现代企业风范。
毫无疑问,荣宗敬担任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下设两个职能部门,一个是专营进、出货的外账房,另一个是负责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的银账房。此外,更下一级设有庶务、文书、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等8个部门,各部设主任、副主任及办事人员和实习生若干。
三新总公司犹如一台精明机器,数百号人马围绕它运转不停,荣宗敬处于绝对核心。在三新大厦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室,这个年届50的商人端坐中央,各厂经理分列左右,轮流汇报生产经营情况。荣宗敬发号施令,俨然企业“教父”,也曾难掩意气地说: “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不容忽视的是,三新总公司本身并无多少资本,只是代各厂筹措、管理资金。各厂独立预算,多余资本存放总公司,存款利息高于钱庄、银行。总公司开展存贷款、投资业务,实现资金盈虚调度。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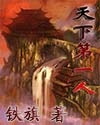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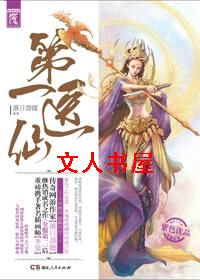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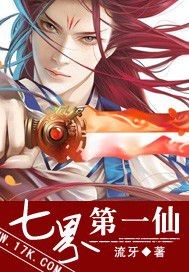
![[主家教]史上第一校花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3/30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