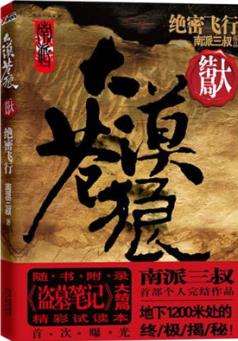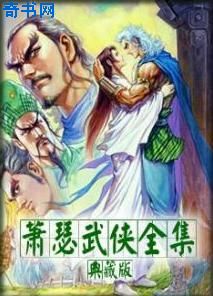大漠谣-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子?跟我来!”
我还没来得及出声反对,他已经强拽着我跳上马车,我的力气都已在刚才用完,此时只觉一切都无所谓,默默地任由他安置我。
他见我一声不吭,也沉默地坐着,只听到车轱辘轧着地面“吱扭”的声音。
半晌后,他道:“我知道你吹的是什么曲子了,我随口哼了几句被陛下无意听见,打趣地问我哪个女子向我唱了《越人歌》,我还稀里糊涂地问陛下:‘为什么不能是男子唱的?’”
我向他扯了扯嘴角,勉强挤了一丝笑。
“楚越相近,但言语不通,楚国鄂君乘舟经过越国,河上划舟的越女见之倾心,奈何语言不能说,遂唱了这首歌。鄂君听懂了曲意,明白了越女的心意,笑着把她带回家。”霍去病娓娓讲述着这段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故事。
因为美丽的相遇与结局,也许很多女子都会效仿越女,试图抓住自己的幸福,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偿心愿。我不愿再听这个故事,打断他的话:“你要带我去哪里?”
他静静地盯了我一会儿,忽地一个灿如朝阳的笑容:“带你去听听男儿的歌声。”
霍去病竟然带着我长驱直入建章营骑的军营。当今皇帝刘彻登基之初,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出身良家的少年护卫建章宫,称建章营骑。当时朝政还把持在窦太后手中,刘彻虽有扫荡匈奴之志,但在连性命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只能做起了沉溺于逸乐的纨绔少年,常命建章营骑分成两队,扮作匈奴和大汉相互厮杀操练,看似一帮少年的游戏取乐,却正是这支游戏队伍,经过刘彻多年的苦心经营,变成大汉朝军队的精锐所在。
虽然是过年,可军营内仍旧一片肃杀之气,直到转到休息的营房才有了几分新年的气象。门大开着,巨大的膏烛照得屋子透亮,炭火烧得通红,上面正烤着肉,酒肉的香气混在一起,惹得人食指大动。
霍去病自小出入军营,屋内围炉而坐的众人显然和他极是熟稔,看到霍去病都笑着站起来。一个锦衣男子笑道:“鼻子倒是好,新鲜的鹿肉刚烤好,你就来了。”我闻声望去,认出是李敢。
霍去病没有答话,带着我径直坐到了众人让出的位置上,大家看到我都没有任何奇怪的神色,仿佛我来得天经地义,或者该说任何事情发生在霍去病身上都很正常。一个少年在我和霍去病面前各摆了一个碗,二话不说,哗哗地倒满酒。
霍去病也是一言不发,端起酒向众人敬了一下,仰起脖子就灌下去。大家笑起来,李敢笑道:“你倒是不啰唆,知道晚了就要罚酒。”说着又给他斟了一碗,霍去病转眼间已经喝下三碗酒。
众人目光看向我,在炭火映照下,大家的脸上都泛着健康的红色,眼睛是年轻纯净、坦然热烈的,如火般燃烧着,不知道是炭火,还是他们的眼睛。我竟觉得自己的心一热,深吸了口气,笑着端起碗,学着霍去病的样子向众人敬了下,闭着眼睛,一口气灌下去。
一碗酒下肚,众人鼓掌大笑,轰然叫好。我抹了把嘴角的酒渍,把碗放在案上。第二碗酒注满,我刚要伸手拿,霍去病端起来,淡淡道:“她是我带来的人,剩下两碗算我头上。”说着已经喝起来。
李敢看着我,含笑道:“看她的样子不像会喝酒,竟肯舍命陪君子,拼却醉红颜,难得!在下李敢。”说着向我一抱拳,我怔了一瞬后,方沉默地向他一欠身子。
李敢和霍去病的关系显然很不错。霍去病在众人面前时很少说话,常常都是一脸倨傲冷漠,一般人不愿轻易自找没趣,也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可李敢与霍去病一暖一冷,倒是相处得怡然自得。
李敢又给霍去病倒满一碗酒,也给自己满上,陪着霍去病饮了一碗。又用尖刀划了鹿肉,放在我和霍去病面前,霍去病用刀扎了一块肉,递给我,低声道:“吃些肉压一下酒气。”
其他人此时已经或坐或站,撕着鹿肉吃起来,有的直接用手扯下就吃,有的文雅点儿,用刀划着吃,还有忙着划拳的,吆五喝六,吆喝声大得直欲把人耳朵震破。
我的酒气开始上头,眼睛花了起来,只知道霍去病递给我一块肉,我就吃一块,直接用手抓着送到嘴里,随手把油腻擦在他的大氅上。
醉眼蒙昽中,似乎听到这些少年男儿敲着几案高歌,我也扯着喉咙跟着他们喊:
日月光,河山壮
狼烟阵阵起边疆
血肉躯,英雄胆
将士铸成铁铜墙
铁弓冷,血犹热
奋勇杀敌保家乡
好男儿,莫退让
马踏匈奴汉风扬
汉风扬……
大喊大叫中,我心中的悲伤愁苦似乎随着喊叫从心中发泄出少许,我也第一次约略明白了几分少年男儿的豪情壮志、激昂热血。
第二日早上,我呻吟着醒来。红姑端着一碗醒酒汤,嘀咕道:“往日不喜饮酒的人,一喝却喝成这个样子。”
我捧着自己的脑袋,还是觉得重如千斤。红姑摇摇头,拿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我喝了几口后问:“我是怎么回来的?”
红姑嘴边带着一丝古怪的笑,娇媚地睨着我:“醉得和摊烂泥一样,能怎么回来?霍少送到门口,我想叫人背你回屋,霍少却直接抱着你进了屋子。”
我“啊”了一声,头越发重起来。红姑满脸幸灾乐祸:“还有更让你头疼的呢!”
我无力地呻吟着:“什么?”
红姑道:“霍少要走,你却死死抓住人家袖子不让走,嚷嚷着让他说清楚,你说得颠三倒四,我也没怎么听懂,反正大概意思好像是‘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你可不可以对我坏一些?你对我坏一些,也许我就可以不那么难过’。弄得霍少坐在榻边一直陪着你,哄着你,直等你睡着才离去。”
我惨叫一声,直挺挺地跌回榻上,我究竟还胡说八道了多少?
渐渐想起自己的荒唐之态,一幕幕从心中似清晰似模糊地掠过。我哀哀苦叹,真正醉酒乱性,以后再不可血一热就意气用事。
我伸着裹着白罗的左手道:“我记得这是你替我包的。”
红姑点头道:“是我包的,不过霍少在一旁看着,还督促着我把你的指甲全剪了,寒着脸嘀咕了句‘省得她不掐别人就掐自己’。可怜我花在你指甲上的一番心血,但看到霍少的脸色,却不敢有丝毫废话。”我忙举起另外一只手,果然指甲都变得秃秃的。我哀叹着把手覆在脸上,昨夜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怎么没人唱歌了?”我趴在马车窗上大口吸着冷风。
霍去病把我拽进马车,一脸无奈:“怎么酒量这么差?酒品也这么差?”
我笑着挣开他的手,朝着车窗外高声大唱:“铁弓冷,血犹热,奋勇杀敌保家乡……好男儿,莫退让,马踏匈奴汉风扬……”
他又把我揪回了马车:“刚喝完酒,再吹冷风,明天头疼不要埋怨我。”
我要推开他,他忙拽住我的手,恰好碰到先前的伤口,我龇牙咧嘴地吸气,他握着我的手细看:“这是怎么了?难道又和人袖子里面打架了?”
我嘻嘻笑着说:“是我自己掐的。”
他轻声问:“疼吗?”
我摇摇头,指着自己的心口,瘪着嘴,似哭似笑地说:“这里好痛。”
他面容沉静,不发一言,眼中却带了一分痛楚,定定地凝视着我,看得已经醉得稀里糊涂的我也难受起来,竟然不敢再看他,匆匆移开视线。
红姑笑得和偷了油的老鼠一样,揪着我的衣服,把我拽起来:“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喝完醒酒汤,吃些小米粥,再让婢女服侍着你泡个热水澡,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小谦和小淘现在喜欢上吃鸡蛋黄。小谦还好,虽然想吃,也只是在我喂食的时候“咕咕”叫几声;小淘就很是泼皮,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在我裙边绕来绕去,和我大玩“步步惊心”的游戏。我在“踩死它”还是“胖死它”之间犹豫之后,决定让它慢性自杀。这个决定害得我也天天陪着它们吃鸡蛋:它们吃蛋黄,我吃蛋白。
我时不时就会看着小谦和小淘发呆,我尽力想忘记九爷的话,那句“曲子倒是不错,可你吹得不好”每从心头掠过一遍,心就如被利刃划过般地疼。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任何联系,有时候我会想,难道我们从此后就再无关系了?
夜色低垂时,我倚在窗口看点点星光,小谦和小淘在黑夜中刺眼的白时刻提醒着我,今晚的夜色和以前是不同的。我暗自问自己,我是否做错了?我也许根本不应该吹那首曲子,否则我们之间至少还有夜晚的白鸽传信。我太贪心,想要更多,可我无法不贪心。
清晨刚从水缸中汲了水,一转身却无意中扫到窗下去年秋天开的一小片花圃中的几点嫩绿。我一惊下大喜,喜未上眉头,心里又有几丝哀伤。
走到花圃旁蹲下细看,这些鸳鸯藤似乎是一夜间就冒了出来,细小的叶瓣还贴着地面,看着纤弱娇嫩,可它们是穿破了厚重的泥土才见到阳光。从去年秋天,它们就在黑暗的泥土里挣扎,从秋天到冬天,从冬天到春天,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不知道头顶究竟多厚的泥土,它们是否怀疑过自己真的能见到阳光吗?
我轻轻碰了下它们的叶子,心情忽地振奋起来,催心砚去找花匠帮我扎一个竹篾筐子,罩在鸳鸯藤的嫩芽上,好挡住小谦和小淘。它们还太弱小,禁不得小淘的摧残。
晚上,我在石府围墙外徘徊良久,却始终不敢跃上墙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现在才明白人对真正在乎和看重的事,只有患得患失,勇气似乎离得很远。
想进不敢进,欲走又舍不得,百般无奈下,我心中一动,偷偷跳上别家的屋顶,立在最高处,遥遥望着竹馆的方向,沉沉夜色中,灯光隐约可见,你在灯下做什么?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只三两颗微弱的星星忽明忽灭。黑如墨的夜色中,整个长安城都在沉睡,可他却还没有睡。我独自站在高处,夜风吹得衣袍飒飒作响,身有冷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