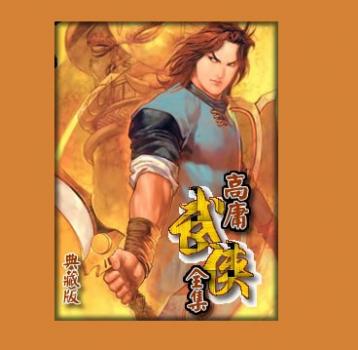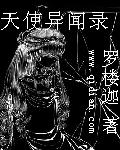二战回忆录-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 ※ ※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 ※ ※
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 ※ ※
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①
①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
“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 ※ ※
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①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