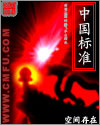中国一九五七-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事故发生在回“御花园”的途中,也就是在刚刚踏进沼泽地时,陈涛发现一条蛇在泥水中缓慢爬行,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意识中清楚此刻不是捉蛇的时候,但终是经不住诱惑,决定将其捉拿。他追蛇捕蛇时不慎滑倒在地,这时蛇瞅准时机咬了他一口,逃走了。当时天已快黑,雨还下着。返回场部就医已不可能,只好回到“御花园”。这就是陈涛被蛇咬的全过程。
你不能断定咬你的是有毒蛇。老龚说。
是毒蛇,长着一颗三角形头。陈涛说。
这不完全说明问题,长三角形头的蛇不见得都是有毒蛇。老龚说。
陈涛开始发烧了,浑身很烫,又冻得在被窝里打哆嗦,完全是中蛇毒的症状。对此老龚也不再怀疑。但我们没有对症下药,只能硬撑,我和老龚都清楚陈涛能不能过这一关,取决于他自己的生命力。
我完了,老周。陈涛用绝望的目光看着我:那天咱们还唱打回老家去,看来我回不去了,我要死在这儿啦。老陈,你别胡思乱想,不是所有中蛇毒的人都没救,关键是要有活下去的信心,精神是第一位的。我极力安慰他,我知道自己的话有多么苍白无力。
龚教授,平日里我对你不尊重,没大没小,这都怪我政治觉悟不高,我现在提前向你道个歉,否则我死了……你不会死的,老陈,你好好睡一觉,明早就会好的。老龚安慰地说。
我不要睡,我知道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我,我才二十七岁呀,我还戴着帽子,我还没结婚,呜呜……陈涛说着哭泣起来。
我和老龚都不知怎样安抚他,只是木木地看着他。
我知道,是我做了孽呀,我杀了那么多蛇,这是报应啊,呜呜,我发誓,只要别叫我死,以后就不再杀蛇了,呜呜。陈涛边哭边说,像对自己,又像对沼泽地里的蛇们,我怀疑他的神志已有些不清楚了。
这时老龚也有些支撑不住了,他本来就虚弱,加上刚才一番折腾,额头往下掉着大颗汗珠,身体也摇摇晃晃,我赶紧把他扶到铺上让他躺下。老龚闭了一会儿眼又睁开,让我把油灯挂在他头上的墙上,他从枕边摸出一本书看起来。
陈涛渐渐安静下来,慢慢合上眼。
雨下大了,雨声很响。
陈涛又睁开眼,把头歪向老龚的铺,声音微弱地问道:龚教授,你说神经性蛇毒和血液性蛇毒哪样厉害呢?
我说:老龚讲过血液性蛇毒厉害。但你中的肯定不是这一种毒。
你有根据么?他问。
有,根据就是你现在还活着。我说。
陈涛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得出我这句话很入他的耳。
这时老龚将目光从书本上移到陈涛脸上,问:老陈,你看见咬你的蛇么?
陈涛哭丧着脸说:看见了,要不是当时顾脚就能把它抓回来了。
老龚说:这本书里有各类蛇的照片,你看看有没有咬你的那一种?老龚说着将书递给我。我交到陈涛手里。陈涛就看起来,过会摇摇头说没有。
都不说话了。
这时雨下得更大了。电闪雷鸣,春季里下这种大暴雨是罕见的。在闪电耀亮的瞬间,我从窗子里看到沼泽地白花花汪洋一片。随之而来的雷声好像要把我们的窝棚震垮。我不知道雨继续这么下会不会吞没了“御花园”,我感到恐惧。
陈涛陡然坐起,瞪着眼说:老周,我想吃饭。
我一怔:你说什么?
我想吃饭,咱有粮食了,我真馋粮食啊,龚教授你也别睡,咱一块儿吃,老周你也吃,今晚吃上一顿饱饭死也闭眼了……陈涛认定自己是死定的人,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我的心一酸,险些掉下泪来,我说:老陈,我给你做饭,让你吃饱。我转向老龚:老龚,你也吃,这些日子……我没往下说下去,大家都心明的事情说出口是多余的。
我看看搁在枕边的手表,时间是上半夜十一点零五分。我开始做饭。“御花园”有一个小煤油炉,来路我不清楚,因为煤油短缺,平时基本不用,我决定这次派它的用场。领来的口粮还是以高粱面为主的杂和面儿。做烙饼?还是做粥?利弊是很好权衡的。吃饼过瘾,可太费,喝粥不解馋,可细水长流。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问陈涛想吃干吃稀。陈涛不假思索地说吃干。陈涛的回答使我顿生疚责,他差不多是个快死的人了,还有奄奄一息的老龚,在这生死攸关时刻我还管他妈的什么细水长流,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说吃干,咱吃干,吃烙饼。窝棚在风雨中剧烈摇晃,闪电横扫,雷声震耳,水从天降,世界似乎到了末日。我无疑在制作“最后的晚餐”。
饼做好了,满屋香气扑鼻,我喊陈涛和老龚起来吃饭,却没有回声。再喊还没有回应,一看,见他们都紧闭着眼,我的心猛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刚才光忙做饭,没顾上注意他俩的动静。我首先到陈涛的铺前,把手按在他胸上,啊,他还有呼吸,很微弱。他还活着。这时我又一次想起老龚的“薛定谔猫”。按照老龚的推理,陈涛原来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当我把手在他胸上一按,半死半活的陈涛就突然变成了活的陈涛。难道事情是这样吗?我不懂物理学,但我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事实是,在我按陈涛的胸之前和之后,他都活着;但只有通过这一按,“陈涛还活着”这一事实才被我所认识。这里确实有一种突变,但突变的是我的主观认识,而不是陈涛是死还是活这样的客观事实。回头再看“薛定谔猫”,情况也是这样,“箱中的猫是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是活猫的概率是二分之一”,说的是观察者的主观认识,而“箱中的猫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说的则是猫的客观状态。老龚把这两个概念给混淆了,这才得出“太阳在没有人看时就不存在”的奇谈怪论。烙饼的香味给了我灵感,我终于摆脱了老龚的这一难题带给我的困扰。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评价我的这种想法,反正我自己理清了思路。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陈涛还活着。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我无从判断。我又走到老龚身旁,他睡得很熟呼吸很均匀。我知道老龚一直神经衰弱,睡眠不好,可现在倒睡着了。莫非是烙饼的香气将他催眠了?我同样无从判断。我不忍心叫醒他,让他醒来便吃上期待已久的食物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现在又有了问题,问题是我,我怎么办?今天我没吃任何东西,早已饥肠辘辘。还有做饭这一过程已唤起我不可遏止的食欲,可说是一发而不可收。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在陈涛和老龚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我吃不吃“独”食呢?人生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小到丢不丢弃一条脏手帕,大到放弃不放弃一个王位。就是说大人物有大人物雷霆万钧的选择,小人物有小人物无足轻重的选择,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无足轻重就成了雷霆万钧,比如我此时此刻的“吃还是不吃”的抉择其意义和分量完全不亚于哈姆雷特的“是死还是活着”的抉择。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是个俗人,小人物和俗人的特征是欲望总要占理性的上风。我吃起饭来,大口大口地独自吞咽,我的嘴巴和头脑分工合作,嘴负责将饭送到肚里,头脑负责找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但在意识深处,我清楚任何开脱都是苍白无力的都不能将“小人”开脱成“君子”。“御花园”那个风雨大作的夜晚,我经历了人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我一方面得到了无与伦比的饕餮之足,另方面,心灵上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
早晨雨停风止,明媚的阳光从窝棚窗口射进来,一扫昨天的阴霾景象。晚上睡得很好,很踏实,不用说与睡前吃饱了饭有关。吃饱了饭真好,吃饱了饭睡觉更好,吃饱了饭睡觉醒过来感觉赛神仙,浑身每根毛孔都舒畅,都消停,透着满足。
我醒来头一件事就是看陈涛,看他是否还活着。昨晚吃过饭我守护了他一阵子,后来实在困得不行,就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是陈涛冒雨背回粮食的头一个受益者,蛇又咬了他,生死未卜,我不该只顾睡觉,我为自己未能尽责而感到内疚。我走到他的铺边上,心一下子提起来。我曾做过一次箱里的猫,而这遭轮到了陈涛,他的死活决定我的一瞥。这是多么残酷的一瞥。我简直就像一个刽子手回头一瞥他的刀下人那般把目光投到陈涛身上。啊,谢天谢地,他还在喘气,身上的被子随同他呼吸的节奏起伏,很微弱,却说明了他活着。我放下心来。伸手摸摸他的额头,仍然很烫,烧没有退。大概是我的抚摸给予他感知,他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呓语,像对我诉说什么。是说别担心我还活着?我不再管他,又去看老龚,这一刻日光正通过窗子照在老龚的上身,聚光灯似的,我陡然发现老龚铺上换了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圆圆的一张大脸,绽着光亮(老龚的脸像树皮般灰暗无光)。这瞬间我惊讶得叫出声来,这叫声惊醒了睡觉的陌生人,他睁开眼,四目相对中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是老龚,不是别人,是肿了的老龚。我的心忽嗒一沉。在劳改农场犯人本不把肿当成一回事的,一是大家都肿,再是一时半时死不了人,一旦补充上营养也就没事了。问题是肿与肿不同,有人是一点一点地肿,有人是突然肿,犯人都清楚突然肿是很危险的,十有八九没救。老龚一定是看出我的神色异常,问:老周,你咋啦?我连忙掩饰,说没什么,一切都好好的,老陈也没事儿,还睡着。老龚朝陈涛看看,那陌生的圆脸现出让人无从揣摸的表情,说:不知他是睡着还是昏迷。我说:咬老陈的大概不是毒蛇吧,要是毒蛇老陈早就完了。老龚说:叫毒蛇咬了过十几天才死也是有的。我问:为什么同样被毒蛇咬,有人立即死,有人拖几天死,还有人能活过来呢?老龚说:这与蛇毒的类型和中毒的程度有关。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的。生命力顽强的人活的希望大,老陈体质一向不错,我想他能坚持过来。我点点头,我觉得老龚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